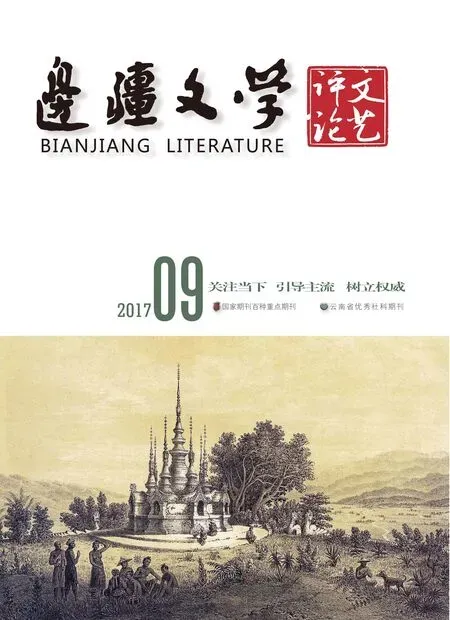沒有救贖的“罪與罰”
——評夏天敏中篇小說《是誰埋了我》
唐詩奇
新銳批評
沒有救贖的“罪與罰”——評夏天敏中篇小說《是誰埋了我》
唐詩奇
·主持人語·
本期新銳批評所發三篇作品都是青年評論寫作者,文章都較短,卻顯示出了批評的敏銳與坦誠。唐詩奇對老作家夏天敏的新作作出及時的評析,不僅看到了這一作品與這位前輩作家創作上的不同,指出其探索的意義,可見她對夏天敏過去的創作有充分的了解,有此基礎才有批評深度的可能性;她還直言不諱地指出這部新作的缺憾,是平等對話的立場。一個初出茅廬者面對著名的前輩作家,有無平等對話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趙靖宏對居于香港的傣族作家禾素的散文作了較為全面的解讀,讓我們看到了遠離故土的作家深厚的鄉愁,牽起了香港文學與云南文學的一條紅線。沈鵬對藏族作家永基卓瑪小說的理解雖然寫得簡單了些,但不失為一個特殊的角度。對云南迪慶藏族文學的理解,我們也還處于相當初淺的程度,希望有更多的評論家參與其中。(宋家宏)
一
《是誰埋了我》是夏天敏最新的中篇小說,發表于《十月》2017年第四期卷首,引起一定的關注。該作講述了一個被俘的解放軍李水在成功逃脫之后無法釋懷、不斷尋求重生的故事。夏天敏把小說設定在建國之初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把參軍、剿匪、修水庫這樣的標志性事件雜糅在一起,又加入了被俘、造墳、驅邪等富有傳奇性和神秘性的情節,使得小說既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又富有閱讀的趣味性,是夏天敏近年來不斷探索、耕耘的成果。
夏天敏自80年代開始創作以來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他的小說多關注農村題材,多以昭通為背景來聚焦社會現實問題,以農民為主要描寫對象,書寫底層人民的苦難,有鮮明的批判精神和悲憫情懷。已出版散文集《情海放舟》,小說集《鄉場上的皮匠》《鄉村雕塑》《飛來的村莊》《絢麗的波斯菊》《窄窄的巷道》等。在之前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之作《好大一對羊》。《好大一對羊》為夏天敏的創作樹起了一座高峰,長久以來,夏天敏的小說創作似乎與《好大一對羊》畫起了等號。但夏天敏是一個有自覺藝術追求和實踐的作家,長期以來對各種主義、流派的嬗變的了解與實踐,讓他對自己的寫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回歸到人和人物命運本身。《是誰埋了我》就是這樣一部關注在大時代中個體命運的作品。
承接了以往的豐贍飽滿的悲憫情懷和反思精神,《是誰埋了我》無論從思想深度還是藝術實踐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在小說中,那種直截了當的道德批判被懸置起來,漫畫式的夸張描寫、符號化的人物與二元對立的敘事套路也退場了,取而代之的是歷史、組織與個體的復雜關系,夏天敏把個體放置于特定的歷史時期,更著重表現個體在時代和體制之下復雜、糾結的精神世界與命運浮沉。這是一個糾結且沉重的故事,如果說前期的作品還能給人“含淚的笑”的閱讀體驗,那么這篇小說則可以說是沉重的“罪與罰”。如同拉斯科爾尼科夫一樣,李水內心也飽受著罪責的懲罰,但在信仰缺失的國度,李水始終沒有得到救贖。
夏天敏曾說過,“沉重永遠是我創作的一個主題。”從前,夏天敏小說的沉重感來自于對那些大山深處觸目驚心的貧困的感同身受,他把所有的苦難的根源歸于貧困,而對“貧困”的追問缺乏精神向度的開掘。在《是誰埋了我》中,他不再急于書寫、忙于控訴,而是緩慢地講述,仔細打磨細節,對人的精神狀態與人在時代中的命運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從聚焦當下的社會問題到回歸歷史與人性,夏天敏的創作呈現出越來越深沉、扎實的特點。
小說的標題為《是誰埋了我》,這個“誰”在通篇小說的敘述中依舊懸而未決。“我”最先是被組織埋了,后來為了獲得重生自己把自己埋了。所以小說中實際上建了三個“墳”:第一個是組織為“不在了”的李水建的“革命戰士李水之墓”,第二個墳是李水自己在河邊捏了個人形,為自己建了一個墳,第三個則是李水秘密地在心里建造的“墳”。在“是誰埋了我”的追問中,失落于時代的個體逐漸浮出水面。
二
新生的政權正在建立,為了鞏固政權和維護人民生活的安定,李水隨軍進入烏蒙山,目的是剿滅烏蒙山腹地的一支強悍的土匪。然而在伏擊土匪的過程中情報出了問題,反而受到土匪的襲擊,解放軍傷亡慘重,不得不撤退。在倉促的撤退中,無法顧及傷員。李水作為唯一活下來的人被土匪俘虜,與匪首之女桃花結下了一段孽緣,從此成為李水心中無法消除的陰影。即便他逃出匪窩,帶隊剿滅了這支土匪,立下大功,依然無法卸下心中的重負。與此同時,家鄉人為被組織認定為“不在了”的李水建起了高高的墳墓。他的失蹤被組織模糊地定義為“不在了”。這個“不在了”非常有意思,它既非生,亦非死,讓人聯想到同是云南作家的胡性能的小說《消失的祖父》。在歷史中,人的生死與身份一樣難以確認,充滿著虛無和荒誕的意味。
李水活著回來了,靈魂卻已經死去。為了尋求重生,李水用河灘上的泥捏造了一個自己,很莊重地把自己埋了進去,試圖與過去告別。與其說是“自埋”,不如說是一種“自救”。這個極富儀式感的葬禮使得李水的重生之路顯得滑稽而悲壯。然而李水的自救之路,無論是請道士作法驅邪,還是拼苦力去修水庫,不但是徒勞,且反而成為他更大的包袱——正如卷首語所言,“受之有愧的榮譽,比不正當的感情,更加讓人飽受折磨。”
李水一直在糾結中度過,糾結的過去使得他不斷在當下陷入“疲軟”狀態。與桃花在一起的時候,因無法面對為救他而死去的班長而愧疚,與玲子在一起的時候,又總是被與桃花的那段陰影所糾纏。情欲是生命力的象征,李水情欲的無能為力象征著其生命力在這樣的心理重壓下一點點被磨耗殆盡。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李水“自己”埋了自己,而前者的“自己”其實代表的是組織、體制或是意識形態,在這個“自己”的背后,依然是大時代在推波助瀾,而后者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個體。在小說中,組織一直都是以溫情的面目示人,非但不追究他與桃花的過往,還對他委以重任,給予嘉獎。這就構成了一種荒誕,在個人與組織的對立中產生了微妙的張力——一方面,組織在精神上“綁架”了個體,使得個體飽受折磨和壓迫;另一方面,個體隱瞞了組織,而組織卻更加信任、寬恕個體。
當我們為“李水為何如此?”而感到不解時,我們必須反問一句:李水還能怎樣?作為伴隨著革命和政治運動出生成長的一代人,李水的潛意識里都被注入了英雄主義的革命因子,視死如歸的榮譽感潛移默化形成了思想之網。忠誠與榮譽是他們最為看重的東西,雖然聽起來虛無縹緲,但卻實實在在地落在生活的每一處。李水的作繭自縛,其“繭”就來自這兩方面。視死如歸的榮譽感是支撐他們的信念和力量。“把榮譽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堅信為革命犧牲比啥都光榮,只要獲得這個榮譽,他和家里會受到人們永遠的敬仰和尊重。”這一點在婦女主任那里得到更實在的闡述:“人活著靠啥?就靠這臉面。”而對組織的絕對服從和絕對忠誠則是作為個體的必修課。“一聽到組織這個詞,李水的神經立即繃緊了。”“組織無時不在,組織無處不在,組織不是形式,組織是你的骨骼,是你的肌肉,是你的血管,更是你的靈魂。組織永遠照亮你的靈魂,讓你的內心藏不住任何東西。”組織無孔不入,就連李水的“私人問題”都被溫暖地“照顧”到,在他吃下狗鞭的同時,他最后的隱秘空間也一并被吞下了。
所以,與桃花那段情感糾葛,讓李水既失去了戰死沙場的榮譽,又因隱瞞這段經歷而失去了對組織的忠誠。在這雙重喪失下,雖然李水活著回來了,但當“革命戰士李水之墓”被刨除之時,那個英雄李水和“軍屬光榮”的榮譽就隨之而亡,剩下的只是一個背負著秘密的“茍且”的軀殼。
三
夏天敏延續了一貫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又加入了傳奇性、神秘性和魔幻性的因素等因素,成就了自己的一套寫作策略。現實與意愿的強烈反差是構成其作品藝術特色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荒誕感使得作品形成一種內在的張力。正如《好大一只羊》中劉副專員“好心”與之造成的惡果形成反差,《左手,右手》中斷指的疼痛和巨額賠償的喜悅形成反差,《是誰埋了我》中,李水極想獲得榮譽之時卻被俘,使得愿望落空,然而當他不再追求榮譽而只想尋求內心的平靜之時,榮譽卻一再降臨,讓他不堪重負。這種反差讓小說氤氳著一種揮之不去的無力感和荒誕感,構成了其小說的悲劇內核。
小說成功地塑造了李水這樣一個極度糾結復雜的人物形象。他從一個視死如歸、英勇無畏的解放軍戰士變成一個只有靠女人才能免遭一死的戰俘,作者寫出了他的掙扎、悔恨、憤怒和羞恥。從一心想尋死到向死而生,逃出匪窩,他強忍著與不愛的女人周旋,潛意識里為保護他而死去的班長血肉模糊的形象不時閃現,之后,死去的桃花怨念不甘的眼神又時常出現在李水的潛意識與夢境之中,讓他內心備受煎熬,充分表現了人物內心的復雜、糾結的精神狀態。小說中大篇幅的心理活動、夢境、幻想等現代性手法的嘗試,對人物內心有了更深度的開掘,也營造出一種壓抑、陰冷的氛圍。其次,作者還善于用細節刻畫人物,這也是李水這個形象之所以鮮活可感的重要因素。作者細致地捕捉到一個細節,李水為了實現逃跑哄著桃花進城,在城里遇到穿中山裝和李寧裝的人,他為了不暴露自己的心事,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羨慕,瞟一眼就堅決地轉開臉。第二次是李水帶軍隊剿滅了桃花所在的這股頑匪,看到躺在血泊里的桃花,李水內心很復雜,但怕被戰友看到,也是只一瞥就迅速離開了。這個“瞥一眼”的細節讓李水敏感、謹慎又有點小心機的性格躍然紙上,這也是李水“糾結”的個性原因所在,為李水整個精神的變化做出了充分的鋪墊。
傳奇性和魔幻性也是該作藝術上值得一提的地方。作為歷史題材,土匪群體的傳奇性書寫已不是夏天敏的第一次嘗試。此前,他就以土匪為主人公寫過長篇小說《古鎮遺夢》,刻畫出朱玉婉這樣一個敢愛敢恨、溫柔堅毅的女性形象,顯示出一種颯爽的英雄氣概。從當下向歷史深處的開掘似乎成為當代作家的一種集體性的轉向,夏天敏近來的創作從關注當下的社會現實問題、底層和苦難轉向對邊地歷史傳奇的書寫,試圖用新的眼光重塑邊地歷史生活,《極地邊城》《絢麗的波斯菊》《北方北方》和《古鎮遺夢》都是如此,顯示出作者對邊地傳奇的關注與重構歷史的野心。而“驅邪”這樣魔幻性的情節的加入,讓小說更富有吸引力和敘述的張力。從顯露魔怔到求助道士陳五先生驅鬼,再到削桃木女人燒成灰埋掉的過程,寫得驚心動魄。當然,困擾李水的是心魔,并非桃花化身的“女鬼”,當李水最后全面爆發把埋葬桃木形女人的坑挫骨揚灰時,才終于在心底清除了魔障。李水那種糾結、害怕、小心翼翼的心理表現得非常豐富,氛圍營造得鬼魅陰森,很見作者功力。
然而,當夏天敏放棄了得天獨厚的底層敘事經驗和對苦難、當下的關注之后,這種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演繹總感覺缺了點什么。那種從《好大一只羊》《左手,右手》《接吻長安街》等優秀之作中流露出來的切膚之痛消失了,反而陷入了一種故事化的寫作之中。當我們拋開作品的立意,回望整個小說的故事情節時就會發現,這實在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故事,在這樣一個頗具闡釋意味的標題之下,讀者的期待視野隨著故事的開展落空了,構思和藝術上的薄弱之處開始顯露出來:俗套的土匪的女兒突然愛上“我”的戲碼;一個伏擊了解放軍一整個小分隊的窮兇極惡的匪首不敢對李水用刑,竟然是因對方是解放軍,怕以后死無葬身之地;李水千方百計來到城里,在尋求部隊救援時被誤傷,“感到身上中了幾槍”卻依然活了下來,而尋求救援的崗哨剛好是他所在的部隊,就如夏天敏自己在文中寫道的那樣,“就跟爛熟的電視劇一樣”,太多的巧合顯示出故事的刻意經營。在人物塑造上也落入了俗套,除了李水之外,人物均顯得概念化。匪首的目光必然是“透露出陰鷙和狡黠”,土匪的女兒必然是既心狠手辣又溫柔多情的,自己心上人就是羞怯溫順……這種概念化的人物,似乎僅僅是為了推動故事發展而存在,從而皆削弱了小說的藝術性,極易讓讀者喪失研讀小說、探究小說主題意蘊的機會。與有著切膚之痛的鄉村題材苦難敘事相比,夏天敏仔歷史題材的把握和書寫上顯得有點力不從心。
雖然藝術處理上略有欠缺,但總體上來說,《是誰埋了我》仍不失為一篇值得一讀的中篇小說。它是夏天敏近年來創作轉向的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夏天敏在無論是題材、主題還是表現手法上的開拓和創新。我們期待夏天敏在歷史題材的寫作中,更進一步地把握人性及人在時代中的命運沉浮,寫出更優秀的邊地小說。當然,筆者更期待的是,在當下“三農問題”“城鄉問題”“扶貧攻堅”等社會問題日漸白熱的今天,有更復雜的問題、更荒誕的現象值得去關注、去書寫,夏天敏依然能堅守這塊陣地。畢竟,能在歷史的天空中展開想象力之翅的作家很多,但能對苦難有真正體察和悲憫的作家太少,希望作者不要放棄底層與苦難寫作,從歷史長河中回顧當下,寫出新時期的疼痛與堅守。
責任編輯:臧子逸
(作者系云南大學文學院2016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