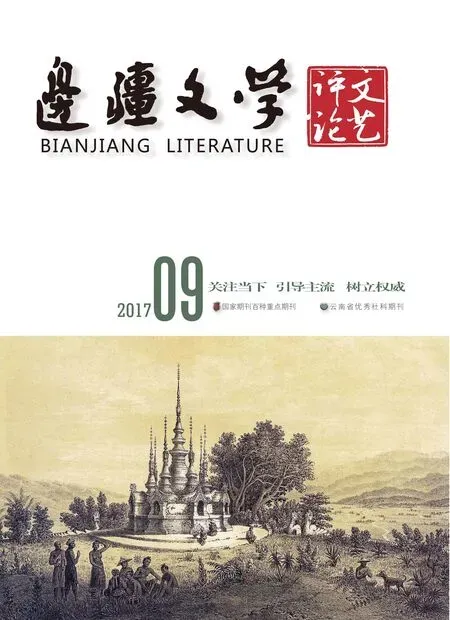可供復述的精彩
——關于冉隆中的傳奇性兒童小說
蔣 蓓
兒童文學聚焦
可供復述的精彩——關于冉隆中的傳奇性兒童小說
蔣 蓓
冉隆中新著《從前有座山》與《早年間》,各由六部傳奇性兒童小說組成。
這組作品的寫作之于冉隆中,可謂“雙重跨界”。一位早有聲名的批評家暨成人文學作家投身兒童文學創作,寫作技巧一旦令目標讀者感到不適,即會影響作品的品質和接受度。而這十二部傳奇性兒童小說,卻是例外,因為,它們實現了其可供復述的精彩。
作為一種人們借以追尋現實的載體,“故事在遠古時代就已出現,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以至舊石器時代。從當時尼安得塔爾人的頭骨形狀,便可判斷他已聽講故事了。”通過講述與傾聽,故事的交流與分享得以實現,人類與之相關的先天性欲望得以滿足。冉隆中的傳奇性兒童小說創作,基本都圍繞講述專屬中國的物產名目由來的故事展開。
講述事物名目由來,近似于對萬物起源加以想象與解釋。這種想象與解釋廣泛存在于民間神話中,是人類處于“兒童階段”時好奇與思索的成果,因此形成了最初的神。這種想象與解釋逐漸成為一種創作手法,借助它,兒童文學作者賦予故事新的思想內容,將堅毅、勇敢、善良、隱忍、細致、耐心、寬厚、克制等品質的魅力,傳達給讀者,同時在作品中隱喻對社會生活中假、丑、惡的批判。《從前有座山》里人參娃娃、知母草、何首烏等的故事,與《早年間》里一系列茗茶的故事,莫不如此。當知識、概念、道理和經驗被寓于十二個故事中,行云流水般地加以巧妙敘述,它們更容易走進小讀者的心靈世界,促發領悟與認同。
《從前有座山》的六個故事皆開門見“山”:第一個故事里的山上有座廟,里頭一老一少兩個和尚;第二個故事里的山上有間破屋,破屋里住了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第三個故事里的山上,有戶人家生了一對雙胞兒子;第四個故事里的山上住著戶單親家庭,他家那個孩子,名字有些怪異;第五個故事里的山上,有一個采藥世家的后人;第六個故事里的山上,同一屋檐下是一對同姓的石匠。由此,作家設置下懸念:老、少和尚間,師傅對徒弟是否關愛有加?春來下山去乞討的老婆婆,一路會遇見什么?相貌一致、性格迥異的孿生兄弟,各自的人生又會怎樣?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兒子,他的名字有著怎樣的來歷?祖祖輩輩采藥為生的老人,他的故事就在日復一日的辛勞中繼續下去嗎?石匠何小壯為什么會到了石匠何大壯的家里?隨后,一個個故事環環相扣地鋪陳開來,借助擬人、夸張等手法,作品構建起了一個亦幻亦真的離奇世界。這個世界里,有能說會動的人參娃娃、化作祥云的老婆婆、頂替兄長接受極刑的弟弟、歷盡艱辛為母求藥的兒子、傾慕勤勞勇敢孝順者并以身相許的少女……他們言行舉止中自然流露的天真良善、知恩圖報和重情重義,在循序漸進的敘述中,將積極的審美情感與價值取向傳遞給讀者,發揮著教益功能。至于虐待小和尚并妄圖貪占人參以求讓自己長生不老的老和尚,以及要么因為貪心、要么因為懶惰而錯失了隨瘋婆婆學習采藥本領的人,還有粗枝大葉、用心不專害得自家兄弟“送”了性命的那個哥哥,他們的劣跡或毛病,以遭到各式懲罰或付出沉重代價的方式,起到了告誡的作用。
《早年間》與《從前有座山》題材有別,立意則一脈相承,“新編”了六種中國名茶名字的由來,想象之翼在一張一翕間,把豐盈、細膩的肌理賦予這些不同尋常的故事。比如《龍井茶》里金榜題名的書生,主動選擇了“茶官”這個冷門職務,情愿回到杭州那十八棵野茶樹跟前就任、成家,從此致力于茶葉的采集、研制與改良,源于他的“真心喜歡”;比如《碧螺春》里形狀似螺殼、如螺鬟的茶葉,見證了一對自發希望為遭惡龍侵擾的太湖百姓解難,不惜獻出生命的青年男女的經歷與感情;比如《廬山云霧茶》里兩戶人家的宿怨,不期然間因為兩個青年后輩一次山間意外臨危時其中一人的襟懷而消除;比如《鐵觀音》里的兒子,一心渴望前程遠大,歷經高人指點回歸祖業——當茶農,從此有了一番作為;比如《大紅袍》里的女兒,想方設法替父伸冤后,攜一襲御用紅袍回鄉,為大紅袍茶在茗苑增色;比如《普洱茶》里藏在深山人未識的云南茶葉的故事,并未在它們被馬幫千里迢迢托運進京成為貢茶之際劃上句號,而是隨著欽差受命回訪茶葉產地又有了一段不絕的余韻……
師傅說,坐船和爬山,有什么區別嗎?
云順想了想,說,都得使勁兒,才能往前。
師傅說,一半對一半錯。
云順不解其意。
師傅告訴他:“逆水行船,只有一種選擇,不進則退;但如果是爬山,卻可能有多種選擇,往上走,繞著走,甚至退著走,以退為進,都可能到達目的地。”
(《早年間·廬山云霧茶》)
欽差說:“你看,送了貢茶的,都得到了金子,你卻什么都沒得到,你不覺得吃虧嗎?”
小伙子問:“要金子來干什么啊?”
欽差說:“金子可以讓人富貴啊,可以吃更好的,穿更好的,可以讓日子變得更愜意啊!”
小伙子說:“大人你看,我這里,茶是自己的,雞是自己的,媳婦兒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大房子是自己的,一樣不缺的日子,還要金子來做什么?”
欽差被小伙子問得答不上來了。
(《早年間·普洱茶》)
行山路乃至行人生路,退、進之間,自有回旋的辯證。而參與運茶進京所掙得的財富,跟作為“家鄉寶”的邊地少數民族山民們安享的自在、逍遙相比,又孰貴孰賤?“所謂中國特色的元素,強調的是特色而非模仿。它不單是一個中國的景物、一座建筑,也不完全是前門大碗茶、風車和糖葫蘆這些表面的東西,它更多的是指那種精到的、哲學的、智慧的、一針見血的想象和表達方式。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因素一旦出現在作品里,立刻會被讀者強烈地感受到。”如果說,《早年間》中的一系列故事以其情節的曲折、跌宕,體現出對兒童因其感性認識強于理性認識、形象思維強于抽象思維而更傾向閱讀、欣賞故事的習慣的尊重,那么,除去素樸的臧否,地域特色、哲思意味的添加,又助長了這部作品對有情、淡泊、恩義、勇敢、豁達、機智等等的張目,體現了對兒童讀者理解能力的信任——孩子們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場和生命想象,通過對故事的涵泳而感受現實世界的深廣、多維,在精神享受中體味生活的真實,思考人生的疑難,逐漸實現心靈的成長。冉隆中的兒童文學創作,在探索“精到的、哲學的、智慧的、一針見血的想象和表達方式”方面,做了嘗試。
《從前有座山》與《早年間》對讀者進行著教益與啟發,卻又超越了簡單的成人經驗灌輸或道德規范教化,這與作者的語言技巧密切相關。
單薄的情感難經得起體會,說教、乏味的語言則不免令兒童生厭。語言是讀者接觸文學作品的首個層面,因此,用心的作者善于把握孩子們表達情感、思想的方式、方法。《從前有座山·小和尚與人參娃娃》開篇,即“故事范兒”十足:
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里,有一個小和尚。
這個開頭,明顯是講老故事的套路,而且,老掉牙了。
其實,我們要說的這個廟,廟里真實的情況是:小和尚之外,還有一個老和尚。
只是,故事發生的那一天,剛巧,老和尚不在廟里。
老和尚去哪里了呢?老和尚下山去了。
要是在別的寺廟,派下山去的,一般都是小和尚。下山之前,白眉毛的老和尚,會對黑眉毛的小和尚,千叮嚀、萬囑咐: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老虎會吃人啊;
見到了女人你要躲,千萬要小心啊——
這不,還是套路!
但是,這個寺廟發生的故事,其實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陳述,隨即將此陳述自評為“套路”,繼續陳述,隨即再度自評“套路”,轉折后再繼續陳述……一番口語式的周折,宛如與讀者展開對話,親切、風趣,引發讀者對即將抖開的“包袱”——一個“其實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故事的好奇,營造出令人仿佛圍坐火爐邊的情境。
他把樹木山林,看做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也是心中的神靈。
因為他知道,樹林是家園,庇護了無數飛禽走獸;樹林是溫床,養育了各種珍稀藥材。
走在采藥路上,他會哼哼自編的歌謠:高高的山啊大大的樹,你把藍天,頂得更高了;美麗的野花青青的草啊,你把大地,渲染得更鮮艷了……
他就像一個寂寞的行吟詩人,只為大樹和小草兒歌唱,為松鼠和小鳥兒歌唱,為猴子和小兔子歌唱,為藤蔓和野花野草歌唱……
(《從前有座山·深山里的黃精靈》)
這是小說主人公眼里、心頭的風景,也是故事呈現給讀者的“風景”,種種美麗、溫柔或博大,因著流暢的文字,繪制出一幅人與自然相洽的圖卷,參與了作品的精神構建。
又如曹文軒所言:“我們在復述那些古典的作品時,有一個基本的動機,這就是打動聽者。我們——復述者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復述能夠打動聽者,正是因為我們相信那個被復述的作品,它自身就有這個功能。而這個功能是藏于故事之中的。通過故事,人的不幸、人的坎坷、人的情操才得以體現。”冉隆中的傳奇性兒童小說,以短句為主,免去了長句、復句可能制造的語意混亂,簡潔有效地表達所敘述內容,與扣人心弦的情節的發展相得益彰,實現了敘事的通透、明了,具有可復述性。掩卷多時,對碧螺春的故事究竟發生在太湖還是西湖已然印象模糊了的讀者,仍會清晰記得那對男女為了人間安寧而做出的犧牲。至于在普洱茶故事里優哉游哉、反詰欽差的那個小伙子,他究竟是拉祜族、哈尼族還是基諾族已不重要,關鍵是,他的一句“還要金子來做什么?”,道出了普洱茶與眾不同的緣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物,云南的大山,易于滋養散淡的性格與灑脫的脾氣……
大約因為作者在構架故事情節方面太過注重,對人物內心的探索反而有限,部分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不夠豐滿。比如《從前有座山·三七不是二十一》中的那位雙胞胎弟弟,“一聽說哥哥需要‘盤纏’,他將壓在箱底的一個包袱皮兒翻出來,‘嘩啦’一聲,將里面的銀元、角子,全倒在了哥哥張開的口袋里”,在其兄長下獄后更設法借送斷頭飯之機灌醉獄卒,“三把兩把,剝皮一般將哥哥田里身上的囚服剝了下來,迅速地穿在了自己身上;又把那一面枷鎖,套在自己脖頸上;然后,拖著腳鏈,叮叮當當地走向充做刑場的菜市口。”這直至付出性命也無怨無悔甚至沒有絲毫遲疑的選擇,使得弟弟的言行,因缺乏充分的動機支撐,更像是在機械配合作品意欲警示的“切不可耍小聰明,否則將以性命為代價!”。又如《早年間·廬山云霧茶》里,聽過僧人解簽“退后一步自然寬”的一席話后,似有所悟的云順,卻未在接下來與仇家一道下山的途中為化解兩家人的仇怨采取任何建設性的行動。這些,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肯尼思·格雷厄姆筆下怡人的蘇格蘭田園風光,塞·拉格洛夫筆下瑞典大地上瑰麗的自然景色、古老的歷史文化,宮澤賢治筆下典雅多姿的日本民俗……傳統文化、民族元素,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根”的意義,其間蘊藏著人類生命和情感的符碼,一旦以文學藝術作品為媒介接觸、體察到它們,這些符碼很容易令受眾與更廣闊深遠的時空產生聯系,從而獲得精神內在的歸屬感。圍繞各種草藥、香茗及與之結下或這或那不解之緣的人們編織故事,冉隆中的傳奇性兒童小說,題材、意象、語風,均植根于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由它們所復合而成的精彩,是否昭示著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實踐,應當在深入把握兒童內心情感世界的同時葆有民族性?因為,這樣的創作方能以其自信、活力,參與到一片繁榮前景的建設中去。
【注釋】
[1] [英]愛·摩·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蘇炳文譯,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
[2] 黃貴珍:《中國幻想文學如何實現本土化》,人民網,2012年8月17日,http://culture.people.com. cn/n/2012/0817/c1013-18771444.html。
[3] 梅子涵等:《中國兒童文學5人談》,天津:新蕾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頁。
(作者單位:昆明理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責任編輯:臧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