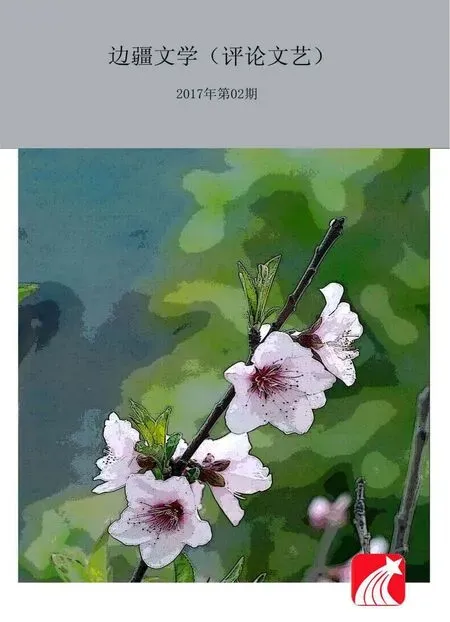論黃代本小說地域性四重存在水乳交融的特色
夏 玲 曾子芙
論黃代本小說地域性四重存在水乳交融的特色
夏 玲 曾子芙
黃代本作為一直堅守在昭通本土的作家,其小說的昭通地域性特色十分鮮明,是很有個性的地域文化小說。他的系列小說圍著泥鰍河畔的蓮花村寫作,他多層次地深入書寫了昭通的地貌、人情、風俗、歷史、宗教和文化的獨特性,塑造了一系列有地方特色的人物形象。黃代本作為一名小說家,雖然“在溢滿云南,乃至全國的昭通作家群中,黃代本并不像……一樣為廣大文學愛好者熟知”。但他的作品在昭通本地人中卻有為數眾多的讀者。
并不是昭通籍的作家寫出來的小說就是昭通地域文化小說,“地域文化小說并不是簡單地以地理性的區劃來歸納小說和小說家,也不是單純以小說的文化類別和特征來區別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而是通過這個雜學學科派生出一種新的小說內涵特征,地域文化小說要具備地域、種群、小說三個要素,而且還包涵各種各樣政治的、社會的、民族的、歷史的、心理的……文化的內涵。”,我們說黃代本的小說是地域文化小說,正是因為他的小說從地域存在的若干方面,反映了昭通地域特殊的政治的、社會的、民族的、歷史的、心理的內涵。
一、地域客觀物質存在的細節真實表達
黃代本的小說是非常有個性化的文字,他的小說整體虛構,而細節處處真實可靠。他的寫作是在寫作空間上有中心有邊界的寫作,圍著他心目中的故土寫作,虛構了泥鰍河畔的蓮花村,但是這個村莊的自然存在物,如這個地方的地理地貌特征,村子前的風水樹、龍尾的麻柳灣、龍頭的臥佛山、五尺道、斷山筋的埡口、被煙槍打死的耗子等,都是他具體觀察過的自然存在物,他寫的烏蒙山區有地理地貌上的真實性,我們從黃代本的作品中可以讀到烏蒙山的大山大水帶給人視覺上的震撼,更多的我們還可以讀到這種封閉而艱難的自然環境的神秘莫測之外,給人的生存帶來的苦難。黃代本筆下真實的地理存在,來源于他對這些地理存在的走遍烏蒙式的反復野外考察,他筆下的山川大地,是人物真實的生活環境,是人物肉體生活所在的具體的地理環境。
黃代本筆下的人類創造出來的存在物,蓮花村的一所房子、一個農具、一個石磨、漏雨的瓦房、門背后的火塘、雨后很滑的山路、苞谷糊糊上長出的人工菌等蓮花村的物質存在細節,在他筆下,每一點一滴都是真實的。他筆下半巖上的村莊、何天麻和何半夏兩兄弟住的院子是乾隆三年修的、兩岔河村的諸葛石、陰沉木棺木、雁鵝派出所、葫蘆口夜總會、古螳螂山、挑水巷等等,都是蘊含昭通歷史痕跡的真實而特殊的物質存在。
我們再來看,他筆下一身汗臭穿氈褂戴氈帽的老者是用黃銅煙槍抽大耆老的葉子煙,富的村民則是抽花腰桿的龍泉煙和綏江雪茄,村民的一餐是“煮了一鍋洋芋,燒了一把青辣子,煮了一鍋酸菜紅豆湯”,而送人的則是天麻、打屁蟲、紅富士蘋果。“他家祖上在大清年間是出過鎮守使的,留下了一頂紅頂子,何十五一直很珍視這紅頂子,當作傳家寶一樣收藏。”當然,僅僅對這些昭通特色的物產存在進行展示也是沒有意義的,黃代本的小說中,這些物產給人帶來的地域性情感非常厚重。我們來看:“吳常蘭說,要得,我活了五十多歲了,還沒有進過城,哪天也進城看看去,聽說城里月中桂糕點廠有種東西,名字我叫不出來,我也是前個月回平灘子聽郭彬家媽說的,是糯米做的,放到嘴里就化了。”還有:“何中貴的父親感慨地說,為了供你讀書,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喝過酒了,你哪天回來的時候,整一斤盤河的燕麥散酒來給我喝。”“老湯圓背著昭通的蕎粑粑上訪”,月中桂的綠豆糕和燕麥散酒作為人物向往的一種物質存在,讀來讓人心酸,而蕎粑粑作為上訪道具,幫助了人物的形象塑造。這些敘述常常有剔骨爆傷,深入事物本質的地方,讀之讓人陡然驚起,如冷水澆背,但是又有慈悲心懷。
他對這些物質性的存在的感受,在小說中的描寫也具有體驗上的真實性,如“一個人睡在山上,就覺得十分的靜,靜得連自己心臟的跳動都像在打雷,血液在血管里流動的聲音都像泥鰍河漲水了一樣。”如“從農村出來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在農村覺得是干凈的衣服,穿著進城的時候,走到半路就覺得不太干凈了,到了城里,就覺得直接是臟衣服了。”“到了鄉政府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路時覺得腳是腳手是手的,就像電影上的機器人。”他小說中類似細節描寫,保證了他的小說人物所見所聞所嗅所感的細節真實性,而這些細膩的感受和經驗,是小說打開讀者經驗世界的重要元素。
他筆下的物質存在再現了昭通的風土人情和歷史遺跡,有濃重的地域性及現場感,這些表現昭通地方文化的源遠流長和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的物質存在,還帶著神秘的傳說,給現在生存其間的人心理上帶來影響,如黃家天井“在廊檐之下,有八根圓木支撐的互相連通的供黃氏弟子讀書的書樓”。昭通的耕讀文化源遠流長,影響著住在其中的年輕人。再如“樹下有一個大石頭,村子里的人稱為諸葛石,村子里的人說的是諸葛亮火燒藤甲兵就是在這里進行的,當時的彝族兵馬全部被燒了滾到兩岔河里,諸葛亮坐在這塊石頭上淚流滿面感嘆說自己要折壽,果然五十四歲死在了五丈原。諸葛亮在死后,經常回到這兒,下蒙凇雨的時候就出來夜游,老百姓說諸葛亮由于后悔傷生太多,成了這兒的夜游神。”昭通民間文化因素被很好地吸收在小說中,成為小說的趣味神秘的細節。
小說反映了昭通地域的客觀物質存在,也反映了人們在這個地理空間中的生存困境,寫出了底層人物物質上的貧乏和生命的不舒展,寫出了人物對自然和環境的細密感受,寫出了人物內心的呼嘯、吶喊、掙扎和雷霆。
二、地域歷史文化存在的厚重深入表達
黃代本小說中激情和理性都十分充足,這種充足來源于他對地域性歷史文化存在的充分了解和反省,他小說的靈性來自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他對昭通地域歷史文化有認真的野外和案頭的調研,也能用當代性眼光重新審視自己所在地域的歷史文化,以本地經驗和寬廣的文化視角來關注和表現地域性歷史文化,很好地表現了昭通文化的多元混雜性。
他的文學作品“蘊含著豐富的地方文化信息,涉及到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心態文化等諸方面”。他的小說是一幅幅有醇厚泥土味的農村生活風俗畫,他筆下的地方風物的細節采集于現場,對地方性的風水、算命、宗教、喪葬、婚姻等習俗的描寫精彩,如婚俗就寫了“網兜親”“掛角親”“順水流”“水倒流”“倒插門”等,對花臉婆娘收魂,巫師登壇耍馬等風俗進行場景再現,對昭通的集市文化、大清朝封建文化的殘余、農耕經濟也有許多饒有情趣描寫。這些風俗描寫后面是人物的精神世界,如老湯圓要過生日時說:“將城里有點身份的親戚請幾個來坐坐,也給村里面的人看看我老李家在張張船上都有蒿桿,做事說話就會少一些阻力。”又如:“老者在走的時候,是倒退著出門的。出了門,在下院坎的時候,老者還作了兩個揖。”地方風俗文化成為了人物的生存之根、命運之根、文化之根和心靈之根生長的土壤。他筆下的人物共同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地域,血緣關系鏈條對人捆綁很緊,人際關系密集,而地域上的封閉和物質資源的緊缺,讓人際關系更加復雜,人物對權勢的崇拜和向往特別強烈。
他的幾個代表作,都深入到了地方文化風俗,如《魚在枝頭鳥在浪》從陳代理找大地尋龍點穴說起,圍繞著老湯圓在風水寶地上蓋房展開,眾多的人物在緊張的對峙中出場,對鄉間風水迷信、民間信仰和現代社會的法律公正的矛盾,進行了深入描寫。而老湯圓過生日時吹拉彈唱將半個村子搞得笙歌滿地,扭著秧歌唱《十二杯酒》等細節描寫,也保證了小說場景的活靈活現。而“有一首山歌唱的是,山高不過臥佛山,水深不過白龍灘。龍灘邊有一棵古樹,龍灘的水草中有游魚,古樹上有鳥兒,古樹倒映在龍灘里,就給人一種魚在枝頭鳥在浪的感覺。”則是對昭通地方文化趣味的表達。因為迷信,老湯圓要在風水地修房子,也因為迷信,村里面的人將白龍灘水的變渾歸結為老湯圓修房子,就沒有人想過會不會是白龍灘反背龍洞河溝夏二娃的開山炸石,而老湯圓修房子和白龍灘的水變渾沒有因果聯系的真實性,也讓故事的荒誕性引發讀者的思考。
黃代本筆下的人物往往有復雜的主觀性文化存在,人們的精神氣質有地方色彩,他通過人物的宗教信仰、迷信、講究風水等把筆觸深入到人物的主觀世界,他筆下的人物是精神上不自由的人,他們想象的世界和向往的世界常不真實,但是,他們又在用自己的已經打上了虛幻烙印的主觀世界打量自己、周圍、他人、自然、人性。另一方面,他在對傳統文化對人的心理深層結構的影響進行探究時,不動聲色地對民間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進行批判。《入土為安》的劉氈帽,生前子女甚至不能保證他的溫飽,最后以八十高齡自殺死了,默默向世人訴說著不盡哀怨和無奈,但最悲哀的是,他死了也還是不能被世人理解,因為他的喪葬還很風光,村里人認為“劉氈帽這輩子值得了”。
他筆下對昭通豐富的地域性文化的挖掘,讓他的文本具有高度的綜合性,他筆下的人物有政治、經濟、哲學、宗教、倫理多維度地方性特色。他觀察體會到的是一個具體的地方,他自己的存在之地和生存發展之地,這個具體地方的一個人物是一個地方的標本,解剖這一個標本,可能會有更大空間上的普遍性意義,如果形成一定的氣象,也許就會有中國意義和世界意義,如莫言的高密鄉一樣。
從歷史文化的厚重表達來看,黃代本的作品是有一定的宗教、哲學、社會、道德的綜合意義的,文學的意義恰恰在于文學意義的多重性,我們應該把文學的意義同政治的意義區分開,更不能把政治意義強加給文學,但政治意義以外,文學的意義和哲學、社會學、風俗學、美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意義有許多重疊難分的地方,文學和這些學科的最重大的意義區別是文學通過豐富多樣的個性化的人生、人性、人格的描摹來實現他的多重意義。
在他的小說中,陳代理帶著問卦、預言、宿命等日常細節,來到作品中,給小說的審美價值多了一重神秘文化的空間,對神秘文化的現場體驗,是黃代本這部分寫作的基礎,他對民間文化中迷信層面和宗教層面的影響有許多了解,對他小說中的人物來說,神秘文化顯在或隱形地影響著他們的心理和行為,他們受這個神秘世界的左右也在這個世界中尋求精神上的安慰。
黃代本一再在小說中表現逝去的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如小說中的神跡、傳說、符號等文化傳統的表達,給作品增加了文化厚度和神秘的審美感,而“一般用于神秘主義的話,也適用于美學”。比如《空心的大樹》《蒙凇雨》《找水》等小說,就有一種東方的魔幻現實與輪回觀念的雙重神秘氛圍,黃代本小說中宗教感滲透著冷靜清涼的詩意,在神秘氛圍中表達蒼茫博大的人文情懷,常常從命理命相角度,表現一種觀察生命和人性的獨特視角,表達人物的人生觀,他自己人生哲學也常在小說中通過人物表達出來,在文本中灌注的一種大氣、禪意、自然、厚重,同小說中的神秘的氛圍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感。
三、地域主觀精神存在的超現實主義表達
黃代本小說中的人物有精神世界的立體性,人物的感受、觀察和想象的表達齊頭并進,深層次表達人物,給他的人物增加了一種超現實的現實主義特點。
他描寫的蓮花村卑微的底層民眾掙扎生存的小說,總體故事是虛構的,但這些人物的生存環境是原生態的,黃代本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有富有特色的好玩得富有哲學味道的名字,如陳代理、陽桃子、背陰李、金白龍、老湯圓、剮狗匠、桃花、金雀花、何天麻等等,這些人物有漫畫特點,且都是有移花接木的客觀存在原型的。比如在黃代本的多數小說中,陳代理常常作為一個經常串場出現的人物,在真實生活中,陳代理是黃代本隨時可以請來和我們聊天的朋友,他說的話他的神秘的預言和算命推事的技能和小說中一模一樣,讀者不信,那天我也可以約他來和你聊一聊的。
他在小說中將真事隱去,讓假語存在,是一種寫作策略。同時,黃代本小說中這種像“陳代理”這樣的真實人物經常出現的半隱半現手法,對小說中的虛構人物的表現有一種特殊陪襯作用,小說虛構的目的,是為了更為本質地表現內在真實,而他用真實人物來串連虛構人物,是為了剝開現實罩在人物和事件上的重重迷霧。除了陳代理外,黃代本小說中真人真事真名隨處可見,如在《用神》中:“何中貴在學校里是涼風臺文學社的負責人,他的班主任夏玲在學生科當副科長,見蘭花商場來要文字功夫好的,就推薦了何中貴。”這是我的一次出場,我的名字和身份都是真實的,這種小說細節、人物、環境、物象的虛中有實,讓讀者形成獨特的閱讀感受。
在黃代本的小說中,底層人物在從事算命、看風水等活動時,卻有一種宗教追求在其中,這些活動是底層人民抵擋險惡的自然環境和不幸命運的一種緩解藥劑,他在處理這些人物時,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很好地表現了民間文化的神秘神奇的魅力,因“對于民間的一些信仰和宗教活動,如果我們輕率地將一些神奇的東西都認定是迷信,是否過于殘忍和武斷了”。他常常通過一些風俗民情的描述,表現了人在精神產物和宗教儀式面前的批判、選擇、信奉、褒貶,呈現昭通人精神現實的客觀性,也讓小說中呈現哲學色彩和宗教情懷,通過人物追問人生意義。
他的小說是虛構的,但人物的生命軌跡卻不是編造出來的,事件和細節都是在生活中錯位發生過的,是作者成長過程中見到或遇到的。如《太陽出來瓦上霜》中的金白龍這個人物就有他自敘傳的特色,這個人物很有郁達夫小說筆下人物的自我觀察自我表達的特點,那是許多學生進入社會初期都會有的共同的經歷,他把那段歲月自然呈現了出來,用他的話說就是:我不過是把剛剛踏入社會時,別人如何整我,我感受如何,怎樣行動寫了下來。白金龍走入社會的迷茫、困窘、痛苦,對現實的失望感挫折感,和環境的不融洽等等,也是曾經屬于大家。他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經驗,從感覺層面,從自己所見所聞層面,寫出人的感情的動作性外現,用文學去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黃代本筆下的富貴、荷花、丁心蘭、秋生等互相關聯的人物個性是豐滿的,也是復雜立體的,這些人沒有全好的人,也沒有全壞的人,都是些為了生存為了發展,被命運推動,被欲望推動,而產生了或者荒誕或者悲慘故事的人,他們的分裂的生命多厄的命運和時代的喧囂混亂有關,也和自身靈魂的善與惡的斗爭有關。有的人物在社會中陷入了嚴重的生存和道德困境,有關背陰李的系列小說,表現了年輕人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的撕裂感,小說敘述中反諷語氣下悲涼彌漫。《沼澤》中二秋夢想著女兒通過讀書成為像金白龍一樣的人,為了籌集女兒上大學的學費,他不惜借高利貸,導致傾家蕩產,但是女兒中專畢業后回到了鄉村,在女兒的婚事上,二秋也努力抗爭,可女兒最終還是嫁給了他當初極力反對蘋果狀元劉大河,女兒未能通過讀書改變命運,而是從最初的起點開始經過一番掙扎艱辛最終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上,現實違背了人的理想,陷入了一個不能擺脫命運的怪圈,陷入一個越陷越深的沼澤。《丁心蘭脫貧》敘述丁心蘭靠生了五個孩子而一步步蓋起大瓦房,一步步脫貧。《荷花荷花》敘述供養不起孩子上學的家庭,在壞人的誘惑威逼下,成了繁華大都市那些罪惡的靈魂的性工具。
黃代本以一種寬容和理解的姿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貼緊了人物進行寫作”,而且是貼緊了人物的自然生活空間來寫,但是卻又深入到了人物的精神空間。在文學作品中一定要有人的精神軌跡,要有對人類普遍命運的關注,要有形而上的探索,人不能在空間中孤立,也不能在時間中孤立,但是,我們現實的空間時間常常讓人的靈魂難以居留,而神圣的東西最常讓人體會虛無,面對生命中的黑暗面,需要提起勇氣,從虛無中超脫,完成人生升華。
他貼著人物寫作,他在展示人物的無能、卑微、寒磣、無聊和陰暗中,文字充滿了悲憫色彩,人物被隱秘痛感左右,人物的文化處境艱難,人物有精神傳統的復雜性,讓人物產生生命力堅韌而強大的效果,源于他和小說中無奈掙扎的人物共悲歡。小說中人物的心理體驗,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體驗和發自內心的生命感悟,對人物命運的深層次關注,讓他能夠借助文字抵達人物心靈的根部,
他的寫作是樸素的,是平易近人的生存狀態,是真實生活中人的悲歡離合本真呈現。他的地域性寫作,讓人物的生命時間和地理交融,更加深入具體細致的切入人性和生命的各個切面。從一種意義上說,他的小說也是他自己的一部隱秘的成長史,他用自己的心靈經歷過作品中人物成長的痛楚、屈辱和傷害,他是疼痛著一顆心,寫自己的人物,他對人物的生存狀態、生存環境和人物心理行為有非常準確的或者黑或者灰或者帶點彩色的把握。
四、地域性語言存在的富有韻味的表達
黃代本小說中對方言給予了過濾性的積極的創造性的使用,小說語言表現出方言和雅語結合的特點。黃代本的古文功底和方言功底都非常厚實,讓方言和古雅的文言同時出現在小說文本中,語言風格在雅俗之間游刃有余交替使用,讓小說中的雅人說雅語,讓小說中的俗人話方言,保證了他寫作語言的唯一性和真實性。
昭通方言作為一種地域性的存在,一種現實中群眾還在使用的語言,在黃代本的小說中,體現出來是民間語言的豐富和博大。他小說中的人物語言,大量地使用鮮活的真實的昭通人的家常話,我們讀他的小說,感受到昭通民間語言的詼諧幽默中特有的粗獷機智,昭通民間語言中自然存在的夸張、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形象生動,動作性強,讀來親切有趣,如形容人“灰嘴灰臉”“賊眉鼠眼”“蝦腰蝦胯”“雞胸雀腹”“一臉豬相,心里明亮”,說人英俊是“特別是鼻子長得好,就像一座墳一樣,不像是壞人”。說一個人高傲是“一塊死人臉,面無表情,腦殼抬多高,就像大山包的雁鵝一樣,很不好接近”。
他小說中的民間語言,有三川半的特殊風味,有云橫霧鎖的連綿烏蒙山的味道,有酸甜苦辣打翻了五味瓶的人間煙火味道,如“喜鵲老鴉含來么,還要張張嘴嘛,怎么盡想吃清凈食。”“說到粑粑要面來做,要不然就是空口講空話了。”“這個人成了火塘邊的藥渣了。”“恨不得將這人燒成灰來點蕎子”“心急吃不得熱稀飯,他巴不得一耳巴打進嘴里去。”讀這些富有生活氣息的語言,可以充分的體會到昭通民間語言在宣泄、自嘲、幽默等上的出色表現力。
他的小說人物也常常享有語言上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感,有時甚至上升為語言的暴力和語言的困境,如爆粗口、說臟話,不多舉例,這種語言也使得他筆下的人物更為鮮活、肉感、生動,表現出一種野性野蠻野趣,這些方言是底層人內心幽暗的真實表達,而黃代本通過這些民眾語言,對其生存狀態進行獨特的描寫。
“反正喊死了,不要你負責,見人家在抬東西,就過去搭個手,特別是要笑,好笑不好笑的都要笑,將臉笑成一朵菊花,像彌勒佛一樣。”“有粉要搽在臉上,不要搽在屁股上。”他小說中人物的語言,常常讓人讀之忍俊不禁,“靠兄弟如紙上談兵,靠父母如畫餅充饑。用形象一點的話來說,就是何中順伸手就拿到的東西,何中貴跳起來都還夠不著。”“當官就像螢火蟲爬尿罐,爬上去么就高高在上,爬不上去落下來落在尿罐里么就又臟又臭。”“半夜起來做法事,不要裝心頭不明白,說得脫,走得脫,說不脫,就拌著腳。”“單位是一棵爬滿了猴子的大樹,從高處往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臉,從低處向上看,看到的就全是屁股。”類似的機趣幽默的假語村言,在他作品中比比撿拾,表現出民間人物的幽默達觀,民間存在的一種樸實的人生智慧。這些語言的使用,更能揭示事態,用故事中人物的語言吸引住讀者,是小說的一個基本功夫,也更為切近生活。
而這樣的語言“一顆草有一滴露水,大樹腳的酸楊梅沒有一點陽光,時令到了,他都有紅起來的時候。”“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河里來的江里去,江里來的水里去。”“人是三節草,不知哪節好,好還是不好,一直要看到老。”讀來還很有詩意,“語言、生命、詩本是三位一體的東西,真正的語言是詩的語言,真正的詩性是人的本性。”民間語言的豐富后面是生活的豐富,這些民間語言的詩意后記是生命的感悟,同時,民間語言后面,有豐富的地方文化印跡。
黃代本小說中的方言使用地道,而且不影響閱讀。《山花》在最后定稿時,將黃代本小說中自己刪除了的方言一一恢復,說明他小說中的昭通方言,是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的。我閱讀黃代本作品,是沒有閱讀難度的,而且經常因為感受到昭通方言的幽默生動,而得到閱讀的快感。但是,我有時還是遇到了問題,比如在《用神》中何中順美麗的妻子叫楊潴留,按照我的推測:這個人物的名字一定有一定隱喻性,但是,我不知道“潴留”這個名字的意思,又是如何和女主人公的美麗聯系起來?后來我問黃老師,他告訴我:潴留是一種非常機靈的小動物,類似松鼠,十分可愛。這就印證了我的推測,我想,以后這樣的地域性方言詞匯,如果估計普通讀者有理解困難,可以加個注釋,這樣就可以解決外省讀者的閱讀問題,有利于作品在省外刊物的發表。
【注釋】
[1]周明全.西部文字西部之魂.太陽出來瓦上霜[M]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p249.
[2]丁帆.二十世紀中國地域文化小說簡論[J]學術月刊.1997年9期.p97.
[3]呂崇齡.散文集《我的河山》的地方文化特色[J]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12月.p44-49.
[4]喬治桑塔耶那.美感[M]中國社科出版社.1982年.p75.
[5]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N].2004年3月12日.
[6]魯樞元.超越語言[M].中國社科出版社.1990. p88.
(夏玲系昭通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曾子芙系首都師范大學在讀學生)
責任編輯:萬吉星
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昭通文學的地域性”階段性成果。(2014Y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