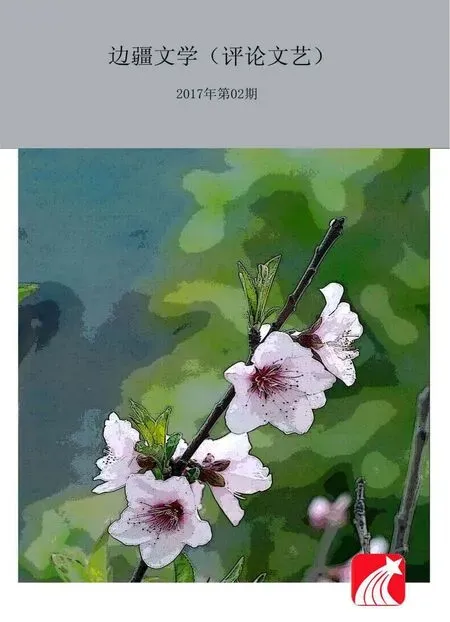金沙走筆,故土情深
——評馬淑吉散文
黃 玲
邊疆閱讀
金沙走筆,故土情深——評馬淑吉散文
黃 玲
·主持人語·
服務基層是本欄目的一項工作任務,關注基層的文學評論工作者,關注基層的文學寫作者。馬淑吉、張學康、段海珍是楚雄的寫作者,以前關注較多的是段海珍,也發表過評論張學康散文的文章,以馬淑吉的文學作品作為評論對象還是第一次。南馬長期關注紅河州的文學發展整體研究,對少數民族文學很有心得,這篇對彌勒詩人黃光平的部分詩作進行點評,是他在對紅河州文學進行宏觀研究之后的個案微觀研究,注重文學的地域性和鄉土特色。基層的文學經常在語言特色、敘事風格、表現手段等方面有別樣的味道。(楊林)
出生于彝州大姚縣灣碧傣族傈僳族鄉的馬淑吉,對金沙江畔的故鄉始終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她近期出版的兩部散文集的書名,都深深地打上了金沙江的烙印。一本是《金沙人家》,一本是《金沙傈僳》,全部取材于故鄉的人和事,抒發著作者對故鄉的濃濃情意。
《金沙人家》的副標題是“沿金沙江‘環百草嶺’區域風情散記”,《金沙傈僳》從書名上就透露了這部集子的選材范圍,是以金沙江沿岸傈僳族的人文風貌為內容,還配以精美的攝影。兩部作品都是以金沙江的地理區域為中心,看似范圍比較小,但深入閱讀會發現小的視角后面隱藏著大的情懷。作家的視野與文筆,全都緊緊扣住金沙江沿岸的民族風情和各民族的現實發展而展開,和那些單純的觀光者心態有很大區別。要解讀這兩部散文集,就得對寫作者的文化身份、文學追求進行一番梳理,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其散文的內在意蘊。
一、基層干部和文化行吟者的雙重視角
在閱讀散文作品時,應該看到作者的身份對散文選材的影響和制約。
不同的寫作者,面對生活時的角度與選擇是不相同的。一名外來的觀光者,他的目光更容易被陌生的風景和民俗所吸引,產生審美的沖動。他的作品可能會體現出漫游的特色,和走馬觀花式的新奇感。而一名長期生活在民族地區的寫作者,對他來說故鄉的風景和民俗已經化在血液里,成為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寫作應該是沉入式的,能從生活中選擇最有感受、最能體現情感的內容進入散文。這樣的作品可能沒有外來者的新奇感,但卻會有一種外來者所沒有的深入與厚重。這是植根于生活土壤里,充滿泥土氣息的寫作。
讀馬淑吉的散文,就有后一種感受。
馬淑吉的身份比較明確,她首先是一名國家公務員,一名長期在民族地區工作的基層干部。同時又是一名熱愛文學的寫作者,可以用文字表現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收獲與思考。其深厚的生活底子,會讓很多作家羨慕。從書的扉頁的簡介中可以了解到她的工作簡歷:七十年代出生于彝州大姚灣碧,金沙江畔一個傣族、傈僳族雜居的地方。參加工作后,從事過民政工作,擔任過副鎮長,鄉黨委副書記、鄉長、縣廣電局黨委書記、現任縣文聯主席。這樣的人生歷程,完全可以積累下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經歷,也能具備一定的寫作高度。如她自己所說:“對彝州這方水土的豐富地域文化有著濃厚的熱愛之情。”這不是客套話或者矯飾之語,而是發自內心真誠的抒懷。
這樣的人生經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馬淑吉散文選材上的獨特性。如青年批評家楊榮昌在為《金沙人家》所作的“序”中所概括的:“作為一名基層干部,一名對家鄉本土文化有著強烈熱愛的文化行吟者,馬淑吉的文字中充滿了對現實民生的傾情關注。”和一些專注于審美追求的散文不同之處正在于此,馬淑吉的散文中隨時可以體會她作為一名基層干部的視角和情懷。
《金沙人家》由八章構成,每一章都有三個層面的內容互相交織。一是大姚豐富的自然資源的展示,二是多姿多彩的民間文化資源的匯聚,三是現實生活中各民族群眾的勞動創造與精神追求。三者之間互為表里,體現了馬淑吉散文選材上的獨特性和豐富性。
第一章“鐵鎖印象”,是對一個基層鄉鎮民俗風情和現實生活的敘寫。需要注意的是,馬淑吉曾經擔任過鐵鎖鄉的黨委副書記、鄉長的職務。她對鐵鎖的關注和一般的觀光者自然有很大的區別。首先作為一名在鐵鎖工作生活過的干部,她的散文中肯定會有一些對鐵鎖自然風光和民俗風情的描寫介紹,比如壯觀的梯田,火紅的攀枝花,還有流于民間的各種傳說,都為鐵鎖這個偏遠的鄉鎮增添了異彩。從字里行間能感受到作者對這塊土地的熟悉、親切,還有一份真摯的情懷。她不是這里的過客,而是一名與山水結緣的文化行吟者。但是,她同時還是這塊土地的領導者,是上級方針政策的執行者。所以從一些篇幅中可以體會到這一視角對馬淑吉散文選材的影響。她在《2010年那場干旱》中記錄了干旱對民生的影響,充滿焦慮和渴求。甚至對那一年的每一場雨到來時的時間、雨量、心情都有詳細描寫,既傳達了一位基層領導的責任感,也能體會到一位寫作者的憂思。她還用文字記錄著鐵鎖的建設與變化,《漁泡江畔燈火明》,就是對建設鐵川橋水電站的側記,并對鐵鎖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記。在《風情鐵鎖》中,她對鐵鎖的歷史、民情、風物特產都有細致的描述。還用文字記錄下了自己對這方土地的一片真摯情感:“一點一點了解鐵鎖,走進鐵鎖,它的每一點美麗都令我欣賞,每一點變化都令我興奮鼓舞。與鐵鎖血脈相連的不解之緣,讓我樸素的生命永遠不能與它分離。”
在馬淑吉的散文中,鐵鎖只是一個點,也是她人生中的一個驛站。但她卻投入了深深的情感,記錄下自己與鐵鎖的一份情緣。這些文字雖然不夠精致,但其中洋溢的情懷和樸素的敘事,卻仍然能打動讀者的心。
從馬淑吉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因為工作和職務的變動,她取材的目光和視野也在發生著變化。所以在《金沙人家》這部集子中,還有這樣一些內容:金沙人家、水乳灣碧、咪依魯的故鄉、中國核桃之鄉、祭孔圣地等等,差不多囊括了大姚重要的文化現象。所以楊榮昌在本書的“序”中評價說:她“從立體型、多維度的層次上勾勒了‘文化大姚’的風采”。
大姚的文化特色很多,比如“中國核桃之鄉”、“中國彝劇的誕生地”,資源也非常豐富,素有“三鄉露銅”“五井噴鹽”“文化名邦”等美稱。這里還有世界上現存體積最大的孔子銅像。這些特色在《金沙人家》中都有涉獵和表現,馬淑吉以“文化行吟者”的角度,用文字細致描繪著這些人文景觀,為外界了解認識大姚文化創造了很好的文本。
長期基層工作的實踐,為她深入認識了解大姚提供了條件,文化行吟者的視角則為她的散文增添了豐富的內涵。在另一部散文集《金沙傈僳》中,她把視角聚焦于彝州境內的傈僳族,對他們的民族文化、現實生活進行忠實記錄。既寫出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對他們生存環境的艱辛有深入理解。閱讀這些作品,能感受到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文情懷。在馬淑吉這樣的寫作者這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早已經是一種自覺的行動。所以她的散文既是長期深入生活的積累與收獲,也是接地氣式的寫作,其精神和態度都值得提倡。
二、對故鄉山水民情的深情書寫
從馬淑吉的經歷和文字中都可以體會到,她是一名金沙水養育的彝家女兒,對生養她的土地有著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她才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提筆寫下記錄故鄉變遷的文字,還攝下無數記錄故鄉發展進步的圖片。
熱愛故鄉,并歌頌贊美它,是很多游子在文學中書寫的永恒主題。但是多數人取的是離鄉之后的回望視角,是距離產生美的“思鄉”與“懷鄉”。馬淑吉的散文則不同,她是始終站在故鄉的土地上,與之保持著水乳交融的關系,以一腔熱情為它的發展而謳歌。所以她把《金沙人家》的第三章命名為“水乳灣碧”,就是在暗喻自己和灣碧之間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這里是她的出生之地,也是她身上另一半傣族血統的發源地。但她取的寫作視點不是個人情感式的表達,還是從文化行吟者的角度側重對灣碧的風土人情和民族文化內涵的表現。比如傣族的“窩巴節”“金沙傣”“金沙傈僳”的獨特習俗,都從馬淑吉的筆端流淌出來,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受。
雖然她努力把視野投向文化和民族,個人的情感表達不是那么突出。但是認真閱讀作品還是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和個體生命成長有關系的片斷,它們散落在作品中,猶如斷線的珍珠,可以串起作者成長的痕跡,找到她和故鄉之間內在的聯系。在《炳海渡口》一文中,馬淑吉以略帶憂傷的筆調寫到外婆,也寫到自己的成長。從中可以感受到金沙江的自然環境和文化風俗,是她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背景。也是她為什么如此執著地以故鄉的山水人情作為寫作對象的一個注腳。
在《村頭有棵萬年青》中,馬淑吉穿上傣族服裝,很快又融入到傣族文化的文化氛圍中去。她的血液中原本就有彝族和傣族兩種血緣,兩個民族的文化在她身上融合得如此奇妙與和諧。在《水巴崖》中她對家族祖上的歷史有比較細致的敘述,從“老祖”打土匪的光榮歷史中也可以窺探到一個家族曾經的艱辛與曲折。
但類似的個人成長史和家庭歷史,在馬淑吉的散文中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穿插散見于其散文篇章中。她更多的筆力還是放在對故鄉文化和民俗的描寫中。或者說她更集中表現的是大姚這個故鄉的人和事,而不僅僅局限于灣碧這個出生之地的小故鄉。這是一種開闊的視野,也體現了其散文意蘊的深度。
《金沙人家》第四章“桂花飄香”,第五章“咪依魯的故鄉”,集中對彝族地區的自然環境和民俗文化進行了深入表現。百草嶺的絢麗風光,和彝山文化的豐富多彩,體現了作者對故鄉的一往情深。
《金沙傈僳》是一部獨特的作品集,作者在書的“前言”中透露了寫作的動因:“隨著水電站建設移民搬遷和‘現代化’洪流滔滔,一些民族文化遺產瀕臨消失”,所以這部作品的寫作意圖是“為加強金沙江岸傈僳族文化的挖掘、傳承和保護,同時促進金沙江流域文化旅游發展”。為了寫作這部作品,馬淑吉調動了自己多年的生活積累,希望能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呈現給讀者一個個古樸、厚重的傈僳村莊,讓古老的民族文化魅力得到展示。在《一灣碧水》《一方山水》《江外姜驛》《江有浣女》等篇章中,濃郁的傈僳族生活撲面而來。生存條件的艱辛和民族精神的頑強,都能給人深深的感染。
就如馬淑吉在“后記”中所總結的 :“我感受到傈僳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傈僳族人的堅毅、質樸、樂觀。他們的頑強和精神感染了我,連我也頑強起來 ,有一種力量,有一種精神,鼓舞我完成了這本書稿。”和那些依靠觀光采訪獲得素材的寫作相比,這種與生活本身建立起密切聯系,從寫作對象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的寫作,更具有一種深沉的內涵。
這兩部散文集的另一個特色是馬淑吉充分利用了自己喜愛攝影的特長,采用了圖文相配的方式,通過攝影和文字的結合,生動形象地展現出大姚的文化風采。各民族地區的風情和多姿的文化特色,在鏡頭和文字的雙重作用下煥發出全新的光彩。這是一個大姚女兒對故鄉的深情回報。
三、馬淑吉散文的優勢和局限
馬淑吉的散文已經體現了她所具備的優勢,那就是扎根于生活,與故鄉的土地和人民保持水乳交融的關系,用一顆多情的心靈擁抱世界。自然會獲得豐富的寫作資源,也能讓情感之渠永遠流淌出滾滾碧波。
散文是敘事的藝術,也是抒情的藝術,它對情感的追求是自然、真誠和樸素。這點在馬淑吉的散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她對故鄉的情感是建立在相生相依,休戚與共的基礎之上,和山水草木有天然的親近感。她是大山的女兒,也是金沙江養育的女兒,所以她的文字自然純樸,較少修飾,寫人敘事都是以親切的語氣娓娓道來,有如和朋友交談一般,毫無矯飾之感,這是一種難得的散文風格。
她散文中的抒情,不追求氣勢的強烈和情感的沖擊,而是如溪流一般自然純靜,又能帶給人清風撲面的質樸之感。似乎能讓人體會到職業和性別對寫作的潛在影響。比如在《村頭有棵萬年青》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對村頭萬年青進行描寫:
“遠遠就看見了村頭那棵萬年青,風風雨雨中依然枝繁葉茂地挺立著。從記事起,這棵樹就這么大,年復一年,三十多年過去了,它依然如故。村里的老人說,這棵樹叫萬年青,這種樹長得慢,卻長壽。”
這段文字里,作者的情感是隱忍而含蓄的。下面這段文字隨著回鄉時間的增長,對景物和往事回味的加深,情感才開始慢慢升溫:
“在這從小長大的家園里逛來逛去,摘食著從小就喜歡的吃的紅心果。思緒飛揚中,眼前,我們家族姐妹分明還在那塊大滑石板上‘梭耥耙’,分明還在那棵洋茄樹后面躲迷藏……”
或許是因為工作和職業的關系,馬淑吉的散文涉及個人情感的內容比較少,情感表達也比較節制。而寫到一些和工作有關系的內容,或者描寫民族生活和節日的氣氛時,她的語言才會張揚起來,體現出個性和風采。比如《窩巴節》這篇描寫金江傣族節日的作品中,對傣族人過節的氣氛就營造得很生動,場面和細節的描寫都能體會到作者主體情思的滲透,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象腳鼓鏗鏘有力,葫蘆絲婉轉悠揚,小卜炒股的火草筒裙衣袂飄飄……歡快的舞曲鼓舞了情緒,大家開始互灑吉祥水,互道祝福的心愿。人們提著桶,端著盆自由追逐,肆意潑灑。水花四濺,笑聲飛揚,人頭攢動,人們盡情享受著這場民族的盛宴。”
這個場面的歡樂是放松而盡情盡性的,作者的情感也在場景的生動描寫中得到了有效的抒發和傾泄。作為一位民族干部,是否可以說她的抒情方式也已經染上了職業的特點,既具備一種大氣的姿態,也保持著一定的理性和節制。適合寫群體性的快樂,不擅長寫兒女情長。
所以我注意到馬淑吉的一些散文中其實還隱藏著許多線索和秘密,可以成為下一篇作品的開掘內容。比如《江有浣女》中那位80歲傈僳婆婆的愛情悲劇,《愛藥》中的孤兒美女,那些行走途中遇到的人物,因為作者表現視角的原因他們只是一些帶著故事的匆匆過客,引而未發。如果認真深入進去,或許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作者今后的作品中成為主角。
任何人的寫作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以客觀的態度對創作中的問題和局限進行分析研究,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目的是為了今后更好地發展進步,寫出更有特色的作品,所以最后要對馬淑吉散文中的某些存在問題進行評說。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才是真正科學的批評態度。
第一,《金沙人家》作為散文集,文體屬性不統一。其中甚至收入了幾首詩,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它作為一部集子單純的文體特色,這是出版編輯時的不嚴謹。另外,從具體作品上看,藝術水平的高低也有不統一之感。雖然大部分作品藝術性比較強,審美特性比較突出,寫景抒情能引人入勝。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從文體上看是可疑的,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散文,而是把新聞通訊或者工作報告參入其中。比如《金沙人家》第五章的“中國核桃之鄉”,在整部集子中就顯得不太協調。第八章“金馬碧雞的故鄉”中的一些篇幅也有同感。其中的《三岔河扶貧整鄉推進繪藍圖》,更像一份工作報告,和散文似乎沒有什么關系。
第二,到目前為止,馬淑吉已經發表了不少文學作品,還出版了好幾部作品集,又擔任著大姚縣文聯的領導工作。所以我認為她已經到了可以對自己的創作進行階段性總結的時候,以期在寫作上能更上一層樓。比如散文的文體意識需要明確,散文的文學性需要提升,主題可以考慮從時政的層面向人情人性的縱深有所傾斜,進行比較深度的開掘。一個有著如此深厚的生活積累,又對文學懷有深愛的寫作者,只要善于總結,揚長避短,相信她一定能寫出更多優秀的散文作品。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