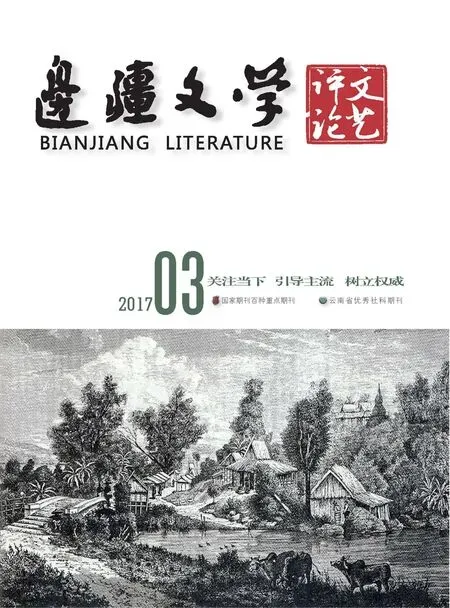人肉的兩種吃法
——魯迅與馬克·吐溫筆下的“吃人”意象比較
李 英
經典重讀
人肉的兩種吃法——魯迅與馬克·吐溫筆下的“吃人”意象比較
李 英
·主持人語·
李英的文章《人肉的兩種吃法——魯迅與馬克·吐溫筆下的“吃人”意象比較》,通過對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與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比較分析,提出了兩個文本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文章認為:“魯迅先生與馬克·吐溫就‘吃人’這一主題,達成了某種跨越時空的共識。又因為各自生活的具體社會環境不同,他們在‘吃人’的未來趨勢這一問題上,分道揚鑣。”文章觀點鮮明,說理性強,分析透徹,是一篇好文章。
《野草》是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也是一部很難讀懂的名著。青年學子任瑞卿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圍繞《野草》文本從體認與超越兩個方面,分析魯迅的超越虛無之路。論文思路清晰,層次分明,重點突出,對《野草》文本的闡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追風箏的人》是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一部小說,2003年出版后受到讀者的喜愛,成為美國2005年排名第三的暢銷書。劉永松的文章認為:“阿米爾的贖罪的行為其實也就是凈化靈魂,不斷和人性弱點做斗爭的過程,通過斗爭,最后達到一種凈化靈魂的效果。”文章立論較好,如果第二部分“英雄與虛偽”的分析再厚實一些,整篇論文就更完備、更理想。(李騫)
一
馬克·吐溫是我最喜愛的美國作家之一,幾乎讀過他的所有作品,尤其是他的中短篇小說,印象十分深刻。如今重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的《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時,毫無疑問,我真的喜歡。最先吸引我的是其中一篇標題叫《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小說,特別是標題上的“吃人”二字。
我的本科畢業論文跟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有關。眾所周知,《狂人日記》是一篇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的小說,或者說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據我能查閱到的資料,《狂人日記》受到過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的影響,魯迅先生曾這樣說過:“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此后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我找不到《狂人日記》與《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之間有任何師承關系的直接證據,但比較這兩個文本卻發現,它們竟然驚人地相似。
二
首先是它們的雙重敘事。
值得一提的是,“狂人”所寫的“日記”固然是《狂人日記》最核心的部分,但“狂人日記”之前的那段文言文的小序在敘事的層面上卻是至關重要的,它才是整個小說的開篇,不容忽視。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這段小序至少告訴我們,《狂人日記》的敘事者并不是“狂人”,而是這個“我”,“狂人”的日記是“我”引用的,“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
再來看《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開頭:
不久前我去圣路易斯觀光。西行途中,在印第安納州的特雷霍特換車后,一位紳士,樣子溫厚慈祥,年紀大約有四十五歲,也許是五十歲,在一個小站上車,然后在我身邊坐下了。我們談笑風生地山南海北聊了大約一小時……
……
我說我不會打岔,于是他講述了以下這件離奇的驚險遭遇。他說的時候,一會兒很激動,一會兒很愁郁,但始終帶有感情,顯得那么一本正經。
不難看出,這段開篇跟《狂人日記》中的文言文小序具有相同的功能。兩個文本的第一重敘事主體并不是“狂人”和“紳士”,而是這兩個“我”。在《狂人日記》中,“我”直接引用“狂人”寫的日記;在《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我直接引用了“紳士”講的故事。如果說有什么區別的話,前者引用的是文字,后者引用的是語言。小說開好頭之后,就進入了正文。《狂人日記》的正文自然是“狂人日記”,《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正文,“我”將它命名為“陌生人講的故事”。
說到“直接引用”這個詞,其實就已經說明了兩個文本的另一相似之處:“狂人日記”與“陌生人講的故事”,采用的也都是第一人稱,都是通過另一個“我”來講述的,出現了第二重敘事者。當然,這種敘事手法在今天看來不足為奇,很多作家都用過,就連我先生在寫小說時也常用,大家比較熟悉的當屬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小說一開頭,“我”在收集民間故事時邂逅了正在犁田的福貴,然后聽福貴來講述他們一家的種種遭遇,用的都是第一人稱。但是,這兩個發表時間相隔了51年的文本,在擁有了相同的形式之余,又指向同一個主題——吃人,竊以為,不可不察也。
三
在討論《狂人日記》與《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在內容上的相似處之前,有必要對它們的第二重敘事者進行比較。無獨有偶,他們都是精神病患者。《狂人日記》中,“狂人”患的“蓋‘迫害狂’(應該是被迫害癥或受迫害狂——筆者注)之類”;《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紳士”患的是“偏執狂”。不同之處僅在于,《狂人日記》開篇就交待了“狂人”的身份,而《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則將“紳士”的身份之謎放在了小說的結尾處由列車員道出。
現在,我們來對比兩個精神病人的講述,其內容都是“吃人”。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文本都沒有涉及到“吃人”這件事本身,都沒有描寫如何將一個人開腸破肚、如何烹飪、如何咀嚼,等等,兩個精神病人所講述的內容,全都發生在“吃人”之前與之后,對“吃人”的細節都絕口不提。
事實上,“吃人”前后的故事遠比“吃人”這個動作本身精彩,正是它們提升了小說的審美高度。在《狂人日記》中,“我”對趙貴翁與趙家的狗的種種揣摩與仇視、“我”關于“狼子村”佃戶吃惡人的傳聞的“研究”、“我”對“郎中”的無聲反抗、“我”與“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的對話、“我”對“大哥”的“勸轉”,等等,大都是“狂人”的意識流,“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陌生人講的故事”要完整得多,還交待了吃人的原因——火車被暴風雪所困,二十四位乘客在求救與自救無果后,不得已而為之,為了以示公正,他們召開選舉會議,經過提名、投票表決等一系列看似非常正規合法的方式來選舉出“哪一位為其余的人提供食糧而犧牲”,而選舉委員會又分為兩派,兩派的意見常常起沖突,最后綜合所有選民的利益,以實際票數的多寡為準繩來確定最后人選。
顯然,以幽默、諷刺與批判見長的馬克·吐溫,不可能在文本中單純地對人性進行拷問。跟《狂人日記》一樣,《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也是在針砭時弊,也有明顯的抨擊對象。兩個文本,都寫“吃人”,卻都不寫如何“吃”這個動作,而是將具體的“吃人”升華為抽象的“吃人”。這是它們在內容與主旨上的相似之處。如果說《狂人日記》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那么,《火車上人吃人紀聞》揭露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讓“吃人”合法化,或者說它通過這個荒誕的“吃人”故事,表達出對美國兩個政黨輪流執政的合理性的懷疑。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兩位作家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度里,但二者的批判精神是相同的。
從具體的“吃人”,到抽象的“吃人”,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飛躍呢?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文本再一次不謀而合。魯迅先生與馬克·吐溫,他們都找到了隱喻。這些種隱喻的符號,在兩個文本中都很明顯。比如《狂人日記》中的趙貴翁、趙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尤其是“趙”,魯迅先生似乎特別鐘愛這一符號,在《阿Q正傳》就有趙莊、趙太爺,趙太爺罵阿Q時說:“你也配姓趙?”《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這種符號的數量雖然少一些,但也足夠醒目,如:選舉會議以及會議中的兩個派別。
四
當然,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同樣是“吃人”,但兩個文本中吃人者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在《狂人日記》中,吃人的人“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而在《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吃人者要坦然得多,他們甚至還可以在事后對比不同人的肉在味道上的差別:“我可以說一句,再沒誰比哈里斯更配我的胃口,再沒誰比他更使我感到滿意了。梅克西很好,雖然香料放得太濃了些;但是講到營養豐富,肌理細膩,我還是更喜歡哈里斯。梅克西……他太老了!”
此外,《狂人日記》與《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之間還有一個相似之處與一個不同之處,都體現在對主人公的處理上。
先說相似點。兩個文本都有大量的留白,供讀者去思索,就連留白的手法都很相似——均是跳入文本中的敘事者所為,原因或主觀或客觀。在《狂人日記》中,開篇的文言文小序已經說得很清楚,“狂人”留下的日記共有兩本,而“我”只“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那么,“狂人”從犯病到“赴某地候補”,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心理轉變?我們不得而知。在《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由于火車到站,“紳士”下車,不得不提前結束講述,“要不是剛才已經到了站,非下車不可,這會兒他會把那一群人都吃得一個不留下”,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剩下的人是如何被吃的呢?尤其是在只剩下主席、秘書、提名委員會成員與膳食主管的時候,他們都是權力的擁有者,該如何選舉出“為其余的人提供食糧而犧牲”的人呢?我們同樣不得而知。
事實上,不同點與相似點之間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都是為了主人公兼第二重敘事者這個人物的命運服務的。之前說過,《狂人日記》在開篇就交待了“狂人”的身份,而在《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中“紳士”“曾經是國會會員”則在結尾時才道明;《狂人日記》一開篇就說明了“狂人”有病,而《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則在倒數第二自然段才說“紳士”“變成偏執狂”。最應該注意的,也正是此處要說的不同之處,“狂人”病好之后,被他深惡痛絕的封建禮教招安,抑或他自己主動擁抱封建禮教,“赴某地候補”;而“紳士”原本是國會會員,犯病后不再是了。這兩人不同的結局,似乎可以反映出魯迅先生和馬克·吐溫在創作時的內心世界。魯迅先生對他抨擊的那種社會制度充滿了絕望,就連“狂人”這樣的清醒人士也因某種我們不知道的原因加入了他們;馬克·吐溫則對他所諷刺的社會制度抱有希望,吃人者或臆想吃人者終將從國會除名。據我所知,馬克·吐溫對資本主義制度不再樂觀,那是1876年至1884年之間的事,1884年,他出版了他的重要名著《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這是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的重要轉折點,而魯迅先生對封建制度的絕望,則是在他父親去世時就已經有了萌芽,從不相信中醫開始。
五
《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發表于1867年,《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相差51年。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它們之間有某種師承關系,我們也無法知道魯迅先生在創作《狂人日記》之前是否參照、借鑒過《火車上人吃人紀聞》。而它們卻有著如此多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說,上文中提到的不同之處,其實都是用于烘托它們的相似之處。因此,我只能說,魯迅先生與馬克·吐溫就“吃人”這一主題,達成了某種跨越時空的共識。又因為各自生活的具體社會環境不同,他們在“吃人”的未來趨勢這一問題上,分道揚鑣。作為一名普通讀者,我更愿意接受《火車上人吃人紀聞》,不僅因為它沒有設置太多閱讀障礙,讀起來相對輕松,還因為它讓人看到了希望;而《狂人日記》太過沉重,每次閱讀,都給人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負重前行之感。
【注釋】
[1] 見《〈吶喊〉自序》
[2] 見《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3] 馬克·吐溫:《火車上人吃人紀聞》,見《馬克·吐溫中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4] 參見《阿Q正傳》
[5] 參見張友松:《〈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譯序》,[美]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6] 參見魯迅:《父親的病》
(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國際語言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