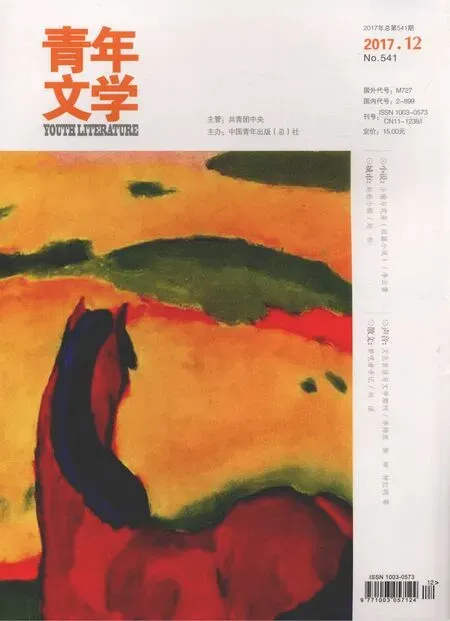小說的制幻與祛幻
⊙ 文 / 趙 松
小說的制幻與祛幻
⊙ 文 / 趙 松
一
我曾夢到過,地球是金屬的、中空的。人類生存在表面,而里面則是不計其數的老鼠,它們中的一小部分總是會在午夜里從遍及全球的無數狹小洞口里突然爬出來,瞬間引發人們的強烈恐慌和最殘酷的反擊,即使不能將它們全都消滅,至少也是驅趕回幽暗的地下……對于那些執著地用爪子扒住洞沿不放的強壯老鼠,人們毫不客氣地用各種冷兵器斬斷它們的爪子,甚至直接一腳踩斷。它們像隕石似的紛紛墜落,尖叫著,然后撞到大地深處,不斷發出長久的回響,這些回響混合在一起,就會像鐘聲一樣回蕩不已,這回蕩是越來越強烈的。我看見,人們都靜默立于地面,像石化的微小顆粒,而整個地球都在鐘聲回蕩的過程中輕微顫動著。似乎人們都清楚,這樣靜穆的某種儀式般的時刻是異常短暫的,我甚至聽到有人悄悄告訴我,過不了多久,老鼠們就會卷土重來,再一次從遍布地面的洞口中涌現。
這個夢即將醒來時,我注視著宇宙中飄浮的地球,它是黑的,盡管距離已開始變遠,可仍舊能清晰地聽到鐘聲在回蕩,只是隨著距離越來越遠,這聲音也漸漸變得微不足道了,直到沉寂。我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視角發生過幾次轉變,從宏觀的,到微觀的,最后再回到宏觀的。唯一不變的,是恐慌。躺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睜著眼睛,什么都看不到。逐漸意識到自己已不在夢里之后,想到客廳里至今還藏著一只老鼠,之前彌漫在周圍的恐慌感,終于凝縮為不遠處的一個毛茸茸的黑點。我從小就怕老鼠。我不怕田鼠,小時候我經常跟男孩子們一起去野地里挖田鼠洞,看著一窩田鼠被澆上汽油再點燃之后,我總是既緊張又興奮。我怕的是城里的黑老鼠,在我的印象里,它們總是又肥又壯,神出鬼沒,永遠在你的附近悄然游蕩,哪怕是被打死了、毒死了,或是被鼠夾子夾死了,甚至是被我用高壓汽槍射殺的,看著它們的尸體,我還是會害怕。對于我來說,老鼠就是莫名恐慌的象征。
記憶深處的那些東西,自然是一種經驗。夢到的那些,當然也是一種經驗。曾經有些時候,我會更傾向于認為夢中的那些是更接近于文學的存在,因為我認為它的生成方式、呈現的狀態和那種天然的陌生化效果,對我寫小說有更多的啟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想法也在改變。現在我更傾向于認為,這兩種經驗的價值其實是一樣的。小說無法單憑任何一種經驗及其所包含的原生形式感就獲得其應有的形式,即使是夢的生成與結構方式總是有著出人意料的特質和超乎尋常的邏輯,也無法如此。因為小說既不是為了反映日常現實而存在,也不是為了反映非日常現實而存在,如果它存在了,那只是因為它本身已成為一種“現實”——語言生成的現實。它不是過去時的,只能是正在進行時的,讀的人打開它,開始讀它,它就是正在發生的。作者所能調用的一切資源,都只能服從于這種“發生”的需要,它們必須消隱于這種“發生”的進程里,成為別的某種東西;但,只屬于這一正在發生的世界里。在很大程度上,小說跟詩一樣,是最接近語言本質的,是對世界存在的某種回應,而不是對世界的反映。
二
或許,城市是因為人類出于安全感的需要而建造起來的。即使城墻早已不復存在,密集的建筑物,車流如織的馬路,人潮涌動的街道;這一切似乎也仍然在持續提供著某種大而化之的“安全意味”,不斷提供著某些約定俗成的“意義”,并以“不在這里你還能在哪里呢”的暗示,實現對事實上的“囚禁狀態”的遮蔽。這種“囚禁狀態”不斷改變著人對于世界以及自我存在感的體認方式,直到使之幾近于幻覺。那么,小說是用來揭發這種幻覺狀態的呢,還是用來制造某種異質化的幻覺的呢?顯然是兼而有之的。
留在記憶里的昨天或之前某天的一個夢,跟同樣留在記憶里的昨天或之前某天的一件事,有什么本質區別嗎?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并沒有。無論是在你的敘述里,還是你把它們都變成文字狀態,都將會發現,不能重現也無法再去驗證的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而且,由于記憶與回憶在機制上的不同,使得對于它們的每一次追述也都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人們對于這些改變通常都是下意識地接受了最近的那個版本,而很少會意識到其近乎幻覺的本質。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下意識的接受狀態,也是讓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承受城市對人的“囚禁狀態”的原因之一。
寫小說是重新制幻的需要,或許也是自我喚醒的需要。當寫作者能夠用某種文字生成的幻覺狀態去對應現實的幻覺狀態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二者之間的那種天然的張力必然會導致對貌似確定無疑的現實世界本質上的懷疑。進而意識到,造成“囚禁狀態”的,并非城市本身,而是人在幻覺中不斷膨脹的欲望。那么,當這種重新制幻的過程在小說寫作中得以實現,自我喚醒能隨之實現嗎?假如真的像卡夫卡所提示的那樣,小說作者以將自我日常現實化為廢墟為代價,達成了小說作品的生成,那么,或許作者在作品上寫下其名字的同時,我們就可以確認,他完成了對其現實生活的祛幻。甚至可以篤定地說,他成功地將消解后的自我隱匿于他的小說深處。他會認為,這或許就是擺脫日常現實所造就的那種“囚禁狀態”的唯一可能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