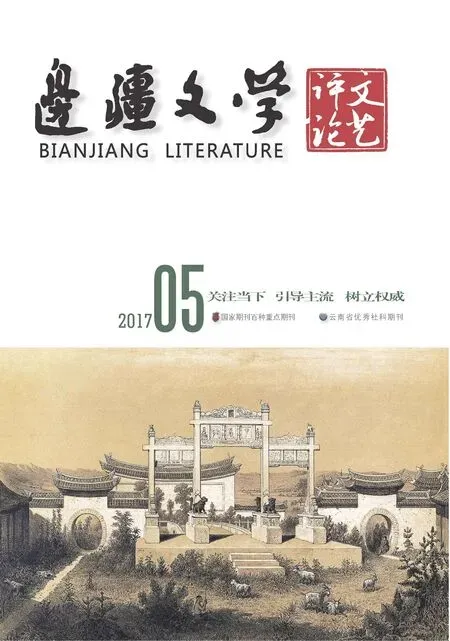劉年詩歌語言的“呈現”
朱 江
劉年詩歌語言的“呈現”
朱 江
劉年,本名劉代福,曾獲《人民文學》詩歌獎、華文青年詩人獎、紅高粱詩歌獎等,出版有詩集《遠》和《為何生命蒼涼如水》。劉年是當代詩壇比較活躍的詩人之一,其詩歌常常借助豐富的表達技巧將生活呈現給我們,基于此,本文以“呈現”為基點討論劉年的詩歌。
一、劉年詩歌“呈現”的基礎
詩歌是詩人利用語言將生活存在轉化為詩歌的語言存在,這是詩歌的本質。詩人所要做的事情即是將生活轉化語言。這里需要追究的是劉年詩歌的語言呈現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的,出于討論的方便,本文將基礎建立在思想的呈現方式即物象上。以他的《陽戲》為例,詩中諸如“狀元郎”、“鑼鼓”、“補妝”、“水袖”等,都是關于“陽戲”的詞語,因為有這些詞語出現,這首詩的生活性就突現出來,“陽戲”是一種生活存在,作者借助敘述將這種特定的生活存在根植在這些詞語中。正因為有前面的基礎,“定情物終將亮出來,沉冤終將得到昭雪”,這是個典型的細節。這既可視為某一場戲的過程,也可視為是對“陽戲”普遍過程的一種概括,這種概括同樣意味著一種敘述過程的形成,它是時空的高度概括,并非真的“陽戲”,真的戲不一定就是這兩句詩,真戲的內容更豐富。但這個過程又是“真”的,它是一種藝術的真實,這就是寫作的高度。這個過程中,詩人暗中設定了詩意,讓讀者在敘述中感受到某種味道。從寫作的層面上講,細節的本質其實就是對詞語的選擇,詞語的本質在于精準、藝術地還原生活。概括同樣意味著詩人對敘述節奏把握,作者在語言呈現過程中顯示出了一種冷靜的節制。而自始至終,我們看到的物象,它的真正根基就是生活。
這里說的高度概括依然是一種詩歌手段,其中包含對詞語的準確運用,這是因為,詞語的準確運用,蘊含著一個事實,那就是,越準確的詞語,它所表達的東西越真實,包容的生活越寬廣。正是因為對詞語的準確把握,劉年的詩歌才有機會在呈現中將詩意建立在句子之下,這也是劉年詩歌區別于許多分行散文式的詩歌的原因之一。詞語的準確是當代詩歌敘述的重要根基。比如“烏蘇里江的白樺,要忍到十月黃金周再黃啊”(《在辦公室遠眺》)中的“忍”字,“忍”就是忍受、忍耐,“忍”的主體是“白樺”,用“忍”去寫“白樺”,將白樺人格化,回歸到詩人自身,深層透視了同情,體現了語言的高效。再如“小臂粗的鐵鏈/一手抓住江底,一手死死地抓住岸”(《在湘江與王單單、胡正剛夜飲》)中的“抓住”,詩人運用比擬的手法,“動態”地寫出 “鐵鏈”外,還暗示當時三個詩人難舍難分的心情,感情的無形被形象地說出。
討論詩歌基礎,同樣需要深及詩歌語言推進過程中語言另一基礎,即詞語與詞語的關系,這就意味著,詞語呈現的關系,意味著詞語與詞語的關系,意味著詞語與物象主體的關系,意味著詞語與作者敘述指向的關系,甚至句子與句子的關系等。以《春風辭》為例,“快遞員老王,突然,被寄回了老家/老婆把他平放在床上,一層一層地拆//墳地里,蕨菜紛紛松開了拳頭/春風,像一條巨大的舌頭,舔舐著人間”。全詩兩節四行,兩組緊密相關的意象將兩個畫面組織成一個整體,簡潔而深刻地寫出了快遞員老王的后事。整首詩沒有借助多余的背景,語言直接進入詩歌本身。這里要探討的是詩歌是如何進入本身的,詩歌寫的是一個快遞員。前兩行詩中,詩人使用了三個動詞“寄”、“放”、“拆”,這三個動詞,是被修飾限制的,“寄”是“被寄”,“放”是“平放”,“拆”是“一層一層地”,這些動作組合在一起,非常形象的還原了一個快遞員作為快遞員的生活情境。這里所用動詞的準確,不僅僅是指動詞自身的準確,還意味著動詞與敘述主體的真正協調。第二節通過環境描寫,實現了“人”與“物”的融合。詩句先是“蕨菜紛紛松開了拳頭”形象地照應前面的“拆”,還暗線式地回到“快遞員”,回到“春風”。接著借“春風”來表達對人生的看法,以“舌頭”比喻“春風”,溫柔而富于味感,到“舔舐著人間”,戛然而止,最終回到人的存在及命運。全詩物象關系緊密,構成了一個縝密的物象鏈。由此可以上溯到詩歌句子與句子的關系,他的《青藏高原》第一行“喇嘛們做早課,做晚禱,隔三岔五地辯經”,非常醒目地呈現了青藏高原的某種常態,生活性非常強。之后作者大膽的想象,呈現一個非常典型的細節“枯死多年的榆蠟樹,因此長出了木耳”,這是一個點睛之筆,作者正是借助特定環境,將這兩行詩放在一起,寫出某種神秘的關聯,這就是詩歌的價值,這也是寫作以“詩人”的方式呈現的關鍵,優秀的詩人,寫作總是獨特的,基礎源于作家對生活的理解及大膽的想象。
二、劉年詩歌節奏的呈現
一般來說,詩歌不是將物象或者事實按先后順序羅列出來。每個作者都有自身的呈現方式,有自我的語言排列結果。句子內部,劉年的詩歌常常通過短句來推進。同時句子呈現,又不是將長句切分之后,按句子所謂的“一般的”“普通的”順序排列,它所借助的是自我獨特的語感,獨特的心理節奏。比如“橫斷山脈的月亮,灑下薄薄的鹽,輕輕地,為人間消毒”(《鹽井鎮》),這種排列,暗含著把月光比喻成鹽,再補充“輕輕地”,寫出了一種人文關懷,同時“輕輕地”又是修飾“消毒”的,加寬詩句的內涵。“灑下”的主體是月亮,句子表層是靜態的,“鹽”的存在,比喻變得動態,月亮被人格化,短句使意象變得很醒目。更主要的是,作者將節奏感設定在詩句中,關鍵詞語“月亮”、“灑下”、“鹽”及“消毒”被修飾語拉開距離,節奏感更強。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獨特的語感和節奏,這就是文學的魅力。
超出句子之后,節奏感是很隱含的,隱含的本質暗示了作者的心理。一個詩人表象的氣質是詩人內心氣質的載體。研究詩人,同樣要打通表象和內心的關系。表象是什么,表象就是語言,內核就是思想。他在《棕熊》,最后一節這樣寫,“多數的時候,躲在樹洞里/看鵝掌般的葉子,一片片落下。看獵人空手而還/看白雪,慢慢地埋沒人間/我把爪印深深地刻在樹洞里”。可以看出依靠句子與句子的關系來呈現節奏是劉年詩歌一種方式。詩歌通過三個“看”字引領的三個短句,排比地呈現了棕熊的主體存在,三個字,連續,反復,造成聲音的綿長。這既是文字主體“棕熊”的節奏,同時又是詩人內心的節奏。再加上一系列物象的使用,一個“孤獨”“弱小”形象躍然紙上。
往詩歌的整體上升,劉年詩歌的節奏與敘述有關,敘述方法的采用同樣可以呈現詩歌的節奏感。敘述方法的采用意味作者對物象的呈現、敘事的掌控和敘述的節制。利用插敘來舒緩敘述節奏是劉年采用的手法之一,如《野菊花》中與“特種兵”的決斗,出發之前的描寫,“青石路口,有九棵楓樹,兩塊巨石/縣志載,荊軻曾從這里,西去強秦”,這里突然宕開一筆,先前詩歌節奏被打破,借助“荊軻刺秦”的典故,將決斗寫得凄美悲壯,詩歌內涵更豐富。又如《在羊拉》中,“阿明是一個曠工,穿著脫了毛的皮夾克/兩杯酒后,他還原了牧羊人/用一種神秘的語言和舞蹈/又跳又唱。云一片片飄過來/羊群一樣,聚滿遼闊的夜空//他的話很臟……”,詩歌寫到“又跳又唱”之后,沒有接著寫阿明,而是插入“云一片片飄過來/羊群一樣,聚滿遼闊的夜空”,通過環境描寫來外化人物的心情,詩歌敘述節奏得以舒緩。
補敘也是改變詩歌節奏的一種方法。《八陣圖》開始寫寺廟,最后兩節,才抵達文字的真實,“如果坐得足夠久/你可以看到/一個尼姑,背著柴禾/從斜斜的青石路上下來//她今年二十七歲/研究生畢業/穿著咖啡色的僧衣/和深黑的布鞋”。詩歌通過最后一節去補充前一節中的“一個尼姑”,這樣一來,詩歌的內涵也就更加豐富。如果不這樣做,這首詩前面的鋪墊就沒有價值。寫寺廟,最終是為了寫人,最后一節形式上是一個補充,實質上是點明主題。節奏上講,開始是非常輕松的,讀到最后倍感沉重。
三、劉年詩歌結構呈現的多樣性
結構一方面是語言的呈現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構建思維。劉年詩歌結構多種多樣,這里討論比較特殊的結構呈現方式。
1.利用空間的位移來結構詩歌
利用空間位移來構建詩歌,是劉年詩歌結構的一種。空間位移是指將主體空間位移到另外物象空間的一種結構呈現方式。
劉年有一首詩叫《胡家寨的牧羊人》,全詩通過空間的位移,將“人”轉移到“羊”身上來結構詩歌,或者說詩歌借助 “人”“羊”交織來表現人間。“為了壓寨里的陰氣,胡生元/給它們一一安上了熟人的名字”,給“羊”安上熟人的名字,這是現實的,是這個特殊寨子的存在,它建立在“寨子里只剩/胡生元和他的四十一只山羊”的基礎上。這同時這又是虛化,作者要通過語言來重建這個世界,這就是文學的結果。這里一句話就確定了一種方式,安上名字之后,一切就變得順理成章。“頭羊叫胡光宏/那是他的知交,一輩子都想當回官/五年前,在城里扎腳手架時,摔死了/就埋在青楓嶺上/那里的草長得特別好”。“頭羊叫胡光宏”,為什么會是“頭羊”,因為胡光宏“一輩子都想當回官”,因為是“胡生元”的知交,所以就“就埋在青楓嶺上/那里的草長得特別好”。詩歌通過打通了人和草的關聯,表達一種無法言說的喜悅與傷感。一個知交,叫他頭羊,埋葬在青崗嶺,那里草長得特別好。人與羊的空間得以位移,那就可以通過羊來罵人,“最不聽話的那只,叫胡興華/胡生元每天都罵它娘,踢它屁股/他是村里的小組長/不僅搞大了唐玉娥的肚子/還砍了胡生元的兩棵核桃/后來跟女兒去了上海,據說學會了跳舞/中秋,胡生元準備親手殺了它”,在“胡生元”看來,人就是羊,羊就是人,最不聽話的羊就是胡興華,所以“每天都罵它娘,踢它屁股”,“中秋,胡生元準備親手殺了它”。詩人在這里,利用空間位移來構建詩歌,想象十分豐富。
2.利用時間的位移來結構詩歌
通過時間的位移來表現現實,是劉年詩歌結構的一種方式。比如“看著對面的他,像在照鏡子/八年之后,自己會有多少白發和皺紋/多少悲苦和辛酸,多少一目了然”(《別雷平陽》),這是將自己和雷平陽做空間上的位移,同時也是通過時間的位移,用現在的雷平陽來寫將來的自己,這里說的“八年之后”,雖然是“之后”,實際上就是雷平陽的某種“現在”,同時又是五年之后的某種自己。又如《寫給兒子劉云帆》中有:“其實,火葬最干凈/只是我們這里沒有//不要開追悼會/這里,沒有一個人懂得我的一生//不要請道士/他們唱的實在不好聽//放三天吧/我等一個人,很遠/三天過后沒來,就算了/有的人,永遠都是錯過//棺材里,不用裝那么多衣服/土里,應該感覺不到人間的炎涼了”,這是說一個人的后事,是一個人對兒子的教導。這里要討論的是,作者是通過什么方式讓人感覺到這是虛擬的。“突然想到了身后的事/寫幾句話給兒子”,有這兩行詩,讀者恍然大悟,這就是技巧,原來是一切是詩人“突然想到的”,是今后才有可能發生的,詩人在這里通過時間的推移,把將來時態的事情移到現在來寫,將還沒有發生的事情設定在現實世界里,讓后來發生的事情順理成章。而作者所寫“將來”的悲苦,同樣是現實的,是生活中正在發生的。
3.互文式的敘述
互文是一種修辭方式。文章結構上,互文同樣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個典型,一曲音樂演奏了兩個悲劇人物。琵琶女的身上,看到了白居易的影子;白居易的身上,看到琵琶女的影子,文字構成了結構上的互文。劉年的詩中就很好的運用互文的方式,《云丹達娃》中,詩人這樣寫“云丹達娃,是扎西尼瑪給我的藏名/意思是智慧的月亮”、“我回來了,云丹達娃卻一直在路上”、“他走走停停,他一直在等我”。詩中 “云丹達娃”就是“我”,“我”就是“云丹達娃”。
《游大昭寺》這樣寫“一個敲鼓唱經的喇嘛和一個沉默的詩人相遇了/大殿上,酥油燈的光芒逐漸強烈,柵欄逐漸消失//懂了嗎?喇嘛歌頌著的就是詩人詛咒過的人間/懂了嗎?那些詩歌串起來,掛在風中,就是經幡//沒有人注意,留在殿里是一個身著袈裟的詩人/走上大巴的,是一個帶著相機和微笑的苦行僧”。這里詩歌所借助的表象是詩人與喇嘛,它所蘊含的也許就是詩歌與宗教的相遇。詩中互文是多角度、多層次的,詩人與喇嘛,詩歌與經幡,詩歌與宗教。“留在殿里是一個身著袈裟的詩人/走上大巴的,是一個帶著相機和微笑的苦行僧”,詩人的身上有喇嘛的影子,喇嘛身上能看到詩人的存在。詩人信仰的是詩歌,喇嘛信仰的是經幡。“那些詩歌串起來,掛在風中,就是經幡”,在詩人看來詩歌就是經幡,對于喇嘛來說,他們一生吟唱的經幡,其實就是詩歌。“喇嘛歌頌著的就是詩人詛咒過的人間”,表面上一看,“歌頌”與“詛咒”是逆運動,本質上,兩種事業都是這個世界上最上層的,這或許就是詩人要借助宗教來寫詩歌在自己內心的地位的原因,這也是詩人為何要借助“大昭寺”的原因,如此厚重,含義迂回曲折隱晦,語句清新自然簡潔,余音繞梁。
4.通過人稱的位移來結構詩歌
通過人稱的位移,將人或者物位移于自身是劉年詩歌的一種結構構建方式,如《棕熊》,詩中寫到“我克制住自己,不襲擊人”,“我把爪印,深深地刻在樹洞里”。詩歌通過第一人稱“我”模擬棕熊的口氣來敘述,收到很好的效果。又如《想買一輛養蜂車》,整首詩的本質是在寫養蜂人的生活,但第一節里寫到“想買一輛養蜂車,后面裝200只蜂箱/我住前面,擺臺12寸的黑白電視”。這樣就很巧妙的是用自我的口氣來寫養蜂人。這里,詩人通過一個虛擬的將來時態的運用,“想買”不是現實發生的,它的主體是誰,是后面出現的“我”,想買的是什么,是“一輛養蜂車,后面裝200只蜂箱”,這里事情是想象的,但事情又是“真的”,世界上確實存在養蜂車。這里的200只蜂箱、12寸黑白電視機都是詩人建造的。作品在于作家的重建,怎么重建,“我住前面”,這里的“我”可以視為詩人自我,也可以說成通過自我的口氣,或者是養蜂人的角度。“我”成為了詩歌人稱位移的結果。
注:除引文[1]外,文中所引其他詩歌來自文[2]。
[1]劉年.劉年的作品[J].十月,2016,(3):230.
[2]劉年.生命為何蒼涼如水[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26—236.
(作者單位:云南鎮雄一中)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