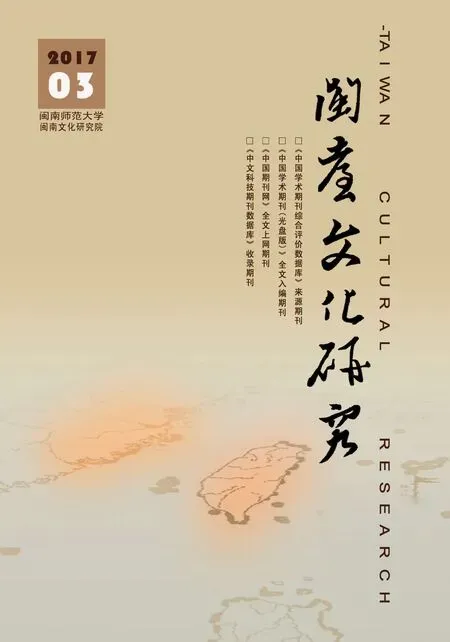利用閩南方言輔助格律詩寫作教學之管見
——兼論語文教育實習中師范生詩詞素養的培育
董國華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363000)
利用閩南方言輔助格律詩寫作教學之管見——兼論語文教育實習中師范生詩詞素養的培育
董國華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363000)
近體詩詞盛于唐代,閩南方言存留“唐音”較為完整。筆者任教于閩南方言區高校文學院,近年來為漢語言文學專業師范生開設古典詩詞寫作課,通過教學實踐發現和總結,在閩南方言區(學生的基礎方言為閩南話)講授格律詩寫作,引導學生利用方言:第一,分韻別部,理解古今語音源流及嬗變,掌握詩韻;第二,認準平仄,學習粘對、辨別入聲;第三,采用方音吟誦格律詩詞,深刻感受其韻律美。利用閩南方言輔助學生鑒賞和創作格律詩,教學效果顯著。此外,詩詞創作是中文師范生不可或缺的基礎能力,在語文教育實習中至關重要。應加大此類課程的比重,以培育和提升師范生古典詩詞素養。
格律詩詞;寫作;閩南方言;教學方法;語文教育實習;詩詞素養
在高校課程設置中,詩詞賞析課是歷久不衰的,往往是文科必修課,乃至是校公選課。而詩詞寫作課,卻就算在文學院也不普遍。在教學指導思想上和教學實踐中,往往把詩詞寫作排斥在教學范圍之外,導致中文專業的學生不愛、不懂詩詞寫作。由于格律詩詞寫作要求和技巧的困難,缺少講教授詩詞寫作課的師資,使詩詞寫作課長期徘徊在許多高校的課堂之外,致使學生對格律詩詞常識幾乎一無所知,更別提寫出一兩篇合律的作品了。另外,有關詩詞寫作的書種類繁多,但真正適合用作大學教材的卻甚少。這些書源流相類,說法大同小異,甚至如出一轍,皆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往往只羅列森嚴的格律,列舉例證又陳腐單調,無法觸類旁通,使初學者望而生畏且興趣索然。在教學中,不諳作詩填詞的教師如果單單據此講解格律詩詞創作,學生難以理解和運用,在習作時治絲益棼,事倍功半。
閩南方言是強勢的地域方言,被稱為古漢語的“活化石”,存留了完整的古音系統及詞匯和語法。《福建省志·方言志》指出:“唐代兩次大批入閩漢人,都以河南中州人為主體,當年的中州漢語,正是形成閩方言的最重要的基礎成分。這個基礎,既有東晉時期中原人士保留的上古雅言成分,又有唐代洛下正音《廣韻》為代表的中古漢民族標準語成分。正是這兩種成分構成了閩方言的共同性。”具體分析來看,唐高宗總章二年(669)陳政、陳元光父子(郡望河東)南下平蠻,屯墾漳州,先帶來七世紀的中古漢語。唐末黃巢之亂(878),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審邽、王審知三兄弟南下平亂,所率兵民大都是淮南道光州人,又帶來九世紀的中原官話(閩南話“讀書音”的主要來源)。近體詩是唐以后的主要詩體,閩南方言區存留中古讀書音系統較為完整,用閩南話吟誦、賞析近體詩,尤其唐人作品,自然本正源清。利用閩南方言學習、鑒賞、創作近體詩,更是格律詩詞寫作課程教學的利器。
筆者所任教的閩南方言區高校,其生源大多來自閩南方言區,少部分來自其他閩方言(閩西為多)區和粵東、贛南方言區,個別來自其他地區。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利用閩南方言輔助進行詩詞寫作教學,不論對于操持閩南話的學生,還是使用其他方言的學生,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具體教學方法總結為以下幾點(依講授和學習先后規律為序):
一、利用閩南方言分韻別部,理解古今語音源流及嬗變,掌握詩韻
近體詩押韻嚴格,初學者首先需記誦《平水韻》平聲30部名及其所轄常用字。學生易受現代漢語普通話韻母音讀影響,誤記、混記韻部轄字,不能準確分辨古人作品用韻,習作中往往出韻。若利用閩南方言讀音記憶,則十分便捷。例如杜甫《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此詩屬“平水韻”平聲“侵”韻,其韻腳在普通話中為 in(心、金)、en(深)和 an(簪),已失和諧。“侵”韻收雙唇鼻尾韻(即收閉口韻[-m]),而普通話中沒有這個韻尾,但閩南方言文讀音卻保有[-im]、[-am]和[-iam]閉口韻尾音讀(以漳州方言音讀為例:深[tsim]心[sim]金[kim]簪[tsim]),故韻腳極為諧洽。學生在記憶“平水韻”中“侵”“覃”“鹽”“咸”這四個收閉口韻尾的韻部轄字時,依閩南方言讀之,自然簡易準確。
而且對于初學者最易混淆的用韻問題,如為何“先、纖”“天、添”“前、潛”“煙、淹”和“年、粘”完全同音卻不能押韻(前一字均為下平一“先”韻字,后一字均為下平十四“鹽”韻字),對于為何“居、余、驢、車”與“初、書、舒、豬”可押韻(同屬上平六“魚”韻),為何“回、梅、杯、雷”與“哀、開、臺、來”可押韻(同屬上平十“灰”韻)等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二、利用閩南方言認準平仄,學習粘對,辨別入聲
平仄和粘對使詩歌誦讀起來具有了抑揚頓挫、此起彼伏、高低錯落的豐富樂感和諧和美感,是近體詩區別于古體詩的主要特征,也是自由詩(或稱新體詩)不具備的審美特質。“平仄”即“平直”和“曲折”,是格律詩詞語之間交錯組合的規則。“粘對”即“相合”與“相反”,是近體詩句子之間交錯組合的格律。“平仄,這是律詩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們講詩詞的格律,主要就是講平仄。”提高舊體詩詞的鑒賞和創作能力,必須了解中古平上去入聲調與現代漢語“四聲”的異同,掌握平仄格律常識,否則無法進行格律詩詞創作。
在教學實踐中,首要任務是讓學生認準古今平仄異讀的字,古平今仄字數少(如看、場、漫、去、俱等)易記,而今讀陰平、陽平的入聲字(尤其是最常入詩的高頻字,如七、八、十、黑、白、國、別、竹、獨、節等)是初學者的攔路虎。由于近古漢語官話音“入派三聲”,這些字古代歸仄聲,現代歸平聲。造成了平仄錯亂,給作詩和填詞帶來了麻煩,是講解平仄和粘對格律的重難點。
從語音學上說,入聲是以塞音收尾的音節。入聲帶有的塞音處在音節末尾,只有成阻,沒有持阻,具有發音短促、突然停止、不能延長的語音特點,形成了一種急促頓挫的閉塞音。漢語的入聲以塞音[-p]、[-t]、[-k]和喉塞音[-]收尾。在現代漢語方言中,閩語和粵語還完整地保留著這四種入聲,在吳語中則已變成了較不明顯的[]收尾了。其他方言(湘語、贛語、客家話等)有入聲存留,而在北方方言中,入聲已經基本消亡了。
傳統講解平仄、識別入聲的教學,利用普通話聲母來分類識記(如聲母是b、d、g、zh、z、j的陽平字是入聲字等)或使用形聲字偏旁類推記憶(聲符為入聲字的形聲字大都是入聲字),增加枯燥的機械記憶量,效果一般。對于保留了入聲的閩南方言區,入聲韻的三種韻尾在閩南方言中保存得比較完整,利用方言辨別入聲字卻并不是困難。
對于班級中其他方言中存有入聲的學生,雖然塞音類型可能不如閩南話存留完整(如吳方言的古入聲韻尾一律變成喉塞音[],發音時喉部緊張,可以選擇部分常用入聲字練習,掌握發音特點后進行類推),但并不影響識記入聲字;而對于不會講入聲的少數學生,如果通過說閩南話的學生進行范讀,也大大增強了直觀感,減少了記憶難度。
此外,近體詩押平聲韻,詞在押韻上卻要區分四聲,仄聲上去或可通葉,入聲字或不與上去聲通葉。有一些詞牌,如《憶秦娥》《滿江紅》《念奴嬌》《聲聲慢》等,其正格需全用入聲韻。誦讀押入聲韻的詞牌時,這種表現更為明顯。例如李白《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個詞調一韻到底,韻腳促密,上片四韻、下片三韻,各一疊韻,韻腳為入聲“薛”韻字,唯有用短促急收的入聲來朗誦或吟唱,才真正能體現出悵惘、迷茫等等哀傷情緒,用保留入聲字閩南方音來吟誦這首詞,才別具風味,若用普通話朗讀則少了很多韻味。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范讀這些入聲韻腳的單字音,然后讓會說閩南話的同學作朗讀示范。
三、利用閩南方言采用方音吟誦格律詩詞,深刻感受其韻律美
古典詩詞是音樂文學。《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見,“詠歌”是為彌補“發言”和“嗟嘆”的不足。“詠歌”即“吟誦”,是“誦讀”和“吟詠”的合稱,是我國傳統的詩文聲音表現的一種重要藝術形式,它介于朗誦與歌唱之間,緊密結合漢語韻調、詩文節律,歷代文人學子莫不諳此,是學習、欣賞和創作詩文的有效輔助方法。
傳統的詩詞教學較為忽視聲美教學。老套的做法是鑒賞名篇名句,從難解字詞入手疏通主旨大意,然后結合寫作背景、作者生平和風格手法等賞析作品。其實,詩詞作為音樂文學,其審美特質應該是二維的,既要注重釋義,更要注重音韻,才能更準確表達出古詩原有韻味,聲韻與字義的結合,才是漢語詩歌完整內涵。另外,由于普通話的推廣普及,方言淡化退出校園,方言文讀音已失去表現舞臺。教師朗讀詩詞基本是以普通話為媒介,按音節兼顧意義來分割語句,五言采用的基本上是23或212節奏,七言基本采用223節奏。這樣的朗讀,使五言絕句讀起來節奏大體相同,沒有什么變化。不能顯現出古詩原有的音韻節奏。而用吟誦的方法才能符合古詩原有的音律。
吟誦教學恰恰彌補了傳統古詩教學的不足。用吟誦這種形式進行古詩教學,有其獨特的魅力。但由于古今差異,現代漢語普通話韻母和聲調已過于簡略,用于吟誦詩詞已不太合適,無法做到音律和諧,絲絲入扣。與中古的聲調系統相比較,閩南方音基本上與中古音平上去入調類吻合(如漳州話平去入三聲各分陰陽,上聲一調,共有七調;泉州話則平上入分陰陽,去聲一調,亦有七調)。這正是用閩南方音吟誦格律詩詞往往要比普通話來得和諧、入律。而用閩南話吟誦近體詩,尤其是唐人作品,本正源清。使用閩南方音吟誦璞出于石,凸顯出古詩原有的音律美和節奏美。為弘揚優秀的中華詩詞文化,我們有必要讓閩南方音吟誦繼續發揮以聲傳情的特殊功用。
在教學實踐中,教師按“平長仄短入聲頓”的方式來斷句誦讀,同時按平低仄高、依字行腔的原則來“吟詠”,詩人的情感,詩歌的意境已了然于胸、情感噴薄而出,在長短高低中極盡曲折變化之音美。教師可通過范讀,引導學生反復練習,后期可根據學生個體獨特的情感體驗,在“平長仄短入聲頓”的大原則下自由吟誦。
另外,除從上述語音角度利用閩南話學習詩詞寫作之外,還可以通過閩南方言詞匯來輔助詩詞理解和鑒賞,如以下三例:
1.無[bo]:語氣助詞,念輕聲。如食無?(吃了嗎?)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閨意獻張水部》朱慶馀
2.傷[siu]:“傷”讀書音[siɡ],說話音[siu],作副詞,表示“太”。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曲江》杜甫
“長生緣甚瘦,近死為傷肥。”——《野雞》齊已
3.人客[laɡk‘eh]:客人。
“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感懷》杜甫
例1中,“無”若依普通話讀作陽平[u],則顯得生硬無味,而使用閩南方言讀輕聲[bo],則能恰到好處地呈現出這位新婦梳妝后,低聲詢問丈夫時嬌羞可愛的模樣,極為生動形象;例2“傷”在閩南語中仍存有程度副詞“太”“過度”的用法,詩詞古文中常見,而普通話中已無此用法;例3“人客”是“客人”的意思,此處平仄恰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對仗嚴整工穩。
四、培育格律詩詞寫作能力、提升師范生文化素養
高等師范學校語文教育實習課程既是一種教育實踐行為,又是一種形成和提升漢師范生教學能力的過程。語文學科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兼而有之的學科,語文學習不僅僅是一般的語言學習,更是母語和民族通用語的學習。中小學語文教學的任務是教會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能夠運用語言和文字工具去認識和反映現實,表達思想和感情,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所以,對于將來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的高等院校師范生來說,他們不能只是具有科學知識和技能的“工匠”,而應是具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未來社會的新人”,同時也是具備包括審美能力在內的人文素養的“文化傳承者”,而這種審美能力體現為以“激情、想象和形象”感受美、認識美和創造美的素質與能力。
中國古典詩詞是體現漢語內在規律的完美體現,是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的抒情工具。而傳統的近體詩和詞,正是從語音和字形兩方面體現了漢語的特質,并充分利用了決定于這一特質的規律和優勢,是優秀中華文化的核心表征。千百年來,詩詞創作一直是中華民族審美精神創造的一個重要途徑,它使讀書人保持了生活的詩性化,保持了對社會的審美追求。
在師范生素養培育中,對古典詩詞鑒賞、創作的教學實踐不應被忽視。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在語文教育實習階段,直接面對的是中小學生。而就目前中小學學段對于格律詩詞的教育目標而言,對古典詩詞方面的要求其實是比較高的。例如,教育部新修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要求小學生背誦古典詩詞80首,《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和《全日制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共要求學生能夠背誦古典詩詞80首、古文30篇。《中學語文教學大綱》還指出:要讓學生“了解散文和詩歌的一般知識”,其中自然包括舊體詩詞和格律常識。全國中學語文通用教材,對古體詩和近體詩、律詩和絕句、詞的種類、舊體詩詞的押韻、對仗、平仄、朗讀節奏等詩詞格律常識,也都分別作了介紹。此外,全國高考語文試卷(也包括單獨命題的省市高考)在語文知識運用模塊,屢次出諸如選配對仗、詩句排序、擇句填詞等涉及詩詞格律的試題。由此可見,詩詞格律教學是執行《大綱》所規定的教學任務的需要,是指導學生學好教材內容的需要,更是培養學生獨立閱讀舊體詩詞能力的需要,而忽視或排斥格律常識教學,則與此相悖,是不利于提高語文教學質量的。而將來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的中文專業師范生,僅僅懂得背誦、鑒賞古詩詞,而不懂得詩詞格律和創作,實質上是不合格的。
總之,針對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師范生的詩詞教學,目標是使學生首先做到熟練掌握詩詞格律常識,能分析鑒賞前人作品,并寫出合格的詩詞作品;其次做到經常創作,形成興趣愛好和習慣,寫出優秀的詩詞作品;進而培養自身詩性、審美能力和品性,培養高雅的審美趣味,培養高貴的文化精神。唯有如此,在他們語文教育實習過程中,才能夠利用這種能力和素養,去教育和引導中小學生發現和感受詩詞中的美,不僅為孩子們的語文素養提供重要的培養基,也使自身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注釋:
[1]黃典誠主編:《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2]王力:《詩詞格律》,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21頁。
[3]馬重奇:《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年。
[4]施榆生:《漳州方音詩詞吟誦初探》,《閩臺文化交流》2006年第3期。
[5]林寶卿:《閩南方言是古漢語的活化石》,《閩臺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6]郭啟熹:《閩方言與寫詩填詞》,《龍巖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7]趙維江:《“全球化”語境呼喚古典詩詞的復歸——兼論大學開設詩詞寫作課之意義》,《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8]熊言安:《高校古典詩詞寫作教學的實踐與反思》,《銅陵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9]劉彩霞:《高師語文教育實習課程的個性特征》,《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責任編輯 吳文文〕
On Minnan Dialect-Aided Poetry Teaching——On the Cultivation of Poetry Accomplishment of Normal Students in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Dong Guohua
The poetry writing is a difficult ye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riting course for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mal).Chinese poetry flourished in the Tang(唐)Dynasty;in Minnan dialect remained relatively intact Tang phonology(唐音).The author,a teacher of classical poetry writing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instructs metrical poetry writing,guiding them in the use of Minnan dialect:firstly knowing the rhythm and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phonology;secondly understanding the tonal pattern;thirdly reciting metrical poetry in native accent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its rhythm.The teaching effect is remarkable.Such courses can help students cultivate and enhance the accomplishment of classical poetry.
metrical poetry,writing,Minnan dialect,teaching method,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poetry accomplishment
董國華(1982~),男,河南汝州人,文學博士,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福建省教育廳社科基金項目:“語文教育實習課程設計”(JAS15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