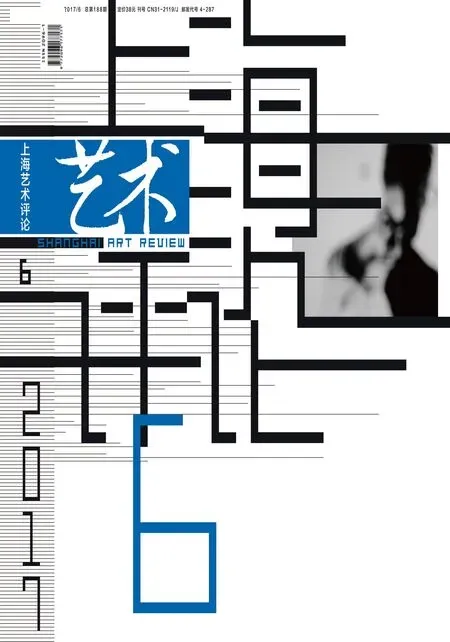無聲詩里頌千秋—從《趙孟頫書畫特展》淺談博物館藝術教育
付韋鳴
在“故宮熱”現象不斷升溫的同時,關于故宮博物院如何更好發揮其文化教育職能的討論也越來越熱。在現代社會對博物館的定義中,通常認為博物館具有三大功能:即收藏、研究與教育。在博物館發揮教育功能的過程中,以各類展覽和文物為契機,對公眾進行藝術審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2017年9月6日,《趙孟頫書畫特展》在故宮武英殿拉開帷幕,展覽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因觀展人數眾多,在武英殿一度出現限流排隊。本次特展所展出的百余件書畫藏品,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另有上海博物館與遼寧省博物館的藏品。包括《秋興詩》《歸去來辭》《洛神賦》《水村圖》《秋郊飲馬圖》《疏林秀石圖》等在中國書畫史上鼎鼎有名的杰作,從不同時期全面展示了趙孟頫的書畫藝術。在本次展覽中國家一級文物數量達到全部展品的80%以上,所展文物的時代之早、級別之高、質量之佳、數量之大,均堪稱空前。
與此同時在午門展廳舉辦的《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中,《千里江山圖》《游春圖》《萬松金闕圖》等名作亮相,使“故宮跑”現象再度重現,在故宮實施領取限時號牌等管理措施后,有效緩解了觀眾的排隊壓力。“千里江山”與“趙孟頫”兩大特展的“雙璧”呈現,為公眾帶來了一場古代書畫藝術的饕餮盛宴,所引發的轟動效應,反映出現階段人民群眾高漲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這種火爆的觀展熱潮既是對故宮博物院展覽質量的肯定,也為展覽的配套服務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筆者作為故宮博物院書畫教育中心的一員,參與了《趙孟頫書畫特展》的藝術教育與文化傳播工作。現針對本次展覽,談一些對博物館開展藝術教育的思索與淺見:
博物館藝術教育的意義
縱觀歷史,從清室遜位到古物陳列所設立再到故宮博物院的正式成立,無數傳承千年文明的珍貴文物由封建社會皇家獨享的私人收藏變成了新中國人民共有的文化財富,故宮博物院及所珍藏的歷代文物本身即是中華文明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見證者,它們見證了中國從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再到社會主義的充滿曲折而又無比輝煌的歷程。截至2016年12月31日故宮博物院第六次文物清點成果顯示,故宮館藏文物總量為1862690件,其中珍貴文物1683336件,文物總量占全國博物館系統保管文物總量的四成以上,珍貴文物占全國的六成以上。這其中就包括館藏的繪畫、法書、碑帖藏品158823件,這些書畫藏品中以《平復帖》《馮摹蘭亭序》《五牛圖》《千里江山圖》《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等為代表的大量一級文物都是公眾耳熟能詳的名作,這些曠世杰作一經展出常能引起舉世矚目。
在數量宏富的藏品背后,是故宮本身屬于世界最大規模木結構宮殿建筑群的嚴格文保要求,在古建筑內開設展廳存在不少的條件制約。故宮每年只有約1萬件藏品能向觀眾展示,僅占全部藏品的0.5%左右,這個數據遠低于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等國外大型博物館的展出文物比例。
即使存在上述客觀情況,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在書畫展覽方面取得的成就頗多:2015年為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舉辦的“石渠寶笈特展”,在為期數月的展覽期間共展出院藏歷代書畫283件,其中尤以《清明上河圖》的展出最為火爆,引發空前的觀展熱潮,并通過網絡媒體宣傳生發出“故宮跑”等專有名詞。在由《藝術商業》雜志發起、經兩岸三地66家主流藝術媒體資深代表票選出的“2015年度十大藝術事件”中,故宮“石渠寶笈特展”以95.4% 的高得票率成為第一名。
在“故宮熱”現象不斷升溫的同時,關于故宮博物院如何更好發揮其文化教育職能的討論也越來越熱。在現代社會對博物館的定義中,通常認為博物館具有三大功能:即收藏、研究與教育。2007年在維也納召開的第21屆國際博物館協會代表大會上,首次將“教育”作為博物館的第一功能進行闡述,將其排在了“收藏”與“研究”之前,使發揮相應教育功能成為博物館的社會責任與首要任務,也代表了現代博物館從“收藏中心”向“公眾中心”過渡的歷史轉變。這一觀點在國際范圍內獲得廣泛認可:美國博物館協會將“收藏”定義為完成博物館教育功能的手段而非目的;法國盧浮宮博物館前館長亨利·羅瑞特(Henri Loyrette)認為:“現代博物館是公民責任的工具,是批判精神的孵化器,是品位的創造地,它保存著理解世界的鑰匙。它必須有能力通過各種手段,把這些鑰匙傳遞給其他人。”
在博物館發揮教育功能的過程中,以各類展覽和文物為契機,對公眾進行藝術審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藝術審美教育亦被稱為“美育教育”,旨在通過對自然美、藝術美等的展示與教育,培養人們正確的審美觀并提高欣賞美、創造美的能力。對于廣大公眾特別是青少年來說,“美育教育”理應成為系統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鑒于我國目前“國學教育”也僅是部分學校教育體系之點綴的現狀,學校中的“美育教育”則更為有限。學校教育的缺失,必須靠社會教育來彌補,博物館的藝術審美教育,恰好屬于社會教育的范疇。
早在民國時期,教育家蔡元培就曾在北京大學提出過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他認為人精神上之作用,分為“知識、意志、感情”三類。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宗教兼具三者的作用;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了“知識”與“意志”逐漸獨立于宗教之外,只有“感情”與宗教最為相關,而“感情”則體現為美育,純粹的美育可以陶冶與培養高尚的情操。蔡元培先生認為美育相比于宗教,具有更加“自由、進步、普及”的特點,因此試圖將美育作為一種改造國民性的理想精神之教育。在他所寫《美育實施的方法》一文中提到的實現美育教育功能的單位中,就包括當時的古物陳列所,即故宮博物院的前身。由此更凸顯出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全國博物館旗幟的故宮博物院,在發揮博物館藝術教育職能時的責任與義務。
博物館藝術教育的方式
博物館教育沒有學校教育的明確目的性和強制性。比如故宮博物院的展覽面向所有感興趣的觀眾開放,但在是否參觀展覽、是否接受藝術教育方面故宮對所有人不具有強制性和約束性。因此,為保證故宮教育職能的有效發揮,需要注意如何激發對象的觀展興趣。具體到書畫類特展的藝術教育,還稍有別于歷史類或革命類展覽對觀眾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部分觀眾對自己參觀書畫類展覽被稱為受“教育”是有所抵觸的。因此,在對公眾進行藝術教育的過程中,通過對展覽與展品充滿故事性與連貫性的闡述,引導觀眾自覺地去發掘、去體會展覽所蘊含的文化,往往能收到比程式化說教更好的效果。
“能吸引觀眾的是故事,是藏品的故事,是展覽的故事。展覽的文物中不一定要有價值連城的國寶,但是一定要有在展覽中講得出故事的文物。文物的組合是要讓故事一環扣一環、一波接一波地演繹,而不是將不同類型、不同排列的文物作簡單的堆砌。”作為故宮博物院這樣一個館藏一級文物數量占絕大多數的收藏“倒金字塔形”博物館,可以做到每次書畫特展都有國寶重器亮相,客觀上擁有更多的受眾群體,更應深入挖掘展覽與展品背后的故事,并通過博物館的藝術教育將相關歷史、文化、藝術信息傳遞給觀眾。
筆者對于挖掘展覽故事性的體會與思考,緣于2015年石渠寶笈特展中《清明上河圖》撤展前后觀展人數的鮮明對比:《清明上河圖》自開展以來即成為最大的亮點,大量觀眾為一睹其風采甘愿排隊六七個小時以上;在此圖撤展后,觀眾人數有很大下降。然而在特展中還有《游春圖》《五牛圖》《伯遠帖》《馮摹蘭亭序》等一大批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均不低于《清明上河圖》的歷代名作,但這些作品并未獲得如同《清明上河圖》的關注度。在石渠寶笈特展結束后,不少專家分析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認為《清明上河圖》作為表現北宋都城汴梁的風俗畫,長篇繪制都市繁華、市井生活等場景,其圖畫本身就充滿了故事性的描述與展示,易于被大多數人理解接受,能夠引起公眾的共鳴,而不像某些文人繪畫需要相關的藝術與歷史知識儲備方能很好地欣賞。由這一現象還引發出博物館教育該如何兼顧順應觀眾的興趣,及合理引導部分觀眾轉變對古代書畫認識不夠全面的現狀。這也對故宮的藝術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趙孟頫書畫特展》藝術教育的傳達
實際上,本次趙孟頫書畫特展的展陳設計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再創造的過程,策展者通過獨具匠心的布置,將展覽劃分為“溯本清源”“書畫交輝”“松雪遺韻”“云泥有別”四個單元,分別從趙孟頫的藝術淵源、傳世的經典書畫作品、受其藝術影響的后代藝術家、真偽作品對比等四個方面進行展示。如果說單件散落的展品猶如一粒粒的“珍珠”,那么通過完善的展覽規劃則可使眾多展品串連成一條璀璨的“項鏈”。特展的內容不局限于書畫本身,而是將與趙孟頫相關的宮廷玉器、漆器、元青花與奇石嘉木、文人書房空間等諸多要素補充其中,用豐富的展品形式與空間形態搭配對色彩與光影的把控,防止特展過于平面化與符號化而削弱傳播能力。正如北京大學宋向光教授指出:“博物館陳列的核心特性在于意義溝通。”以上所有嘗試均力圖以一種更整體的形式同受眾進行一場關于趙孟頫藝術精神內質的交流。而作為服務于本次展覽的藝術教育,也應當充分發揮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為這場“意義的溝通”貢獻一份力量。
因此在趙孟頫書畫特展面向公眾的藝術教育過程中,我們特別關注對展覽與展品故事性的闡述。特展的主角趙孟頫不僅是元代文人領袖,還和明代董其昌一起成為對明清書畫影響最大的藝術家。他又是一個復雜的人物:論歷史地位,他既是被恩遇五朝的“榮祿大夫”,又是代表江南遺逸的“吳興八俊”;論藝術成就,他既是元代“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的藝壇領袖,又是明清“人品書品論”的矛頭所指;論內在思想,他既是“且將忠直報皇元”的儒家書生,又是“人誰無死,如空華然”的釋家弟子。這些復雜性貫穿了趙孟頫的一生,為今天的我們如何定位他產生了一定難度,也在客觀上拓展了趙孟頫特展中故事性延展的可能:
1.將人物生平與展品融合
以趙孟頫的一生作為軸線,我將他的生平大致劃分為幾個階段并梳理出各階段的重要事件,分別為:青少年階段(宗室脈絡—父親與家學—少年喪父—自強學問);青年階段(宋亡隱居—被征仕元—初入大都—外任濟南);中年階段(病休吳興—出任儒學提舉—藝術黃金時期);晚年階段(官場榮耀—子妻亡故—潛心佛學)。隨后尋找他人生不同時期的重要階段與特展展品的對應關系,如將青少年階段與特展第一單元“溯本清源”相結合:從《行書秋興詩卷》展現趙孟頫早年書學高宗趙構的風格特點,結合卷尾前后兩段時隔四十年的自題,讓觀眾直觀感受藝術家在藝術草創期和成熟期的不同面貌;以鮮于樞《草書杜甫魏將軍歌卷》及錢選《八花圖卷》引出趙孟頫的藝術交游及隱居家鄉期間的相關事件。
將趙孟頫青年階段、中年階段與特展第二單元“書畫交輝”相結合:以《行書歸去來辭卷》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名句闡述趙孟頫初入大都時的意氣風發、欲展作為,再到逐漸轉變為彷徨失策、明哲保身的心態變化。并結合作品卷尾啟功先生的長跋,綜合論述此件作品的筆法特點、啟先生對趙孟頫書法的深刻認識以及題款“孟俯”的藝術考證等一系列問題;從《二贊二詩卷》看趙孟頫“非典型性”書風中對顏真卿和米芾的學習,以及他出任江浙儒學提舉后交游山水、把酒言歡的閑適自得;從《行書洛神賦卷》看“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趙體行書成熟期的書風,探究他對二王法度的繼承發展;從《水村圖》看趙孟頫如何“大刀闊斧”地省減中國畫筆墨,為文人畫的發展扛起大旗;從《秀石疏林圖》與“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與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的詩畫互證,探討趙孟頫的書畫藝術理論;以《近來吳門帖》解讀充滿生活氣息的大藝術家日常往來信件,追尋古人信札難識難懂得的歷史淵源;從《帝師膽巴碑》引申出趙孟頫晚年官居一品、追恩三代的榮耀及子妻去世后的打擊,最終看破世事,轉向釋家對內心追尋的轉變。
用特展第三章“松雪遺韻”中的《趙氏一門墨竹圖卷》引出趙孟頫與管道昇“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趙孟頫與趙雍父子相承的家學淵源;以《快雪時晴書畫合璧卷》講述趙孟頫與弟子黃公望的故事;以《文徵明臨趙孟頫蘭石圖卷》為例探討趙孟頫對明代書畫發展的影響,并結合此卷刻本與墨本共存的特點,探討明清時期部分書家對趙孟頫書法“姿媚”和“時有俗筆”的攻擊,并延展到墨本與拓本風神上的區別、真本與偽本同時被收錄刻帖等的情況,扶正部分有失偏頗的意見,使觀眾更全面的審視趙孟頫的書畫與人生。
2.對抽象概念的合理表達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趙孟頫在藝術領域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全能”:在書法領域,他和顏真卿、柳公權、歐陽修并稱“楷書四大家”,而其書法成就又遠不止楷書一項,而是“楷、行、草、隸、篆”五體皆能,為元代各書體的復興作出了貢獻;在繪畫領域,他以山水、人物、鞍馬、花鳥、竹石“全能”的姿態傲視畫壇,所領袖及倡導的“復古”藝術傾向,影響了數百年中國畫的藝術走向,是文人畫逐漸成熟的標志;在文學領域,他著有《松雪齋集》,是元代復古詩文運動的先驅和首領;在音樂領域,他著有《琴原》《樂原》等一系列音樂論著。
在藝術教育的過程中如何向受眾傳達趙孟頫的“全能性”,這是完善特展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畫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展廳內的作品實體加以闡述。而對趙氏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如果簡單的以背誦詩文的方式展現,則相對生硬枯燥不易于被接受。為此我們選擇在講解過程中插入這些文學內容,如在對趙孟頫隱居時期情況進行介紹時,加入《松雪齋集》里祭奠岳飛的詩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體現出他身為宗室后裔卻對南宋統治政權表現出的失望與反思;在講述趙孟頫仕元初期內心仕進與隱退的矛盾境遇時,引出其《罪出》一詩“昔為海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羽日催槁”,表現趙孟頫在這一階段對仕元抉擇的重新思考。這些“嵌入”故事中的詩句既與趙氏經歷的歷史事件相呼應,又展現出他取法晉唐的清麗文風,自然而然引導觀眾注意到趙孟頫“易為書畫之名所掩”的其他成就,是寓文學于故事的一個實例。
3.對每件展品的深入挖掘
除了以上在宏觀層面規劃展覽故事的脈絡,對于特展每件展品內在故事性的深度挖掘也是豐富教育內涵的重要部分。介于特展中的作品眾多,在此僅挑選較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展開論述。處于本次特展第一單元“溯本清源”中的首幅作品是唐代貞觀年間署名“國詮”的《楷書善見律卷》,這卷看似于趙孟頫“無關”的作品很多觀眾往往一帶而過,實際上它卻是一件對理解趙孟頫藝術淵源及元代前期藝術收藏極為重要作品。除去這卷書寫于初唐、記錄佛教律藏經典的書法本身所具有的極高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外,在本次特展中此卷最重要的意義是曾經被趙孟頫收藏十年,可以視為他小楷師法唐人的參照物之一,這對我們理解趙孟頫小楷的師承與衍變具有很高價值。
除去對這卷作品本幅內容和書法的解讀,我還重點選取了三段題跋向觀眾解讀:第一段是趙孟頫的題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很多重要信息:趙孟頫在吳中(此時任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是主管江浙地區教育、文化、祭祀等的儒雅閑適的職務,遠離了元大都的政治漩渦,在江南地區與眾多藝術家相互交流,因此也成為趙孟頫藝術創作的高峰期)獲得了這卷唐人寫經,趙孟頫認為國詮的書法深得初唐書家褚遂良和薛稷的筆意,還指出卷尾有監制書法的唐代趙模、閻立本的署銜。到了皇慶二年(此時元仁宗追贈趙孟頫的父、祖,衣錦還鄉立碑修墓,妻子管道升也回鄉為雙親建造“管公孝思樓道院”),趙孟頫將這卷寫經轉交給了“蘭谷”,并請他一定要妥善收藏這卷珍貴的作品。以上信息既是對趙孟頫書法藝術與此卷關聯的佐證,也是本次展覽收錄這件唐代書法的依據。
第二段為觀眾分析的是元代馮子振的題跋,從題跋所用書體和所寫“僧徒讀律不守律”等內容上都能看出,這位與趙孟頫同時代的文人是極富個性的書法家。更重要的是馮子振題跋中顯示出收藏者此時已變為“皇姐大長公主”,這位公主即元代初期蒙元貴族中著名的“藝術贊助人”祥哥剌吉公主,她對元代初年漢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正在故宮午門展出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在《游春圖》后亦有一段馮子振為公主所題的跋文可互為印證)以及宋代崔白《寒雀圖》、趙昌《寫生蛺蝶圖》、黃庭堅《松風閣詩》等大量書畫名作當時都是公主的收藏。臺北故宮2016年10月舉辦的“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鑒賞文化”主題展覽,正是以祥哥剌吉公主在元大都所主持的“天慶寺雅集”為契機展開的。所以,對于馮跋及其所引申出的關鍵歷史人物和重要事件的解讀,將是帶領觀眾了解元初歷史及藝術領域大事件的關鍵。
第三段需要提及的跋文,應是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題跋。董跋首先記述了自己早年見到這卷寫經及作品的流傳情況,指出國詮書法的行筆和結構出自褚遂良門下。隨后董其昌提出:“(此卷)非宋以后書家所敢望也,以趙文敏正書校之,當有古今之隔,識者不昧斯語。董其昌跋,時年八十歲”。耄耋之年已是明代藝壇“天下第一”的董其昌在鑒賞之余,還不忘“損”一把幾百年前元代藝壇“天下第一”的趙孟頫,這就是另一段藝壇故事了。由此引出兩代“文敏”之間的“糾葛”(作為后代人的董其昌對趙孟頫在藝術上跨越時空的從較勁到輕視再到重新審視的過程);再到董其昌把古今畫家都編排進其南北宗論時,卻唯獨對趙孟頫只字未提。可以說董其昌的這段題跋是對元明時期藝術思潮變化的側面反映,同時還能引出對藝術史較為了解的觀眾就趙、董兩者書風畫風的比較與討論,在實際的教育過程中收到了很好的互動與反饋效果。
解讀文人書畫作品之后的眾多題跋與印章是帶領觀眾深入理解此件作品并明確作品遞藏次序、歷史淵源、藝術思想等的重要資料,而在過去的博物館藝術教育中,常因為不夠重視、時間有限、難識難考等原因,流于對作品本幅的賞析和闡述,而對眾多作品之外的題跋及其所蘊含的信息和故事的延展挖掘不夠,從客觀上限制了對作品整體故事性的探索。
4.以理性指導藝術教育
當然,我們在強調博物館藝術教育中故事性的傳遞時,必須始終牢記以故宮博物院為代表的各大博物館在公眾心目中都是具有極高科學性與權威性的機構,他們通過博物館藝術教育所學習到的知識與信息可能伴隨其一生。因此,博物館必須堅持以嚴謹的態度審核傳播內容,并保證向觀眾提供信息的客觀與準確。
身為博物館的藝術教育人員,亦當恪守其代表博物館傳播藝術文化知識時的理性態度,并以這種態度駕馭對更廣泛傳播效應的追求與渴望。其所選擇向觀眾傳播的理論或觀點,必須是學術界公認的最廣泛和最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在涉及有爭議的學術話題時,博物館教育者應當秉承客觀中立的原則,對各種不同學術觀點都加以介紹和闡述,由觀眾自己作出認識和判斷,而非代替觀眾去思考。唯有把握這個原則,再去探討加強展覽故事性的延展才有實際意義,否則只能是背離博物館藝術教育宗旨的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