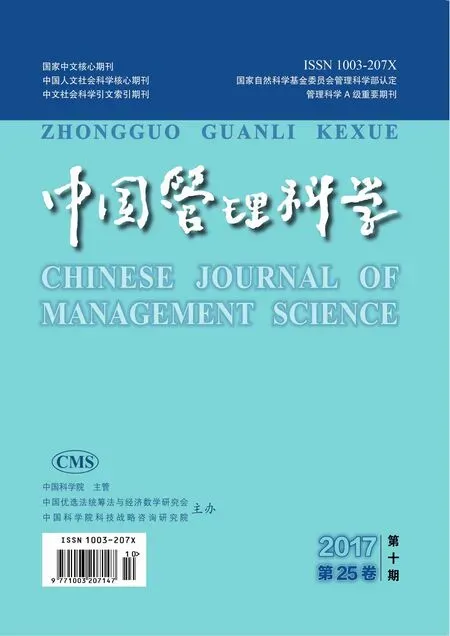中國碳排放增長驅動因素及其關鍵路徑研究
謝 銳,王振國,張彬彬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
中國碳排放增長驅動因素及其關鍵路徑研究
謝 銳,王振國,張彬彬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發展中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和關鍵路徑,對有的放矢地制定減排政策,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基于WIOD提供的中國序列投入產出表,采用結構分解分析和結構路徑分解方法考察了1995-2014年影響中國碳排放變動的主要因素和關鍵路徑。結果表明: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是經濟規模的擴張;而抑制國內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則是各部門碳排放強度的下降;中間投入產品結構的變動則進一步導致碳排放增長。從供給鏈路徑來看,“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和“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分別是驅動中國碳排放實現增長和下降的最重要路徑類型。為有效降低碳排放,中國應加強碳排放強度在關鍵路徑中的減排作用,促進生產的中間投入改革,優化需求產品結構,協調居民消費、投資與減排的關系。
碳排放;結構分解分析;結構路徑分解;驅動因素;關鍵路徑
1 引言
氣候變暖受到了國際廣泛關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成為國際環境外交的核心議題,也是經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話的重要內容。2015年12月,近200個締約方達成《巴黎協定》,標志著全球氣候新秩序的起點,如何實現合作調節、控制并最終減少碳排放成為各國未來幾十年的重要工作。中國作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進了中國碳排放持續快速增長,值得探討。且中國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面臨著嚴峻減排形勢。為深化中國碳排放增長的認識,實現減排目標,有必要識別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力,針對性地制定有效的減排政策。
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結構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可以將影響經濟、能源和環境系統的各個因素分離出來,單獨定量各因素對系統碳排放的貢獻。目前,SDA方法被廣泛應用于中國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研究中,Peters等[1]和Guan Dabo等[2]分析了中國碳排放量變化影響因素,Fan Ying等[3]和Zhang Youguo[4]對中國碳排放強度變化進行了分解,Geng Yong等[5]和Tian Xin等[6]則探究了中國省份碳排放的驅動因素,趙忠秀等[7]和張友國[8]等對中國貿易含碳量進行分解。研究者從上述不同層面與角度對中國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研究,但一般缺少動態序列分解分析。Su Bin和Ang[9]認為序列分解提供了每種效應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信息,當研究時期大于五年且投入產出表可得時,序列分解更優。除SDA方法外,其它方法也被用于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的研究,如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分解法(孟明等[10])、DEA-MPI(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分解法(趙國浩和高文靜[11])和計量方法(吳振信等[12])。
盡管SDA可以識別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建議,但未來碳減排政策將轉向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全過程,因此,需要對碳排放進行更深層面的分解,具體識別驅動碳排放變動的產業路徑。然而,現有研究缺少產業路徑層面的分解分析。EIO-LCA(Environmental Input-Output-Life Cycle Assessment)模型可以分析產品生命周期對環境的影響,揭露產業部門經濟活動間的鏈狀關系。其基本思想是將列昂惕夫逆矩陣拆分為關于直接消耗系數矩陣的序列展開式(Waugh[13]),以分析最終需求直接導致的影響(如為滿足居民對電力的直接需求而產生的排放)和涉及中間需求的間接影響(如建筑業對非金屬礦物品的間接需求而引致的排放),但其屬于靜態層面的研究。Wood和Lenzen[14]通過結合SDA,提出了結構路徑分解(Structural Path Decomposition, SPD)分析法。該方法不僅可以識別碳排放變動的具體產業路徑,還可以明確每條路徑上不同因素的變動效應。Gui Shusen等[15]即采用SDA和SPD方法分析了中國1992、1997、2002和2007年25部門碳排放變動的關鍵因素和關鍵路徑,但其所依據的表是國家統計局編制的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不能直接測算最終需求對碳排放的影響(劉瑞翔和姜彩樓[16])。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外經貿關系日益密切,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不能詳細反映研究系統與外部環境間的聯系,所得結果往往存在偏誤,而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更適用于國際貿易發達的經濟環境(陳錫康等[17])。
綜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發現關于中國碳排放變化影響因素文獻存在以下不足:(1)缺少SDA序列分解,缺少從動態角度分析碳排放變化影響效應隨時間推移的變化趨勢;(2)大多學者側重碳排放影響因素分析,針對關鍵影響路徑的分析較少。因此,本文主要貢獻在于:(1)基于1995-2014年中國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和分部門碳排放數據,利用SDA序列分解法研究了中國碳排放增長的影響因素及其動態變遷;(2)利用SPD方法深入挖掘中國碳排放增長的影響因素,以及最終需求背后從上游到下游的完整產業路徑,描繪驅動中國碳排放變動的關鍵部門間的關聯關系,從而促進減排策略更精確地針對特定產業部門或特定需求類型。
本文后續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理論模型及數據來源;第三部分,展示結構分解分析結果,并對結果進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紹結構路徑分解結果并對結果進行討論;第五部分,結論與政策啟示。
2 理論模型與數據說明
2.1理論模型
本文采用中國(進口)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即區分了國內產品與進口產品的中間投入。記A為生產過程中國產品和進口品的直接投入產出技術系數矩陣;F為國內對所有產品(包括國產品和進口品)的最終需求矩陣,包含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Ex為出口向量;X為總產出向量;M為進口向量;C為CO2排放向量。如下表1是(進口)非競爭型經濟-環境投入產出表。

表1 單區域(進口)非競爭型經濟-環境投入產出表
注:右上角標d代表國產品,m表示進口品。
由表1的橫向平衡關系,可得:
AdX+(Fd+Ex)=X
(1)
利用Leontief逆矩陣,L=(I-Ad)-1,(1)式可表示如下:
X=(I-Ad)-1(Fd+Ex)=L(Fd+Ex)
(2)

C=cX=cL(Fd+Ex)
(3)
最終需求(Fd+Ex)可進一步分解為最終需求產品結構ψ、最終需求類型結構δ、經濟規模Y、人口規模P四個因素相乘形式,則式(3)可改寫為:
C=cLψδYP
(4)
其中,ψ為n×d維矩陣,表示基于最終需求的各部門產品結構,元素ψij表示第j類最終需求中第i類部門產品的比例。δ為d×1維列向量,表示各類型最終需求結構,元素δj表示第j類最終需求占國產品總需求的比例。Y為數值,由最終需求與人口規模之比得到。
記比較期CO2排放量為Ct,基期CO2排放量為C0,則該段時期內CO2排放量變化由ΔC=Ct-C0給出。符號“Δ”表示變化量。
根據(4)式可對ΔC進行增量分解如下:
ΔC=C(Δc)+C(ΔL)+C(Δψ)+C(Δδ)+C(ΔY)+C(ΔP)
(5)
則從(5)式可識別出六類因素變動對CO2排放的影響。針對SDA分解形式非唯一性問題,本文采用Dietzenbacher和Los[18]建議的兩極分解法確定各因素的影響。所謂兩極分解方法,就是將從第一個因素開始分解得到的各因素變化對應變量的影響值,以及從最后一個因素開始分解得到的各因素的影響值的平均值,確定為各因素對應變量的影響值。分解形式如式(6):

(6)

(7)
為進一步挖掘中國CO2排放增長影響因素背后的上下游產業關系,根據SPD模型,對中國CO2排放量結構分解模型進行擴展。由于Leontief逆矩陣反映了各個部門最終使用對其他部門產品的完全消耗情況,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直接消耗和經過多個部門的間接消耗:
L=(I-Ad)-1=I+Ad+Ad2+Ad3+…
(8)
由于本文僅考慮國產品的CO2排放,因此接下來將Ad簡寫為A,表示國產品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將式(8)引入式(4),可得:
C=c(I+A+A2+A3+…)ψδYP=cψδYP+cAψδYP+cA2ψδYP+…
(9)
由于引入了Leontief逆矩陣的展開式,根據式(9)對CO2排放的變化ΔC進行增量分解,據此可以考察每一條產業路徑中不同因素所導致的碳排放變化量。
ΔC=(Δc)ψδYP+c(Δψ)δYP+cψ(Δδ)YP+cψδ(ΔY)P+cψδY(ΔP)+(Δc)AψδYP+c(ΔA)ψδYP+cA(Δψ)δYP+cAψ(Δδ)YP+cAψδ(ΔY)P+cAψδY(ΔP)+(Δc)AAψδYP+c(ΔA)AψδYP+cA(ΔA)ψδYP+cAA(Δψ)δYP+cAAψ(Δδ)YP+cAAψδ(ΔY)P+cAAψδY(ΔP)+…
(10)
式(10)中,等式1-5項為CO2排放的一階效應,即某一部門沒有經過中間部門直接流向最終需求的碳排放,如居民消費對電力部門的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變化。等式右邊6-11項為二階效應,可以解釋某一類型的最終需求對某一部門的直接需求所引致的對另一部門的間接需求所引起的碳排放,如固定資本形成對建筑業的直接需求所引致的對非金屬礦物產業的間接需求,所引起的CO2排放為一個二階路徑。三階及其以上影響路徑涉及更多的中間需求。SPD賦予各階影響路徑更細致的內涵,即可以細致分析某一條路徑中碳排放強度、中間投入產出結構、最終需求產品結構、最終需求類型結構、經濟規模、人口規模六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占主導地位的因素和作用方向大小。
2.2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在實證分析中采用了中國1995-2014年中國(進口)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其中,1995-2011年投入產出表來自于2013年WIOD編制發布的表,2012-2014年投入產出表取自于2016年WIOD編制發布的表。為使不同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具有統一口徑,本文對產業部門進行整理,得到具有相同產業部門分類1995-2014年中國34部門投入產出序列表。1995-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數據來自WIOD環境賬戶,2010-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數據采用中國分行業能源消費數據并參考IPCC[19]方法估計得到。中國分行業能源消費數據來源為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需要說明的是,由于WIOD環境賬戶中的碳排放數據不僅僅包含能源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還包括非能源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沒有公布相應年份中國分行業的非能源消費數據,根據1995-2009年WIOD所公布碳排放數據對2010-2014年中國分行業碳排放估計值進行了調整。人口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orld Bank)。
3 二氧化碳排放變化的結構分解分析
3.1驅動因素分析
本部分將根據SDA分解結果(公式6),從動態視角來分析六個不同影響因素對碳排放變化的貢獻。如圖1所示,1995-2014年20年間中國碳排放量呈現了快速增長趨勢,從2723.1 MT(百萬噸)CO2增長至8494.0 MT CO2,增長了211.9%。尤其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碳排放量實現了大幅增長。2002-2014年期間排放量增長了5643.3 MT,占整個研究期間總排放增長量的97.8%。
SDA分解結果顯示,經濟規模擴張是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它導致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增加了220.5%。從趨勢上看,在1995-2002年期間,經濟規模擴張對碳排放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平緩,2002年后,其成為驅動中國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但由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規模的擴張對中國碳排放的拉動有放緩趨勢。在整個研究期間及分階段內,抑制國內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是各部門碳排放強度的下降。1995-2014年期間,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導致碳排放減少了162.0%,但仍不能抵消經濟規模擴大所導致的中國碳排放增長(差額為3376.8 MT)。動態來看,碳排放強度效應促使碳排放減少,2001年后,碳排放強度下降促使碳排放下降的效應進一步增強。
導致中國碳排放大幅增長的第二大因素是中間投入產品結構效應,其變動導致中國碳排放增長了27.8%,原因可能在于排放強度大和資源環境粗放型行業中間投入產品比例上升。雖然中間投入產品結構效應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導致排放增長),但在各分階段內變化較大,在1995-2003年變化幅度較小,2003年以后上升速率加快,2005-2012年穩定在1200 MT左右,但之后又有上升趨勢。人口規模的擴大則使中國碳排放在整個研究期間有所增加(549.0 MT),但其促進作用相對較小,其影響為9.5%。除上述因素外,無論是在整個研究期間還是在各分階段內,最終需求產品結構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這兩個因素的變化對中國碳排放變化的驅動作用不明顯,影響都很有限。此外,我們發現中國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由于受2001年“入世”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規模以及碳排放強度效應都在2002和2008年附近發生變化。這與Gui等的結論類似。

圖1 1995-2014年中國CO2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效應的趨勢
3.2最終需求分析
前文對于中國碳排放變化的分解結果顯示,經濟規模的擴張是帶動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本部分集中討論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以及出口等反映經濟規模的五類最終需求變動對碳排放的影響。圖2顯示,在1995-2014年間,五類最終需求規模的擴大促進中國碳排放增加了13516.6 MT。

圖2 1995-2014年五類最終需求對中國碳排放變化的影響
由固定資本形成、出口和居民消費規模擴大所引起的經濟規模效應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總體來看,固定資本形成是引起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需求來源,它導致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增長了5980.4 MT,占總增長量的103.6%。這與Gui等有所不同,其認為出口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需求,可能的解釋是不同路徑的相互抵消效應。不過分階段來看,2002年前固定資本形成引起碳排放增長量要小于居民消費所引起的排放增長量,但在2002年后固定資本形成需求效應迅速上升,一躍成為促進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需求源,這意味著中國固定資本投資結構存在“高碳化”特征。
出口需求效應則緊隨其后,其變化在整個研究期間使中國碳排放量增加了3225.2 MT,占總增長量的55.9%。動態地看,出口需求效應自2001年中國“入世”后加速上升,并在2004年首度超過居民消費需求效應,成為導致中國碳排放量增加的第二大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制于我國主要外貿市場的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濟持續低迷,外需疲軟使我國出口遭受巨大沖擊,導致出口需求效應在2008-2009年間大幅度下降,意味著中國碳排放存在典型的“國外消費,國內污染”的現象。但2009年后出口需求效應隨著出口回升又重現上升趨勢。
居民消費需求效應也使碳排放量在整個研究期間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其變化引起了3209.4 MT碳排放增加量,占總排放增長量的55.6%。而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需求效應對中國碳排放的推動貢獻作用主要發生在2002年前,之后其推動貢獻有所減弱,但由其變化所導致的絕對碳排放量規模則呈現持續上升趨勢。政府消費需求效應使中國碳排放規模呈現穩定持續上升趨勢,它導致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增長了1014.9MT,占總增長量的17.6%。但從趨勢上來看,由于固定資本形成以及出口規模的大幅增加,政府消費需求引致的碳排放的比重則趨于下降。此外,無論從絕對規模還是從相對比重來看,存貨變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甚微,存貨變動在1995-2014年間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了86.7 MT,僅占總增長量的1.5%,程度非常小。
3.3基于行業層面影響因素分析
在上文對碳排放總量分解基礎上,并且考慮到不同行業之間的碳排放差異,本文進一步深入行業層面,以期找到驅動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深層次原因。表2給出了中國三次產業的碳排放變化情況。不難看出,中國碳排放的絕大部分(89.9%)來自于第二產業,即與第一產業(0.8%)和第三產業(9.3%)相比,第二產業的蓬勃發展是驅動碳排放大幅增加的最重要產業,其導致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增加了5189.7 MT,這也符合一般預期。從具體細分行業來看,在整個研究期間,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以及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占排放變化總量的比重分別為53.8%、11.7%、11.1%,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增長最大的前三個關鍵行業。

表2 1995-2014年中國CO2排放變化分產業的構成分解
注:二氧化碳變化量的單位是(百萬噸),占排放變化總量的比重單位是(%)
進一步對上述三個關鍵行業的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表3給出了具體SDA分析結果。三個行業的結果都說明了排放強度的下降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與碳排放強度效應相反,持續擴張的經濟規模是促進碳排放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完全抵消了碳排放強度下降所抑制的碳排放增長。分部門來看,對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而言,經濟規模變化帶動的排放增長是碳排放強度下降所抑制的排放減少的近兩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中間產品的使用結構以及最終產品的需求結構這兩個因素均使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下降,這意味著該部門中間投入和最終需求結構有“低碳化”趨勢。至于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除碳排放強度效應外,其它五個因素都導致該部門碳排放增長,僅經濟規模效應就完全抵消了碳排放強度下降的減排效應。由前文可知,在1995-2014年間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累計為中國碳排放增長貢獻超過一半,是最大的碳排放部門。經濟規模擴大和中間投入產品結構變動是導致該部門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可以預期的是,該部門可能隨著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碳排放,避免的方法在于能否改善其中間投入結構,從而改善投入結構減少該行業蘊含的CO2。
4 二氧化碳排放變化的結構路徑分解
通過上文SDA分析,我們對影響中國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主要需求類型以及關鍵部門在宏觀層面上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本文進一步剖析各類最終需求影響中國碳排放變化的產業路徑以及產業路徑上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本部分將利用式(10)對中國碳排放變化的產業路徑進行SPD分析。

表3 1995-2014年中國關鍵行業CO2排放變化的SDA結果(百萬噸)
注:表中的百分比是指各因素在1995-2014年間引起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變化總量的比重。
由于三階以上排放路徑影響較小,且涉及中間部門多而復雜,因此,本文對影響碳排放的關鍵路徑分析集中于前三階路徑。通過設定閾值篩選,對1995-2014年影響碳排放增長及減少的前30條關鍵路徑進行分析。表4和表5顯示了結構路徑分解結果。表中,“排放變化”表示在某條產業路徑中因素變化導致碳排放量的變動程度。“階數”代表構成產業路徑的部門數量:如果為1,一階產業路徑表示為“部門1→最終需求”;如果為2,二階產業路徑表示為“部門1→部門2→最終需求”;如果為3,三階產業路徑表示為“部門1→部門2→部門3→最終需求”。“因素”表示導致碳排放變化的作用因素,如式(10)所表述。
4.1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關鍵路徑分析
本小節對促進中國碳排放增加的前30條關鍵路徑進行分析。如表4所示,經濟規模是促進碳排放在1995-2014年間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引起了69.3%的碳排放增長(表中前30條路徑導致的排放增長總量,下同),這再次印證了上文SDA結論,即經濟規模擴張是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一階中間投入結構次之,是推動CO2排放增長的第二大因素(14.5%)。最終需求類別結構和最終需求產品結構這兩個因素分別引起了9.0%和7.1%的CO2排放增長。
前文從最終需求層面對于中國碳排放的SDA結果顯示,由固定資本形成引起的經濟規模效應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大幅度增加的最重要原因(如圖2),因此可以預期固定資本形成是引起CO2排放增長的最主要需求。表4所顯示的SPD結果很好的證實了這一點,顯示在整個研究期間有55.6%的碳排放增長量是由固定資本形成需求拉動的。在1995-2014年間,居民消費規模的變動使中國碳排放增加了32.2%。值得注意的是,與SDA結果不同,表4顯示出口對中國碳排放增長的貢獻僅為7.7%,可能存在如下原因:一是中國出口以制造業為主,其生產工序階段涉及產業部門較多,產業路徑大于三階;二是出口通過三階以內的路徑引致的碳排放增長量較分散,不在閾值選擇范圍內,從而未在本部分的分析范圍中。
接下來,我們對關鍵路徑進行深入分析。由表4可知,經濟規模擴大在路徑“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中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了1286.0 MT,占1995-2014年CO2排放增加量的22.3%,是促進CO2排放增長的最關鍵路徑。其它路徑可作類似解釋。
對表4中路徑總體影響分析可知,“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路徑類型(包括中間部門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涉及路徑1、4和13,對中國碳排放增長貢獻最大,引發的碳排放量占1995-2014年前30條關鍵路徑碳排放總增長量的25.2%。經濟規模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均在這類路徑上起到促進碳排放增長的作用,且均為間接影響。其中,經濟規模擴大在“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固定資本形成”這兩條路徑上引起了1469.1 MT碳排放增加量;最終需求類型結構變動在“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路徑上導致碳排放增長了465.8 MT,是第四大促進碳排放增長路徑。
對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整體影響第二大的路徑類型為“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包括中間部門建筑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涉及路徑5、6、11、14、15、18和22,總共引起了20.4%的碳排放增加量。在這類路徑上,經濟規模、一階中間投入結構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都呈現為間接效應。以一階中間投入結構為例,在“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路徑上,其變化導致中國碳排放在整個研究期間增加了386.2 MT(第5大影響路徑)。

表4 1995-2014年中國CO2排放量增加的前30條關鍵路徑
注:“排放變化”單位是百萬噸。
4.2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的關鍵路徑分析
本小節對促進中國碳排放減少的前30條關鍵路徑進行分析。由表5不難看出,抑制中國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影響因素是碳排放強度。在前30條關鍵減少路徑上,排放強度下降使碳排放量減少了5894.8 MT,占1995-2014年期間碳排放減少總量(表中前30條路徑導致的排放減少總量,下同)的84.5%。這意味著,降低生產工序過程中碳排放強度有利于實現“碳減排”目標。此外,中間投入產品結構、最終需求產品結構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這三個因素變化對減少碳排放作用相對有限,僅涉及路徑4、11、15、19、20和21,引起了13.5%的碳排放減少。需要注意的是,一階中間投入結構(涉及路徑4和21)在降低CO2排放量上亦發揮重要作用,占整個研究期間碳排放減少總量的7.9%。
從最終需求角度看,固定資本形成與居民消費同樣是引起中國碳排放減少的主要需求類型,分別引起了56.3%、30.3%的排放量減少。結合表4的分解結果,我們發現在不同產業路徑層面,固定資本形成與居民消費不僅可以促進碳排放增長還可以抑制碳排放增長。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SDA將碳排放變化完全分解為六個因素的作用結果,而SPD僅僅分析特定因素在特定產業路徑上的作用,是不完全分解,因此使用SDA和SPD方法得到最終需求的結果不同。這也再次印證針對重點碳排放部門和具體部門間流向治理的重要性。
對關鍵路徑的深入分析表明,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在路徑“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居民消費”上導致中國碳排放減少了967.0 MT,占1995-2014年期間中國碳排放總變動量的16.8%,在抑制碳排放增長的關鍵路徑中排序第1。
從路徑整體影響來看,“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路徑類型(包括中間部門建筑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以及機械和設備制造業,涉及路徑3、5、7、10、20和29),對中國實現“碳減排”目標助益最大,上述路徑減少碳排放量占前30條路徑總和的23.8%。碳排放強度和二階中間投入結構均在這類路徑上起到促進排放減少的作用,且都為間接影響。其中,二階中間投入結構變動在“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路徑20上減少碳排放量115.1MT,占CO2排放減少總量的1.6%。除上述路徑20外,碳排放強度下降通過其余3、5、7和29路徑一共減少了CO2排放1544.2 MT。以路徑3為例,碳排放強度變化在“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路徑上使中國碳排放減少566.2 MT,為第三大促進碳排放減少的關鍵路徑。
對“碳減排”整體影響第二大的關鍵路徑類型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包括中間部門建筑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涉及路徑2、4和12,在1995-2014年期間貢獻了21.0%的CO2減少量。碳排放強度和一階中間投入結構這兩個因素變化在該類路徑上促進CO2排放減少1467.4 MT。具體來看,碳排放強度下降在“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路徑上減少CO2排放878.0 MT,為第2大促進“碳減排”的關鍵路徑;一階中間投入結構變動在路徑“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建筑業→固定資本形成”上抑制碳排放增長440.0 MT (第4大影響路徑)。

表5 1995-2014年中國CO2排放量減少的前30條關鍵路徑
注:“排放變化”單位是百萬噸;部門3列中“電燃水”為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縮寫。
綜合上述中國碳排放變化的關鍵路徑(如表4、5所示),從關鍵路徑涉及的重要部門來看,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以及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等四個產業部門在1995-2014年期間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較大。而Gui等分析認為,影響中國碳排放關鍵路徑涉及非金屬產品部門、電力部門、金屬冶煉業、建筑業以及機械制造業等部門,與本文分析結果相類似。
從關鍵路徑的整體影響來看,SPD結果表明,“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和“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這兩類路徑類型在1995-2014年間分別對中國碳排放增長和下降影響最為顯著。并且在上述兩類路徑上,經濟規模擴大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變動促進CO2排放增加的效應大于碳排放強度下降的“碳減排”效應,因此上述兩類路徑總體上導致了中國CO2排放量的增加。
5 結語
本文基于中國(進口)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和分部門二氧化碳排放數據,運用結構分解分析和結構路徑分解方法,對1995年至2014年中國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及其關鍵路徑進行了研究。綜合上文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與政策啟示:
(1)SDA實證結果顯示,在整個研究期間及分階段內,經濟規模擴張是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抑制國內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則是各部門碳排放強度的下降,但是持續擴張的經濟規模完全抵消了碳排放強度下降所延緩的碳排放增長。此外,中間投入產品結構的變動則進一步推動中國碳排放的增長。除了上述因素外,最終需求產品結構、最終需求類型結構以及人口規模這三個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化的影響有限。
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經濟規模擴大帶來的碳排放增長具有剛性。因此,中國控制碳排放增長并不意味著要盲目地通過抑制經濟規模的擴張來減少碳排放。而碳排放強度下降對CO2排放減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同時碳排放強度的減排效應還不能彌補經濟規模對碳排放增長的促進作用,因此通過有效政策進一步降低碳排放強度來實現碳排放減少目標是可行的。包括改善能源需求結構,鼓勵生產和消費清潔能源;與擁有先進節能技術和清潔生產技術的發達國家合作,請求技術援助,引入新可再生的綠色能源生產技術。另外,中國還應優化中間產品投入結構,引導生產部門減少對高排放產業部門產品的投入和需求。
(2)由于SDA將碳排放變化完全分解為六個因素的作用結果,而SPD僅僅分析特定因素在特定產業路徑上的作用,是不完全分解,因此SDA和SPD方法關于最終需求的結果不同。SDA結果表明,固定資本形成和出口擴張引起的經濟規模效應是導致中國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但考慮到SPD結果,居民消費同樣是延緩中國碳排放增長的主要需求類型,因而與居民消費有關的產業路徑不容忽視。SPD結果表明外貿增長并非導致中國碳排放增長的最主要原因,居民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規模的持續擴大才是驅動碳排放增長的動因。
盡管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增長主要是由于需求規模擴大引起的,但減少碳排放不等于壓制需求增長,而是促進需求增長模式的轉變,逐漸優化最終需求產品結構,并通過需求產品結構變化控制需求引致的碳排放增長。具體而言,可通過適當的財稅政策及宣傳教育在居民中倡導可持續消費模式和綠色生活方式,優化居民消費結構;鼓勵出口附加價值高而碳排放強度低的產品或服務,如住宿和餐飲業以及批發和委托貿易業等等;利用資金和優惠政策引導對長期綠色的項目的投資,減少物質性投資以優化固定資本形成需求結構等。
(3)從重要部門和產業路徑層面分析發現,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以及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等四個產業部門是導致中國碳排放變化的重要部門,主要依靠碳排放強度的下降來延緩碳排放增長。1995-2014年研究期間,“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和“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中間部門)→固定資本形成”這兩類路徑類型在1995-2014年間分別對中國碳排放增長和下降影響最為顯著,經濟規模擴大和最終需求類型結構變化促進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大于碳排放強度和中間投入產品結構變化的減排作用,因此這兩類路徑均在整體上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
政府應加強對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以及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等高排放部門的監管,并通過適當的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限制其碳排放規模擴大。具體包括加大對這些部門節能減排的技術支持,鼓勵企業部門加大對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力度,推進其進行技術設備更新換代。對于關鍵路徑而言,應從各個影響因素著手,針對上下游部門綜合治理,如優化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以及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的能源使用結構,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碳排放強度,提高上述兩個上游部門對建筑業等中間部門的投入產出效率,優化對上述部門的固定資本投資等。
[1] Peters G P, Weber C L, Guan Dabo, et al. China's growing CO2emissions: A race between increasing consumption and efficiency gai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7, 41 (17):5939-44.
[2] Guan Dabo, Hubacek K, Weber C L, et al. The drivers of Chinese CO2,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30[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 18(4):626-634.
[3] Fan Ying, Liu Lancui, Wu Gang, et al. Changes in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a: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1980-2003[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2(3-4):683-91.
[4] Zhang Youguo.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sources of decarbon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2-2006[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8-9):2399-2405.
[5] Geng Yong, Zhao Hongyan, Liu Zhu, et al. Exploring driving factors of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in Chinese provinces: A case of Liaoning[J]. Energy Policy, 2013, 60(6):820-826.
[6] Tian Xin, Chang Miao, Shi Feng, et al. How doe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mpac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cusing on nine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4, 37(3):243-254.
[7] 趙忠秀, 裴建鎖, 閆云鳳. 貿易增長、國際生產分割與CO2排放核算:產業vs.產品[J]. 中國管理科學, 2014, 22(12):11-17.
[8] 張友國. 中國貿易含碳量及其影響因素-基于 (進口) 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的分析[J]. 經濟學季刊, 2010, 9(4): 1287-1310.
[9] Su Bin, Ang B W.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pplied to energy and emissions: Aggregation issues[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12, 24(3):1-19.
[10] 孟明, 牛東曉, 許曉敏. 經濟轉型過程中資源依賴度演進路徑分解模型研究[J]. 中國管理科學, 2016, 24(3):18-23.
[11] 趙國浩, 高文靜. 基于前沿分析方法的中國工業部門廣義碳生產率指數測算及變化分解[J]. 中國管理科學, 2013, 21(1):31-36.
[12] 吳振信, 謝曉晶, 王書平. 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分析——基于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J]. 中國管理科學, 2012, 20(3):161-166.
[13] Waugh F V. Inversion of the leontief matrix by power series[J]. Econometrica, 1950, 18(2):142-154.
[14] Wood R, Lenzen M. Structural path decomposition[J]. Energy Economics, 2009, 31(3):335-341.
[15] Gui Shusen, Mu Hailin, Li Nan. Analysis of impact factors on China's CO2, emissions from the view of supply chain paths[J]. Energy, 2014, 74:405-416.
[16] 劉瑞翔, 姜彩樓. 從投入產出視角看中國能耗加速增長現象[J]. 經濟學:季刊, 2011, 10(3):777-798.
[17] 陳錫康等. 投入產出技術[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18] Dietzenbacher E, Los B.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Sense and sensitivity[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998, 10(4):307-323.
[19] Intergo o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tudyonDrivingFactorsandCriticalSupplyChainPathsofCO2EmissionsinChina
XIERui,WANGZhen-guo,ZHANGBi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China)
As the world’s largest emitter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hina has promised to reach its peak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or earlier, thus facing a major challenge on aspect of emission reduction for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To efficiently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 it’s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actors as well as the critical supply chain paths that drive changes in life cycle CO2emissions and aid both policy makers and decision makers by enabling the tracing of the change in key production chains over tim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1995-2014 linked Chinese environmental non-competitive (import) input-output table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and structural path decomposition (SPD) methods a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v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and extract critical supply chains involved in changes in CO2emissions over this study period. The IO tables and historical carbon emissions data by sector for China range from 1995 to 2014, extending over a 20-year study period. The influence on changes of CO2emissions derived from final demand is composed of six factors: sectoral emission intensity (c); intermediate input product structure (L); product structure of final demand (ψ); category composition of final demand (δ); per capita final demand (Y), and population (P). The detailed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er capita final demand is the dominant driving factor in China’s CO2emissions growth, while the change of emission intensity of production in China greatly offset the growth of emissions, and intermediate input product structure further lead to emissions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paths, the top ranking path affecting CO2emissions is identified to be “non-metallic mineral industry→construction→fixed capital formation”. We also find that the supply chain paths with the largest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overall impacts are “non-metallic mineral industry→fixed capital formation”, and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supply→fixed capital forma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CO2emissions and boost supervision of critical emissions supply chain paths, offer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s for the policy makers and decision makers reasonable measures that can be applied progressively to aid in China’s carbon abatement in reality.
1003-207(2017)10-0119-11
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7.10.013
F061;X32
A
2016-07-01;
2017-05-1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673083,71303076,71420107027);湖南省科技計劃軟科學重點項目(2015zk2002)
謝銳(1983-),男(漢族),江西人,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氣候變化與碳排放,E-mail:xrxrui@126.com.
Keywords: CO2emission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tructural path decomposition; driving factors; critical supply chain p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