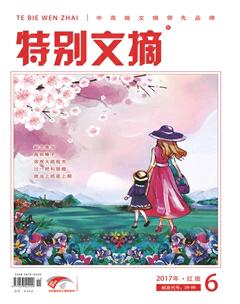皇糧難吃
汪朗
中國的官吏,很早便有皇糧可吃。
春秋戰國時,秦國官員的收入主要是實物,按官職大小配給糧食,作為工資。一年領取皇糧一百石以上的為“有秩吏”,已進入干部序列;能掙到六百石以上者,則屬于“顯大夫”,相當于現在的高干了。當時要了解干部的級別,辦法十分簡單,只要看看該人吃多少皇糧就行了。低級官吏的年薪不過五十石,高的可達千石。
秦漢年間,中國北方的主要農作物是粟,即谷子,因而支付官員的糧食也以此為基準。可百姓繳納的皇糧雜七雜八的什么都有,為了統一工資標準,國家制定了專門的法律,明確各種糧食折合成粟的比例,省得官員攀比。《秦律·倉律》中便規定,稻禾一石,可以抵頂粟二十斗;大豆、小豆和麻籽,“十五斗為一石”。由此可見,當時的稻谷還是挺金貴的,小雜糧卻不怎么吃香,和現在的行情不同。
吃皇糧人數最多的大概要算清朝。除了文武官員外,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無論當不當兵,做不做事,都能領一份錢糧,俗稱“鐵桿莊稼”。京城旗人多的時候有六十多萬,為了供養這眾多的人口,朝廷在北京東城建了十三座大糧倉,專門儲存從南方運來的米糧。如今這些糧倉雖然不復存在,但名稱卻還保留著,包括祿米倉、南新倉、北新倉、海運倉等。
吃皇糧的閑人多了,正經干事的俸祿自然就少了。清朝京官,一品年俸不過白銀180兩,二品155兩,最低的九品只有35兩。每兩俸銀同時配給俸米一斛。到了咸豐光緒年間,國庫吃緊,京官工資還要打八折,日子更加清苦。好在只要人在官場,辦法總是會有的。
清代中期有一官員名叫張集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任命為陜西督糧道,負責征收皇糧供應軍隊,一年要收米豆麥二十萬石,發放十九萬多石,結余歸己。陜西糧道是全國著名的肥缺,據說一年有三四十萬兩銀子的進項。不過,張集馨的親身體會是只有六萬多兩,而且還有許多固定開銷。
其中,要給官員送禮:“駐軍將軍三節兩壽(即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以及官員和夫人的生日),糧道每次送銀八百兩,有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一次。兩都統每節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八旗協領八員,每節每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將軍、都統又薦家人在倉,或掛名在署,按節分賬。撫臺分四季送,每季一千三百兩,節壽但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制臺按三節致送,每節一千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差家人赴蘭州呈送。”此外,來往西安的官員吃飯、聽戲的費用,饋送的盤纏,都要由糧道負責,一次大約二百兩銀子,“通計每年用度,連京城炭敬,總在五萬金上下,而告幫告助者不在其內。每年入項約六萬金,再除私用,亦無復多余”。
張集馨送禮名單上的官員,既有將軍、都統等軍隊領導,也有陜西巡撫(撫臺)和陜甘總督(制臺)等行政上司,這些人收受的禮金,屬合法收入,不必擔心受到查處。當時的陜甘總督,就是林則徐。看來只要官做得夠大,各種皇糧都會有的,是不是肥缺并不重要。
清朝的皇糧多為老米。官倉的稻谷長期存放之后,顏色轉黃,米質變糟,這便是“老米”。雖然屬于變質食品,但管倉者照樣發放:白給的東西,愛要不要。老米原先只是沒錢人家才吃的,畢竟聊勝于無。后來,有人研究發現,具有皇家特色的老米通過長年存放,去了油性,既開胃又爽口,比新米還要好吃。此“老米優越論”一出,迅速得到響應,就連皇上都把老米擺上了餐桌。光緒七年元宵節那天,萬歲爺一天三頓飯,頓頓都有“老米膳、老米溪膳”。由于最高當局倡導,老米頓時身價百倍,一些糧行還專門向貧困八旗人家收購未到期的米券,到期后到官倉領取老米再轉售給那些慕名求購者,售價比新米還要高。
大清國一完,老米也跟著掉價,雖然還有遺老遺少留戀這一口兒,但一般人家是不再問津了。離開皇糧,起碼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如今,如果有誰再把變色發糟的老米拿到市場上兜售,肯定會被扭送到工商局,告你出售劣質商品,危害大眾健康。世上許多事情,是不可以隨意刮風的,一刮風,難免把老米這樣的糟粕當作精華,鬧出笑話。
(摘自《衣食大義》中國華僑出版社 圖/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