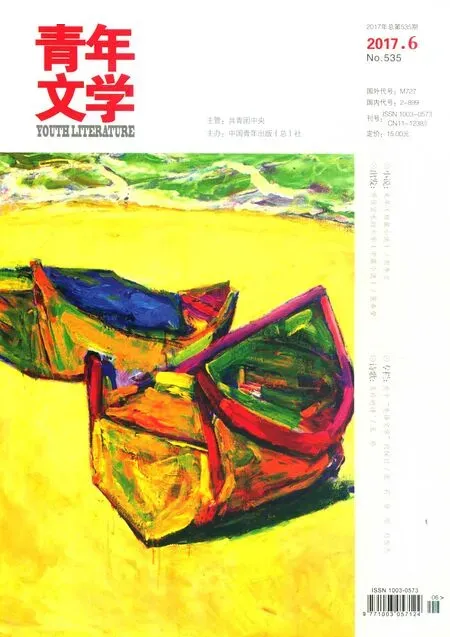為“先鋒文學”注入現實的活力
——以斯繼東小說《西涼》為例
▲趙振杰
為“先鋒文學”注入現實的活力——以斯繼東小說《西涼》為例
▲趙振杰
自“先鋒文學”進入當代文學史以后,一九八六年便被欽定為先鋒元年。此后每隔十年,文學界便會有組織地開展一系列大型紀念活動。近兩年為紀念“先鋒文學的第三十年頭”,以回顧、總結、反思為名目的的文章層出不窮。值得一提的是,諸多學者、評論家在承認先鋒文學巨大的歷史貢獻的同時,也從客觀、公允、歷史化的角度指出了先鋒文學存在的弊端和短板。其中批評較為集中的一點是,作為當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先鋒文學,成也“形式”,敗也“形式”。先鋒文學在極力張揚文本實驗的“純粹性”的同時,不可避免會忽略掉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意義問題。正如楊慶祥尖銳指出的那樣:“我們從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作品中幾乎讀不出八十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的。”當時的中國是何面貌?國人擁有怎樣的生存感受?知識階層具備怎樣的“自我意識”?……這些原本并非“先鋒文學”單獨面對的問題,卻因其對文學形式上“純粹性”的過分強調而被放大成為一個迫切的、棘手的、不可回避的問題。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先鋒文學中“現實的缺失”問題,在阿乙、曹寇、弋舟、李浩、斯繼東等一批七〇后作家的“后先鋒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及時的矯正。他們一方面延續了先鋒文學在形式實驗與敘述歷險上的探索,另一方面有意識地將國民情緒與時代癥候灌注于先鋒敘事之中,從而使其作品普遍呈現出荒誕的現實感與現實的荒誕性。為了更好論證上述觀點,不妨以斯繼東的小說《西涼》為例。
斯繼東的小說創作向來具有極強的探索實驗性,其短篇近作《西涼》亦不例外。該小說采用意識流和記憶拼貼的敘事方式,講述了一位情場失意的富家“京漂女”飯粒與網友卡卡、前男友田一楷之間復雜而又微妙的感情糾葛。文本敘事脈絡看似信馬由韁、散漫無章,實則別出心裁、匠心獨運。作者一方面以游戲的筆墨肆意虛構了一段類似柏拉圖式的愛戀,另一方面又以“元小說”的敘述者口吻對“愛情烏托邦”本身進行著任性的拆解與重組。《西涼》與其說是在敘述一場愛情歷險,毋寧說是在呈現一場事關愛情的敘述歷險。
在這場敘事歷險中,主人公飯粒最后是乘坐飛機前往西涼的,然而,帶領我進入《西涼》的卻是那“最后一班地鐵”。小說中有這樣一句并不起眼的敘述:“而飯粒還得趕最后一趟地鐵”。由于這句話在文本中不承擔隱喻功能,對于故事情節進程也并無推動作用,因而,被多數讀者忽略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于我個人而言,這句看似可有可無的陳述卻像一把被作者故意藏匿在角落里的鑰匙,它可以為我們打開那扇通往作者寫作意圖和文本闡釋空間的密室之門。
斯繼東是否看過特呂弗拍攝的電影《最后一班地鐵》,我不得而知。但在審美追求和藝術主張上看,他的確與那位法國“新浪潮”導演趣味相投:他們都十分強調作品的個性化和內向性,在講故事的同時更加注重故事的講述方式。單就內容而言,小說《西涼》與電影《最后一班地鐵》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后者講述的是“二戰”中的法國,一位出逃未遂的猶太戲劇藝術家被迫躲藏在自家劇院的地窖內指揮舞臺上話劇進展的故事;而前者則是在講述現代都市女性飯粒的情感遭際,及其對純粹愛情的浪漫幻想。但是,在敘事結構、美學風格上,兩者卻存在著某種異質同構的相似性。《最后一班地鐵》以戲中戲的結構統攝全局,影片結尾處,幕后“導演”走上舞臺與男女主演一同鞠躬謝幕,瞬間瓦解了影片故事的“真實”性,給讀者帶來一種“人生如戲”的夢幻感。斯繼東將這種藝術技巧運用得更加隱蔽,更加純熟。小說《西涼》自始至終是以QQ聊天的方式來展開敘事,并通過視角的自由轉變、時態的頻繁切換,建構起多個對話場域,如人物之間的對話、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人物的自我獨白、作者的夫子自道等等。小說中的敘述者就如同《最后一班地鐵》中那位藏匿在地窖內的藝術家,只借助這些彼此交叉的對話場域來把握筆下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情感動向。當飯粒為卡卡講述完自己如何色誘快遞哥的故事后,小說有這樣一組對話:
換好水,簽好單,小伙子就走了。
就這些嗎?就這些。對了,走之前他還喝了那杯橙汁。
可是,就算她真跟李敏搞上床,又怎么了?……不管她跟誰上床,輪得到你卡卡來指手畫腳嗎?
由于缺少必要的主語限制,說話者身份變得異常含混、豐富。讀者既可以將其理解為是飯粒與卡卡的QQ聊天,也可以看作是飯粒的內心獨白,抑或是敘述者的畫外音。這樣的對話在《西涼》中反復出現,顯然是作者的有意為之。
最耐人尋味的一組對話出現在小說結尾處。當飯粒先后失去寵物貓“拖鞋”和快遞哥馬家俊這兩個精神伴侶后,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有必要進行一場前往西涼的“說走就走的旅行”。這時出現一組對話:
噢,對了,出門前千萬別忘了給鋼琴老師告個假,否則老師一準生氣。
下了飛機,也許真的可以給馬家俊打個電話。
干嗎?
不干嗎,就是見個面聊聊唄。順便,順便把啟瓶器送給他吧。
如果我們細加分析,會發現作者是將前面所提到的兩組充滿張力的對話場域——人物之間的對話和主人公內心獨白——融合在同一組敘述空間內,從而建構起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撇開主人公內心獨白不談,倘若我們將上述對話雙方依舊看作是飯粒和卡卡的話,就會驚訝地發現,整篇小說都是在兩人的QQ聊天中完成的。因此,我們就有理由懷疑所有有關“快遞哥”的故事情節都可能是飯粒為欺騙或刺激卡卡而杜撰出來的。小說結尾處所蘊含的強大拆解力與《最后一班地鐵》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瞬間將那些看似真實確鑿的敘述重新還原為一個個有待推敲與解答的謎團。主人公飯粒的人物性格就在這種一虛一實、似真似幻的敘述中凸顯起來。
面對愛情,飯粒既是一個懷有潔癖的浪漫主義者,又是一個心灰意懶的虛無主義者。與前男友田一楷和網友卡卡之間的藕斷絲連、分分合合,讓她真真切切地體會到“真愛”的易腐和虛妄。然而,寵物貓“拖鞋”、郵遞哥馬家俊的出現與消失,又使她無法自拔地陷入“貓與魚之戀”的幻想與悵惘之中。她就像個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一方面渴望著“魚七貓九”童話愛情,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童話里都是騙人的”。“魚忘七秒,貓死九命”的美好傳說如同一面反諷鏡像,恰恰折射出飯粒真實的情感狀態:看似自由自在,實則百無聊賴;渴求死而復活,實則痛不欲生。那些不堪回首的情感記憶,就像是一塊塊長在她心口的瘡疤,不碰它會癢,揭下來又會痛;而那個寄托著飯粒“純真情感”的郵遞哥,也不過就像是家里的那柄漂亮的“全金屬啟瓶器”一樣,原本可有可無,一旦擁有后便再也割舍不下。
從文本的形式技巧角度看,斯繼東的《西涼》似乎延續了“先鋒文學”的敘事套路;然而,有所不同的是,《西涼》所要傳遞和表達的是當今時代普通青年普遍存在的情感狀態和精神景觀,即一種充滿虛妄的小幻想,一種底色陰郁的小溫馨。這是現代人的個人經驗表達,也是都市青年的群體性情緒抒發。在斯繼東這里,文學既不產生于自我,也不產生于外部世界,而是產生于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共振中。正是在這種共振中,其作品的形式先鋒性與主題真實感實現了有機融合。以管窺豹,我們不難從《西涼》中看出當代中國先鋒文學在敘事主題、敘事方式、敘事內容等方面的歷史變遷與時代印記,即七〇后一代作家的“后先鋒文學”已經從先鋒文學前輩的“敘事圈套”“語言迷宮”“文本碎片”中脫身,逐漸走向了個人日常經驗與社會情緒、精神癥候彼此共生的藝術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