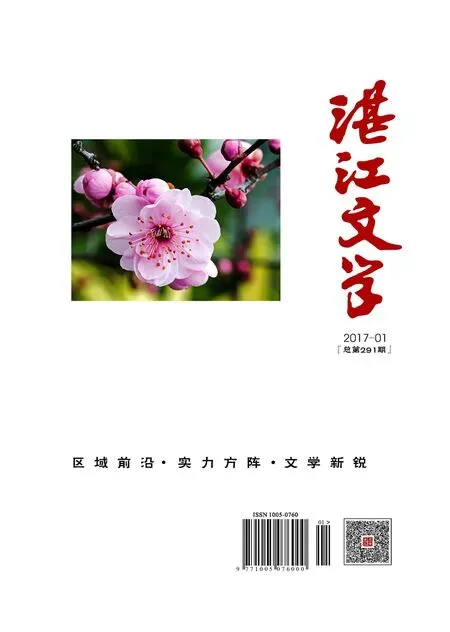舊傷口,青春剪輯的灼痛
※ 范燭紅
舊傷口,青春剪輯的灼痛
※ 范燭紅
一
如同舊時年月里緩緩流動的暖,眼前這座浸瀝著風雨的石橋佇立在老城外洶涌的河流之中,在慘白的光線里暗自細數著塵封的功績與厚重的往昔,這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令我的眼睛撫過舊物上的時光而疼痛不已。
那年夏季的一場洪水肆虐了家鄉的田園、道路、房屋以及暑期結束就要到鄰市讀書求學的少年的心靈。那時的我早已被升學的喜訊弄得飄然忘物,整日只知道劃著竹排悠然鳧于四處泛濫的洪水之上,捉魚、網蝦、采蓮蓬,或者是什么也不干,就那么漫無邊際地劃著,正如面對即將啟程的全新而茫然的人生之旅。當災難突如其來,大多數天真無邪的孩子都是一樣的懵懂無知,在父輩們揮汗如雨重建家園的號子里,我們甚至是很欣喜地夾雜在人群里幫著戽水、搬磚頭、運石子,而更多的關于未來的擔心或說憂患似乎與水底的斷壁殘垣、腐爛的稼禾一起悄然沉睡,全無醒來的跡象。
為了籌集七千多元的學費,父親變賣了所有值錢的家當,耕牛、稻谷、陳年的木料,包括救災下發的部分口糧與果蔬。不知父親后來是如何湊齊了這筆錢,開學那天他將我送到距家數百里之遙的學校,回去的那個晌午,我陪著他一路走至橋頭。那一刻,烈日炙烤著柏油路面,也烘干了我長久浸水的身體和父親腳上那雙破爛不堪的膠鞋。父親說回去吧記得安心學習,然后就走上了眼前這座長長的石橋。望著父親漸行漸遠的背影,我的眼睛倏地噙滿淚水,父親的脊背何時已佝僂成微拱的石橋!手扶鏤空的護欄,聽著橋下傳來的湍急的水流聲,我清晰地意識到這座石橋真實的存在與分量——它堅強的身軀夜以繼日所承載的重荷。
我攥緊拳頭想,等我畢業了,我就可以成為一座新的讓家人走出苦難的橋梁!然而,如今多少年過去了,我除了僅能自食其力之外又為家人做了些什么呢?當年豪言壯語里的橋梁已被歲月的洪流擊垮,慚愧的是,我還能如此心安理得地無視那垮塌局面的凄慘,或許是骨子里早就斷了再建的念想吧。時至今日,當我也成了一個孩子的父親,當我為了生計選擇在這個老城定居,當我每天開著車子送兒子去學校時途經此橋,驀然間我發現自己未曾放飛的希冀漸被如麻的瑣事所羈絆,原本清澈的眸子里折射出的安寧也漸被塵事的喧囂與煙云所襲擾和蒙蔽……
那注定是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青澀時代,那是一座穿越了多少個陰晴寒暑并且鐫刻著曾經的友情的石橋。永不忘畢業前夕那個寂寥的夜,我們三個曾經患難與共過的兄弟來到校園的香樟樹下,約定二十年后的某月某日無論各自境況如何都要再聚首一次。我們慎重地將見面的地點選定在石橋上,因為我們相信不管歲月怎樣變遷,這座歷史悠久、結構堅固的石橋絕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于河流之上。
而今,光陰已如白駒過隙,石橋待在原地未曾移動腳步,只是我們先前的約定,早已幻化為時空片段里的泡影。我無法斷定到底是生活本身即是如此的令人捉摸不透呢,還是生活早在很久以前就毫無保留地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隱喻:我們一行三人,一人在畢業三年后的秋天就喝農藥尋了短見,其間的原由大抵是難以抵御家庭的紛爭與社會的誤解所帶來的壓力;另一人在沿海某大城市啟動了波瀾壯闊的個人奮斗史,業已開起了公司購置了豪車豪宅;然后就是我,至今蝸居在城市的一隅,時而為生計奔走打拼,時而像這般流連在當初約定見面的石橋邊,凝望、聆聽或沉思,并由此滋生出一些或明或暗無關痛癢的文字。
凡此種種,非關石橋。當下,青春里的灼痛慢慢沉淀,晦暗莫名的日子按既定的節奏已然走遠,卻徒留幾聲慨嘆與一連串的拷問:是生活的粗糙漸次消磨了我們起初的鋒芒與激情,還是我們躁動輕浮的心性早就誤讀且傷害了原本美好的生活?
此刻,我只能參悟到一種象征生活的意象在目之所及的載體上跌宕起伏,猶似生命里奔騰不息的汩汩暖流。也或許,迂回與放下未嘗不是對生活的一種正視,一如我在石橋邊輕撫記憶里的舊傷口,抖落一身歲月累積的塵埃……
二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斑斕的歲月仿佛由一些錯落的畫面剪輯而成:走過花事迷離的季節,身后凌亂的腳印漸次變得模糊不堪,唯有片片凋落的花瓣飄忽于時光的深處,像一些人心頭揮之不去的碎念和憂傷。
繁華已然落幕,但心靈的震顫猶在。彼時,一盆盆花草被擺置在校園的顯眼處,或含苞待放,或迎風招展,皆以一種率真而自由的方式裝扮著每一個明媚的白晝,也在許多個孤寂的夜晚點綴著一些人最初的夢靨。
那年春天,為了迎接上級領導的視察,學校特意從市里的苗木公司購買了一大批花草,用來美化校園。數個雙休日,我與小武被抽調留校加班:讓鮮花進駐每一個需要的角落。小武大學里修過園林設計,頗有些造詣,便自告奮勇地攬下重任。其時我是他的助手,偶爾會給他提點建議,但彼此合作起來算不上默契,期間因理念不同還產生過一些爭執,全都是我向其妥協。我想,但凡有思想有才華的人,性格多少有些孤傲,并非不諳世事,大可不必為之糾結。
老家遠在鄰省的小武走上工作崗位才兩年,剛剛失戀,但生活里正昂揚著詩意與遠方。我已過而立之年,不再茍同未知的風雪是人生的歷練。
傾注心血的設計沒有白費,上級領導雖是匆匆一瞥,卻也對此褒獎不斷。慶功宴上,小武喝得酩酊大醉,仿佛只有如此,才有氣力去抵抗之后那漫長的被人遺忘的冷卻期。當我們回到先前的生活軌道,小武開始變得郁郁寡歡,對于一些人際圈子,他討厭加入,本能地排斥著那種“入鄉隨俗”的觀念。那些盛綻過后已無利用價值的鮮花,日漸凋零,誰也無法阻擋。
心疼之余,小武再次用自己的雙手去撫慰那些受傷的精靈。澆水、增肥或添土保暖,過往的愛與希望分明碎成一地,或許他是在期待另一種形式里的孕育?
非議接踵而至。心力交瘁的小武索性順了人心,從辦公室搬至樓道內的貯藏間辦公。他無所畏懼,聲稱自己有更多的閑暇同那些奄奄一息的花草共度朝夕。
而我未再參與其中,縱使我的內心也在忍受類似的折磨。那段時日,因不愿仰仗某些人的鼻息而活,我甘愿被其采取所謂的邊緣化。我倔強地認為,其實孤獨并不可怕,只要你明白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再多的困頓也難以紛亂一顆強悍的心。至少,我會矢志不渝地保持課堂上應有的溫暖和深度。
好在事過境遷,生命里的傷痛已悄然結痂,然后慢慢凝固成了時光里不可或缺的暖。
花開花謝,夢已成歌。多年之后,小武歷經考研、讀研,憑著一身執著的闖勁,業已成為南方某著名政法大學里最年輕的副教授,且著作豐碩。而我,也終究離開了那個令人傷感的冷漠之地,于散場的擁抱之后,依舊以一顆熾熱和虔誠之心,在新的天地里自由地諦聽花兒的絮語與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