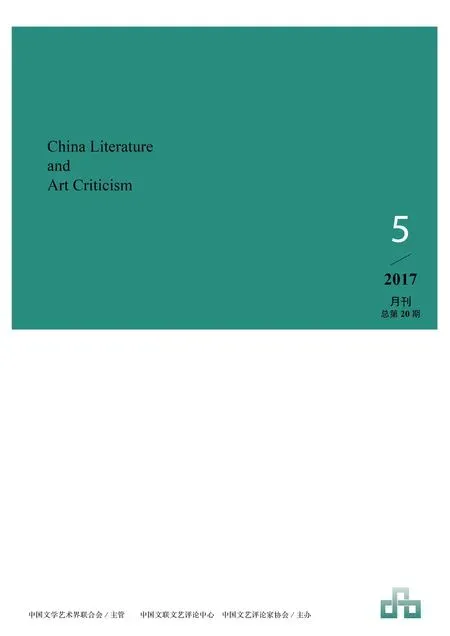不要誤讀戲曲文學的“地域性”
周津菁
不要誤讀戲曲文學的“地域性”
周津菁
編者按:真理越辯越明。發揚文藝評論的批評精神,改善文藝評論的生態,提升文藝評論的說服力,有賴于圍繞有價值的學術問題開展討論與爭鳴。從本期開始,本刊開設“學術爭鳴”欄目,歡迎廣大文藝評論家和專家學者積極參與。
本文對目前文藝理論界正在熱議的“地域戲劇題材”問題作了回應,以隆學義川劇文學創作為例,討論了戲曲文學創作與“地域性”題材之間的復雜關系。戲曲文學作品呈現效果的關鍵并不在于“本地域”或“彼地域”的“二元選擇”,而在于特定題材對地方戲曲藝術形式的具體適應性。
隆學義 川劇 戲曲文學 地域性
在為國家藝術基金做三年總結之際,評論家傅謹提到:“從題材角度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劇團和藝術家在題材選擇上愈益趨于地方化和狹隘化,似乎不選擇表現本地區的歷史文化名人或當代英模就無法向當地政府交代,嚴重制約了藝術的發展空間。”。學者李紅艷也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她于2016年10月,在《中國文藝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戲劇創作地域題材應降溫》的文章。兩位評論家都談到:在地方文化功利論、政績觀的影響下,舞臺藝術作品在選材上日益狹隘,這嚴重影響了原創者藝術哲思的高度和廣度,制約了戲劇藝術水平的提升。這是針對目前藝術界廣泛存在的“地域題材熱”現象提出的中肯之語。但是,我們在反對“地域題材”的褊狹性和功利性的時候,還應當警惕另一種聲音,就是用“二元對立”的態度看待“地域題材”的問題,即走向問題的另一端,認為但凡是“地域題材”的,就都不好,就都要反對。這種看法,也是不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
我認為,戲劇作品藝術水平和思想境界的高度,并不完全取決于它的“地域”指向。首先,主創者看待題材的角度,編、導、演的水平,藝術院團的存量積淀,都會影響作品的呈現水準。而回到“地域”問題上,“地域”的,是族群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是由一個一個人類片區組合而成,此“地域”與彼“地域”,小“地域”與大“地域”并無好壞之分。莎士比亞戲劇是英國“地域”的,日本能劇是東瀛“地域”的,布萊希特是德國“地域”的,沒有“地域”文化就沒有世界文化。而作品的好與壞,與它的用材并無直接聯系。世界戲劇沒有“通用”的題材,但有“通用”的價值:有的人用了“地域”題材,卻沒有做出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有的人沒有用“地域”題材,卻用本土藝術的形式,做出了戲劇的生命力,能撥動全人類的思想和弦,讓作品具有了超越文化的魅力;還有人用了“地域”的題材,結合得天獨厚的“地域”藝術形式,奉獻出了能為世界文化所理解和接受的文化營養。戲劇的好壞,在于它挖掘主題的深度,點染人物的亮度和展示情感的力度,題材只是材料,做大餐的手藝才是關鍵。談到戲曲,我們似乎還應當關注地方戲曲劇種的藝術特性問題,外來的題材雖好,卻不一定適合本土戲曲劇種——用本地的方言、音樂和人物形態去表達。
劇作家隆學義先生的幾個作品對于討論“地域”題材問題頗有啟發。隆學義先生于2015年2月去世,他畢生創作了十余個川劇劇本,主要有《金子》《鳴鳳》《白露為霜》《東坡先生》《草民宋世杰》《貂蟬之死》等。他根據曹禺原著《原野》改編創作的川劇《金子》,入選首屆“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并榮獲了包括文華大獎、中國藝術節大獎、中國戲曲學會獎在內的各類大獎34項。隆學義先生碩果累累,在現代川劇劇作家中具有代表性,而他的創作經歷和成就表明,戲曲文學題材的“地域”性是一個復雜的,與多種舞臺因素縱橫交錯的問題,并不是簡單的“放棄”或者“死守”,就能獲得最佳的舞臺作品。
隆學義先生是一個改編大家,他的作品有改編自巴蜀“地域”文化之外的《金子》《白露為霜》等,也有改編自本土文學作品的《鳴鳳》和以川渝“地域”人物為原型創作的《布衣張瀾》等。這些本土和非本土的文化內容,無一不通過川劇這種藝術形式進行表達。隆學義畢生都在嘗試寫作不同“地域”題材,為了適應這些“地域”文化迥然的題材,隆學義先生進行了戲曲文學形式的創新和試驗,有的戲,獲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而有的戲卻不一定獲得了理想的呈現。
一、本土戲演本“地域”題材的得與失
從操作層面來看,川劇對表達本土風情民生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川劇是四川地方音樂、舞蹈、四川語言、百姓形態動作的凝練結合體,當要表達的戲劇內容和藝術形式同源同脈時,藝術家的表達便會順風順水。
川劇《鳴鳳》改編自四川籍作家巴金小說《家》。這出戲主要講述鳴鳳追求自由愛情而不得,被封建主義毀滅的故事。鳴鳳在巴金的《家》中只是一個“戲份”極少的小人物,她的生命如同螢火蟲的光亮倏忽閃爍,最終消弭在陰沉的黑暗中。隆學義的川劇《鳴鳳》拮取了螢火蟲的意象,奠定了這出戲的唯美基調,并將此意象由歌、舞、說白等戲曲形式加以表現。創作立意點的奇特,使這出戲并不將“鋪敘故事”作為敘事重點,而將筆力用于人物情感變化與跌宕的關節點上,該劇分為五場:“情綻”“愛鳴”“驚變”“敲窗”“投湖”。每一場戲的設計,都是為了生動淋漓地呈現一位少女——心靈的成長與掙扎。這出戲中,每個人物各具風格,卻在舞臺呈現中都很討喜:老太爺、陳姨太、馮樂山、李駝背、王媽……這些民國四川的老式人物,經過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很自然地貼合進川劇之中。被理論界津津樂道的,是隆學義以李駝背之口吐露的蒼涼悲情又戲謔的說白:“戀愛是一種病,用結婚來醫;結婚是一種病,用離婚來醫;離婚是一種病,用死亡來醫。”在以現代抒情詩式的唱詞描繪純潔少女形象的同時,隆學義在人物的唱詞中灌注了大量四川民間俗語,并用積極修辭的方法,將說白和唱詞澆筑得朗朗上口,富有古典韻律和現代詩學的交融美感。例如:“蟲蟲飛,蟲蟲飛,/蟲蟲蟲蟲飛。/哪里來?/何處歸?/一閃一亮一熄,/你是誰?我是誰?他是誰?/蟲蟲蟲蟲飛。”“一個捏金童,/一個捏玉女。/玉女身上有金童,/金童身上有玉女。”
從《鳴鳳》開始,隆學義就開始嘗試他的“散文化”戲劇風格。采用“散文化”的戲曲文學結構,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散文化”從總體上追求生活的本真性,不重視對“沖突”和“矛盾”的營造,而常以生活場景的展示為脈絡,展示人物的性情。這種戲曲文學的構造方式,繼承了傳統戲曲文學線性、寫意的美學特色,重抒情,而淡化戲曲的敘事功能。例如,在戲曲《東坡先生》中,隆學義直接以“雪”“風”“月”“濤”“情”“云”“迷”作為每一場的名稱,這種注重“詩性”而輕于“結構”和“沖突”的戲曲文學結構方式,不太適合當下觀眾的接受習慣。這一點,隆學義先生也是明白的,于是他努力以四川本土文化入戲,講四川的“言子兒”,展示四川的“民俗”,談論四川的“熱點”,以具有親和力的地方形式內容,激發觀眾的熱情。在這時,這些來自本土的“地域”的題材就能為他提供更豐富多樣的文化內容,使他的川劇有看點,有特色。而在演員塑造人物時,也因為他們更加熟悉本土文化而倍顯生動。川劇《鳴鳳》就是這樣一種情形,而到川劇《布衣張瀾》時,問題便不那么好辦了。
川劇《布衣張瀾》分為引子“布衣憂患”、第一場“布衣犟項”、第二場“布衣清泉”、第三場“布衣苦舟”、第四場“布衣情深”五個部分。隆學義先生摘取了張瀾幾個人生片斷,以民生為重心,以布衣為象征,貫穿始終,力圖展現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表里如一、方正做人的高潔風范以及和百姓水乳交融的布衣精神。“布衣”是貫穿各場的主題意象,這使得該劇具有高度的象征主義特色。隆學義先生也遇到了“地域”“大”題材的諸多限制:由于是寫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劇作家必須更加尊重政治、歷史的真實,在追求“失實求是”的戲劇原則時,充滿創造力的“臆想”和“編造”便需要更多地讓位于“史實”的表達需要。為了規避“歷史問題”,躲避“敏感話題”,隆學義先生設計了張瀾的幾個生活小故事,但如此看來,此劇充其量只能算作情景劇——缺乏大的戲劇構架。隆學義先生和此劇作曲家任禮康一起想了很多辦法,以本土的文化特色,來調和結構上的不足。首先,以“布衣”的文學意象來牽引和貫穿全劇脈絡,從而解決戲劇結構的“松散”。任禮康以“布衣”的文學意象作為基點,設計音樂框架,用主題曲變奏的方式,為全劇尋找舞臺藝術支撐點,達到聚氣的目的。這些用于變奏、發揮和呈現的音樂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四川本土的藝術存量。比如,本劇的末尾,有一段張瀾夫人劉慧征的抒情唱段。曲作者使用了【香羅帶】曲牌,增其抒情性。在張瀾與劉慧征的對唱中,曲作者加入了清音行腔方法“哈哈腔”,增加音樂張力,表達強烈情緒。又如,主題曲在該劇中并不是一支反復出現的單一曲子,而是一個音樂結構體系,它在全劇不同段落反復呈現時,根據戲劇情景穿插和融入了本土化的音樂元素:川北號子、西充號子、川江號子、石工號子、嘉陵江號子,這使得整個音樂作品馥郁著濃重的鄉土氣息,這是對張瀾奔波一生,卻始終不忘淳樸本質的最好象征和表達,音樂裹挾著鮮活、清新而鄉土化的文學意象。《布衣張瀾》就是李紅艷老師在《戲劇創作地域題材應降溫》中談到的典型的“地域”題材。隆學義老師在運用這個題材的時候,顯然是有著難處的——舞臺劇講“名人”多有忌諱,“求是”和“事實”殊難兼顧,于是隆學義先生終而放棄了以嚴謹的敘事結構“重現”歷史名人故事的想法,繼續踐行他戲曲文學的“散文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好在這是一個本土題材的作品,豐饒的地方語言和音樂文化才能順暢地溶入川劇藝術整體,幫上“聚氣”的大忙。
二、本土戲演非本“地域”題材的是與非
聞名遐邇的川劇《金子》原本是一個“外來文化”艱難適應本土劇種的“反面教材”。《金子》的成功無疑是被“逼”出來的。川劇《金子》始改編創作于1997年,初演時保存了曹禺原話劇劇名《原野》。這個從東北文化移植而來的故事,一開始便患上了川劇的不適應癥。主要有以下幾點不適應:一是話劇《原野》風格雄強,曹禺描繪和渲染的,是一種與大自然與動物天性相呼應的“野性”和“生命力”。這種“東北”風格與擅長表現神仙美眷,討論人倫關系的“西南”川劇有出入。二是曹禺筆下的花金子,是一個摻雜著野性和性欲的女人,川劇的旦角在她的面前顯得過于“柔軟”,因此川劇《原野》的第一次呈現對曹禺原著的表達就不準確。總結起來說,曹禺的《原野》與川劇之間的第一個距離是文化上的——東北文化的蒼茫雄強與西南文化的質巧柔軟;第二個距離則是戲劇風格上的,曹禺話劇試圖描繪的是野性和生命力,而川劇則長于描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譬如“婆媳妯娌”之間的倫常關系。這兩個“距離”實際上都可以統一在地域文化的“差距”上,因為戲劇可以看作地域文化的集中表達。既然川劇無法復制話劇《原野》的主題和人物,那么索性暫且拋開話劇,按照川劇和巴渝地方文化的規律,創造一個川劇金子。1998年,隆學義先生和導演胡明克一起,進入川劇《原野》的第二稿修改打磨。他們決定以主要人物的調整,來牽動整出戲的改進計劃。調整主要人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啟用能唱擅演的沈鐵梅擔綱飾演第一主角,這就意味著沈鐵梅所扮演的金子即將取代仇虎,成為整出戲的核心。第二件事由第一件事情引起:創造一個重慶“俏媳婦”金子形象。這出川劇的名字由《原野》變為了《金子》。比起東北少婦,隆學義先生更加熟悉的是重慶媳婦兒,因此他筆下的金子具有重慶女人的特點“嬌”“俏”“真”“直”“善”,在確立了人物的地方文化性格之后,隆學義著手改編情節橋段。而事實上,他發現傳統川劇已經為她準備了大量的身法和程式,去幫助他呈現一個“嬌”“俏”的重慶女人,這也正應了“藝術源于生活”一語。而隱藏在傳統川劇旦角“俏麗”之下的,是一個個悲哀的靈魂。《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琵琶記》中的趙五娘……哪一個不是深居閨閣,備受束縛的女性形象,而川劇賦予了她們內斂、隱忍、幽怨的品格,即或是剛烈,也是在隱忍、凄麗的外套下表現,比如說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按照川劇表演的規律,一個美的金子,應該首先是丈夫的妻子、婆婆的兒媳婦、族弟的嫂嫂……她在表現她的獨特個性之前,首先應該表現得溫婉、隱忍、善良、規矩。她不能與自然天性對話,而只能與家庭關系對話;她不能講欲望,而只能講純潔的感情——這是一個被傳統戲曲樣式所設計的,被倫理“極端束縛”的金子形象。此外,金子在舞臺上又必須是美的,不能是野蠻的,應該是程式的、節制的,而不應該是輕狂的。善良風情的金子被卷入復仇的風潮之后,會有一個必然結果,那就是選擇善良到底。女性本是世間真、善、美的代表,金子在作為第一主角之后,她的戲劇動機只會有一個:阻止虎子的復仇行為——她想跟虎子遠走,去到黃金鋪路的地方,了卻仇虎心頭的奪妻之恨;她想留住大星、焦母還有小黑子的性命,因為“冤冤相報何時了”?可是仇虎一心陷入復仇深淵而無法自拔。到這里,川劇《金子》的主題已經離話劇《原野》有距離了:《原野》講述的是農民復仇的故事,戲劇主要沖突在仇虎與焦閻王寡妻焦母之間直接展開;而《金子》的矛盾中心在于“金子想要阻止仇虎復仇而不能”。阻止復仇,即倡導以寬容去化解仇恨。寬容——這便是《金子》創新的戲劇主題。
如今川劇《金子》聲名遠播,其原因并不是因為隆學義先生重復了曹禺,而是因為他創造了一個頗具重慶地域文化色彩的“金子”,并因為“金子”人物形象的成功,帶動了整個劇作主題的升華。雖然《金子》算得上是一個外來題材在本地成功的典范,卻告訴我們一個鐵的事實:利用豐饒的地方文化資源,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仍舊是地方戲曲劇種獲得良好演出效果的可行辦法。我們可以將本土以外的人物做出本土文化特色,就更能把本“地域”土生的人物形象呈現好,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本“地域”還是他“地域”,而在于對人物的挖掘力度。
川劇《白露為霜》是隆學義先生改編曹禺話劇《日出》而創作。故事講道:沉浮在濁世中的陳白露,目睹少女小東西的悲慘遭遇,而救助不得;面對方達生苦苦勸告,卻不能自拔于浮華虛偽的洋場。最終她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生命,就像白露為霜一樣,融化在日出之后,回到泥土之中。該劇以“蘆葦花飛白,白露結清霜。清霜如女郎,女郎綠水旁。日出清霜化,清心泥土藏。”這首小詩貫穿始終,極富象征意味,確定了該劇的“詩話”特征。《白露為霜》對曹禺經典的重塑,具有現實意義。陳白露身上被打上了當下都市女性的性格痕跡和命運困惑:面對物欲橫流的社會,人人皆渴慕幸福,而支撐幸福的到底應該是“物質”,還是“精神”和“自由的理想”?曹禺《日出》的故事發生在上海十里洋場。隆學義先生為了讓這個戲更具有川劇性和地方性,在劇中加入了重慶大碼頭的民間環境、用四川清音《小放風箏》來表現少女時代的陳白露,甚至用四川民間曲藝音樂“蓮花落”來表現老妓女“夜來香”和茶房“隔夜茶”。然而,無論如何改編和潤色,總也不能改變曹禺原劇的“洋場”特色,川劇擅長表現市井和小人物,但對表現聲色犬馬的洋場,卻不十分在行。本土的文化內容雖然豐富,即使適時加入,有時也稍嫌生硬。
隆學義先生的幾個川劇劇目讓我們看到:無論運用什么題材,創作的目的都是深挖主題,塑造人物。本“地域”的題材和非本“地域”的題材都有可能做出好戲,也有可能差強人意。因此,面對戲曲文學創作,我們不能將目光過多糾結在“地域”問題上,而應當把注意力放在特定題材對地方戲曲劇種的適應性問題上。例如《原野》的金子雖然來自東北,但這個故事發生在農村,展開在婆媳關系中,這個“倫理關系”的引子是可供川劇發揮的;又例如巴金小說《家》中的鳴鳳,川劇的花旦、閨門旦和奴旦可為她的戲曲舞臺呈現提供現成的程式和身法。說到底,能不能做出優秀的戲曲,題材只是多種舞臺創作因素中的一種,而題材這種因素,又不僅僅只具有“地域”性這一個屬性。
在即將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再談一談我對傅謹先生所提出“地域性題材降溫”問題的理解:首先,這個觀點是傅先生對當下整個戲劇生態作出的評論,戲劇的種類繁多,如話劇在藝術形式上受“地域性”文化的影響就比戲曲小得多。話劇的表現形式在世界范圍更具有共通性,因此話劇的確應該站在更寬泛的文化視野中進行選材。其次,傅先生是站在“地方政府推動戲劇文化”這一操作層面上來講的,其語意重點其實是“提醒地方政府,并杜絕他們的功利主義”。作為戲曲從業者,我們要理解這一觀點,卻不要“非此即彼”地誤讀。中國戲曲應當開拓眼界,根據自己劇種的特點,大膽嘗試新的適合自己的題材,以激發新表現形式的探索。這一切都建立在解除“浮夸”與“跟風”的堅實藝術實踐之上。
*本文為2016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川劇藝術創新發展視閾下的隆學義川劇創作研究》(項目批準號:2016YBYS147)成果之一。
周津菁:重慶市文化藝術研究院藝術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