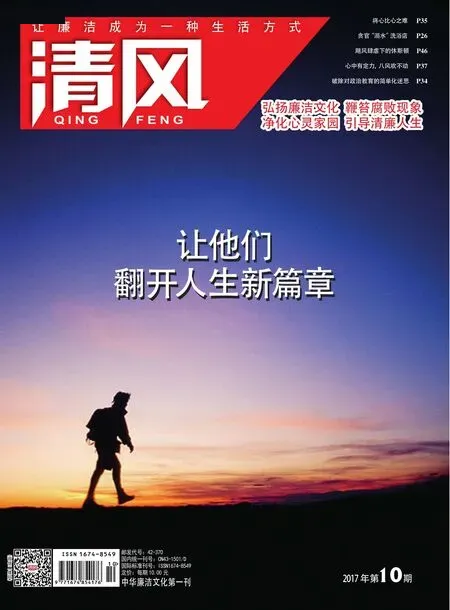讓互信之光照亮新生之路
文_林永芳(福建龍巖)
讓互信之光照亮新生之路
文_林永芳(福建龍巖)

曾經有這么一個人,他在朝中以武勇和正直出名,只認法紀,不避權貴。特別是擔任御史中丞后,連梁王司馬肜違法都敢糾舉,把梁王給得罪了。到了公元296年,西北氐族反叛,朝廷讓梁王做統帥,卻讓他做先鋒。他自知這回落入梁王掌中難免遭到暗算,但以自己的身份,國家有令,沒有理由推辭,于是抱著必死的決心西征。就連敵人都覺得,這小子若當主帥則無法抵擋,若受制于人則必可擒獲。
結局果然如此——翌年初,敵軍屯兵七萬,梁王逼他僅以五千兵力發動攻擊,不但不給后援,而且士兵連飯都沒吃就被推上戰場。他奮勇殺敵數以萬計,堅守陣地拒不逃跑,力戰至死以身殉國。
如此英勇忠直、德才兼備、為維護法紀不惜冒犯權貴的人,肯定一直遵紀守法、從小優秀到大,做慣了大家的榜樣吧?非也。此人名叫周處。你一定在中學課本里讀過他當年的劣跡——年少時縱情肆欲,兇暴強悍,只信奉拳頭,視法紀如無物。鄉親們將他和河中蛟龍、山上猛虎并稱為“三害”,且視其為“三害”之首。為了借刀殺人、為民除害,人們故意勸他去殺猛虎、斬蛟龍。殺虎斬蛟途中他一時失聯,鄉親們頓時熱烈慶祝,以為他已經死了。他這才驀然意識到自己有多么不受歡迎,于是“有自改意”,想重新做人,可又擔心已經回頭無路,困惑中找到陸云。且看陸云是怎樣幫助、開導他的:“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憂令名不彰邪?”在陸云的安慰、鼓勵和點撥下,周處改過自新,終于名揚千古。
周處的故事證明:人是可以轉變的;只要痛下決心,浪子也能成才。可,假如當他有心改悔、登門求助時,陸云躲避他、鄙棄他,或者冷嘲熱諷,并且全社會都如此排斥他,那么,除了破罐子破摔,他還能如何?
事實上,堅信“浪子回頭金不換”,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共識,而非只有中國古人有此慧眼。倫勃朗大師晚期的代表作、圣彼得堡冬宮的鎮館之寶《浪子回家》,便是以耶穌所講“浪子回頭”的故事為藍本:小兒子揮霍盡了向父親索要的資財,受雇為人放豬,食不果腹,想要點飼料來充饑都不可得,遂幡然悔悟,回家跪在老人面前。雙目已失明的父親,屈身俯下,伸出顫抖的雙手去擁抱他,并告訴大兒子:這個兒子失而復得,實屬喜慶!耶穌以此告訴他的信徒:迷途知返最可貴,上帝不會因某人曾迷失而拋棄他。
是的,世上的路有千百條,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找到最正確的那一條。犯下罪錯的人,固然必須為自己的錯誤選擇買單;可倘若他們在接受法律的嚴懲、命運的敲打之后已經有了重啟人生的愿望,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排斥他們呢?
長沙有個商會會長謝著輝及其穗誠集團,便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刑釋人員鋪起重返社會之路,該公司因而成為全省刑釋人員過渡性安置基地;第五屆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獲得者、被青少年稱為“孟媽媽”的孟繁英,則創辦了湖南省首個社區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長沙孟媽媽青少年保護家園,十幾年來,幫助了數千名特殊群體青少年。他們的行動令人尊重,也值得各界反思:我們,又該如何對待“迷途的羔羊”?
人為什么會犯罪?概言之,無非兩類:一是價值觀“病”了,需要矯正;二是性格沖動暴躁,一時控制不住自己,事后懊悔莫及。可犯下罪錯,不等于徹底無可救藥。當他們想重返正軌時,拉一把可能就成了“周處”,至少是自食其力、無害于社會的人;可如果用冷漠和白眼“推”一把,他們很可能就因正路不通而更加死心塌地倒向“邪路”,甚至絕望中往往更加不計后果。前者,是互利共贏的模式;后者,則無異于在整個社會埋下一顆顆不定時炸彈,你以為受害者只有他們,實則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因此處于險境,因而是不折不扣的“互害模式”。
從“互害、互疑”到“互利共贏”,二者之間,一個必不可少的路基,就是“互信”——你相信他誠心誠意重返社會,他相信你能夠包容接納全新的他。
基于文明、基于寬容,甚至,哪怕只是為了自己,也應當主動敞開胸懷,釋放善意,幫助、接納他們獲得新生,讓這個世界少一些敵對,多一些溫暖。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