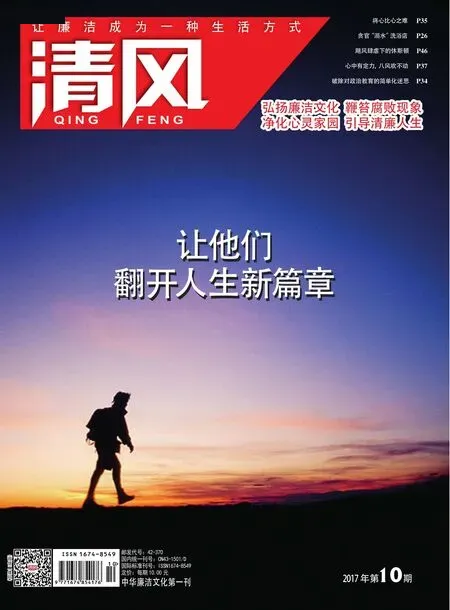相輕何止是文人
文_張友全(湖南長沙)
相輕何止是文人
文_張友全(湖南長沙)

文人相輕的說法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其最早出現在曹丕的《典論·論文》中,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至于為什么文人相輕是自古而然的事,曹丕分析說是因為“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換句話說,就是文章的體裁并非只有一種,而人不可能每種都會,所以時常會以己之長輕視別人所短。
正常來講,文人相輕這話不該由曹丕來說,因為他雖然主要以帝王形象出現,但從文學角度講,他是“三曹”之一,也有一定成就,沒必要批評一種現象時把自己也捎上。如同魯迅所言,“相輕”之說只是站在旁邊看文人輕來輕去的第三者,而真正卷入窩里斗的只有“被輕”和“輕人”兩種。比如今天來講,如果兩個文人爭執起來,旁邊的人就會說,你看,文人相輕。這里面往往帶有某種輕蔑和嘲笑,因為在旁人看來,文人只會紙上談兵,爭來爭去非但沒有實際意義,還斯文掃地。也就是說,文人一般不會自己承認彼此相輕,只會說那是思想爭鳴或者意見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嘛。
曹丕之所以敢于那樣說,在于他有自知之明,他認為自己有能力衡量別人,可以避免文人相輕的拖累。從整個文章看,他對當時一些文人的評價確實是“持平之論”,并沒有厚此薄彼。不過,曹丕撰寫《論文》主要是討論文章體裁和氣象的,因此在分析文人相輕時只是點到為止。于今而言,文人相輕,恐怕不是寫詩的看不起寫小說的,寫小說的看不起寫散文的這么簡單,而是有的文人內心的一種復雜心理。
一方面,有的文人最在乎自己的思想,對自己的東西時常有一種“獨斷式的確定感”,這就容易輕視別人的所思所想。比如魯迅就具有這樣“熱烈的好惡”,對同時代的好多文人采取輕視態度,胡適、梁實秋等等皆在他的批評之列;另一方面,文人之間雖然才華有一定的高下,但時常各有千秋,從歷史長河來看,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要讓一個人服膺另一個人并不容易,互相看不起也就在所難免,畢竟沒幾個人愿意在學識上甘拜下風,都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正常的學術批評與爭論,盡管難免會有偏頗之處,但在筆者看來,與文人相輕無干,反倒是互相尊重,思想交鋒。如果是因嫉妒或者高傲而有意貶低別人,那就是典型的文人相輕了。
對此,林語堂先生有更尖銳的分析。他說:“文人好相輕,與女人互相評頭品足相同。世上沒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個美人走出來,女性總是評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寬,否則牙齒不齊,再不然便是或太長或太短,或太活潑,或太沉默。文人相輕也是此種女子入宮見妒的心理。軍閥不來罵文人,早有文人自相罵。一個文人出一本書,便有另一文人處心積慮來指摘。你想他為什么出來指摘,就是要獻媚……文人不敢罵武人,所以自相罵以出氣,這與向來妓女罵妓女,因為不敢罵嫖客一樣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林語堂先生所言,可謂說透了一些文人的心理,同時給我們帶來了啟發。從其分析的立足點來看,其實我們無需對文人相輕做過度闡釋,因為互相輕視的事大約出于人的一種心理,而這種心理并非文人獨有。只不過有的文人喜歡來點嘴上風暴,還把輕視別人的話變成了白紙黑字,不知不覺給人一種得理不饒人的感覺。再加上有“文人相輕”這么一個現成的詞,讓旁人對文人產生了刻板成見。
如果從嫉妒、高傲、取媚于世等心理因素來看,彼此看不起的又何止是文人?同行相輕、同事相輕、朋友相輕,比比皆是。這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有的人愿意給遙遠陌生人的成功歡呼,卻不愿為自己身邊人的成長而鼓掌了。因為身邊的人與自己有競爭和比較,這就容易產生嫉妒之心,嫉妒而又趕不上,就容易生出看不起對方的心理,覺得對方沒什么了不起;而遙遠的陌生人,既不會給自己生存的壓力,也沒有互相比較的必要,不妨奉獻一點廉價的掌聲,證明自己還有一顆見賢思齊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