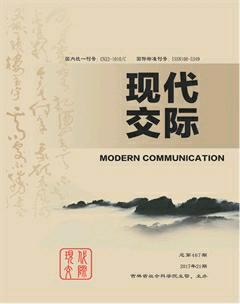中國臺灣作家眼中的新文學
吳京宣
摘要:作為在文學史中長期被忽略的作品,中國臺灣作家葉榮鐘的《中國新文學概觀》是身處新文學運動之外的作家以“旁觀者”的視角對中國大陸新文學發展的觀照。這部隱藏于暗角中的作品卻有著在當時看來極為先進的文學觀念,包括“純文學”的觀念、對于人性的探索以及“國際化時代”概念的提出等等。時至今日,這些觀點仍舊應該在中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這部文學史所具有的價值也應進一步得到重視。
關鍵詞:葉榮鐘 《中國新文學概觀》 純文學 新文學
中圖分類號:G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21-0070-02
一、被忽略的文學史
葉榮鐘的《中國新文學概觀》是中國臺灣地區較早論及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部作品。然而這部作品卻常常被海峽兩岸學界所忽略,不論是對葉榮鐘作品的研究還是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這部文學史都很少被提及,導致這部作品被忽略的原因也是多樣的。
其一,葉榮鐘作為政治人物,學者們較多地把目光投向于他《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灣人物群像》《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等政治歷史作品,以至于較少關注他的文學類作品。
其二,葉榮鐘1930年前留學日本,《中國新文學概觀》完成于1929年,且于1930年出版歸為新民會文存第三輯,撰寫和出版都在日本也是使得這部作品沒有得到關注的原因。
其三,《中國新文學概觀》這部作品共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序說”“文學革命的演進”“新文學作品”“文壇的派別”以及“結論”。“新文學作品”又細分為“新詩”“小說”“戲曲”“小品散文”。其中“文學革命的演進”這一章是完全將胡適的《五十年來之文學》中的“末一段”抄錄下來作為獨立的一章。加之葉榮鐘所處偏遠,搜集資料相對困難,造成他創作的“滯后性”,這部作品所具有的文學價值也理所當然地被人忽略。
二、“純文學”理念的初現
葉榮鐘對新文學運動“質”與“量”的不平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肯定了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年間,產生了大量的作品,體裁得到極大豐富,文藝雜志的出版發行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這其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葉榮鐘認為“在那汗牛充棟的作品中,除起兩三部的杰作而外,盡是粗制濫造的文學水平線下的作品。結局新文學運動也是和新政治運動一樣,名實不能相符”。他認為前期梁啟超推行的文學革命失敗的原因在于“任公先生是政論家而純粹的文學者”,他對文學抱有的是利用的態度,對文學自身并沒有改革的意識。當時的先進青年一方面不能擺脫“舊文學”的束縛,另一方面對洶涌而至的各種思想所困擾并不能抱有堅定的信念從事文學創作。在第三部分“新文學作品”中,他又對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現狀進行了分析。
新詩方面,他認為新詩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但是質量卻不甚高明。他認為初期的作品帶有“舊詩詞的余嗅”,之后的作品又犯著“‘太明白的毛病”。他反對胡適所提的“作詩如作文”的要求,認為詩歌既要擺脫舊詩詞的束縛,又要摒棄“太明白”的弊病。雖然新詩的創作并不盡如人意,但他依舊抱有美好的希冀。小說方面,他認為短篇小說以魯迅代表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長篇小說卻并不盡如人意。他并不贊成陳西瀅力薦楊振聲的《玉君》為中國長篇小說的代表,認為中國仍舊缺乏優秀的長篇小說。他認為因現代社會生活的繁忙而缺少長篇小說的說辭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的機械生活還未發展到一定程度,讀者對長篇小說也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作家因為金錢而受到的生活壓力也應該是次要原因。面對長篇小說的缺失,他犀利地指出造成這種缺失的原因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思想混亂到于極點,作家失掉了精神生活的重心,彷徨于思想的歧路,沒有堅確的信仰,沒有一貫的精神”。作家們所經歷的“時代的苦悶”以及長篇小說產量不高通常是被其他文學史所忽略的。在戲曲(話劇)方面,葉榮鐘對其成果評價最低,他將原由歸結為缺乏實踐經驗,不應完全摒棄傳統戲曲中的有益成分。小品散文方面主要介紹了周氏兄弟且評價較高。
三、文學史中的人文情懷
除了對“純文學”的推崇,《中國新文學史概觀》中還充滿著濃重的人文情懷,這種人文情懷主要體現在對魯迅《阿Q正傳》的評價、對老舍《趙子曰》的評價以及對“文壇派別”的介紹中。
首先,葉榮鐘高度評價了魯迅的《阿Q正傳》,他對這部作品的評價并不在于它“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也不在于它“啟蒙”的作用,而是著重于對阿Q這一人物形象的解讀。他認為阿Q身上體現著“人間苦”與“時代性”,他將阿Q作為“人”來進行詳細的心理分析,他對阿Q的一生從“人”的角度進行了總結:“阿Q受著貧富不均等的壓迫,體驗過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著階級的差別,嘗到最高度的蔑辱,受著舊禮教的束縛,終于要拋擲了人生應想的性的悅樂,受著時代思潮的翻弄,終于要無理無由地斷送了性命。”他對阿Q的人生進行觀照,將其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力——性的合理性的喪失為切入點,對阿Q寄予深厚的同情。與早期《阿Q正傳》的評論性文章相比,他是真正地把握住了《阿Q正傳》的精髓。他將目光投射于“人”的生命狀態,同情“人”的人生苦痛,關注“人”的生存境遇。從葉榮鐘對于《阿Q正傳》所具有的極高的藝術價值的肯定中可以看出,他對文學作品的評判是具有人文情懷的觀照的。
葉榮鐘對于作品中人文情懷的觀照還體現在他對老舍《趙子曰》作品的評論中。葉榮鐘對趙子曰的人物性格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對趙子曰身上具有的“闊氣和俠氣”所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進行了贊揚,即“他的生活雖然是頹廢不堪,卻始終不叫讀者生出輕蔑或憎惡的感情,反覺得他是一個和藹可親足以引人同情的人”。這與他對阿Q的評價有著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帶有明顯缺陷的人物形象,雖然一個是農民,一個是知識分子,但他們身上有著現代人共有的缺點,正是這些缺點導致了他們的悲慘的生活遭遇卻使得該人物形象能激發讀者更多的共鳴,更具代表性也更具有生命張力。
除此之外,葉榮鐘對于“文壇派別”的介紹也極具特點。葉所介紹的文學團體有“創造社派”“語絲派”“文學研究會派”“新月派”以及“圈外作家”,其中“語絲派”著墨最多。這與中國大陸文學史文學流派的介紹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大陸的文學史資料通常把文學社團介紹的重點放在文學研究會以及創造社中,對“語絲派”的介紹篇幅絕不會超過前面提到的兩個社團。而葉榮鐘著重介紹“語絲派”的原因在文中也有所提及,因為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同時由于個人對魯迅的欣賞,使得他在對“語絲派”的介紹中摻雜著對魯迅生平的簡要概括以及對魯迅崇高廉潔的人格和那不妥協、嫉惡如仇的斗志的仰慕。endprint
從以上的例證不難看出,葉榮鐘的文學史是充滿著人文情懷的,他不著重分析文學作品的技巧是否精湛,也不關注作品所具有的階級立場和政治傾向,而是看重于作品本身所體現的“人”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程,感受“人”的生命陣痛,對普羅大眾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經驗進行深刻的反思與追尋。
葉榮鐘的《中國新文學概觀》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首先,他處于中國大陸新文化運動的外圍,不能及時接收到最前沿的資料,也對新文化運動的進程存在著模糊的認識,這就導致出現了他作品中完全引用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原文作為獨立的章節;其次,葉榮鐘在編寫這本文學史時,并沒有抱持著完全公平客觀的態度,依據自己的喜好善惡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這就造成了文學史的不完整,不客觀。比如,他因為自己不喜歡讀張資平的小說就提出中國新文學以來沒有成功的長篇小說出現,他由于個人對魯迅的推崇在對語絲派的說明中摻入了魯迅生平的簡介,可以說這是一部個人色彩濃郁的文學史作品。除此之外,這部文學史充滿了感召力,也充滿了個人感情,這就會導致文風不嚴謹的缺陷,比如他評價語絲派的某些作品是“虛無的個人主義”并沒有什么理論依據,再比如他將魯迅的文學地位拿宇宙中發現的行星相比擬,雖然通俗易懂,但運用在一部文學史的作品中還是有失嚴謹的。
雖然有以上諸多弊病,但葉榮鐘的《中國新文學概觀》還是為學者們提供了許多新思路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它作為臺灣較早介紹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發展現狀的作品,給當時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民眾提供了一種較為開化的文學風氣,也為當時希冀革新的知識青年提供了方式及手段的借鑒。其次,這部作品也表明葉榮鐘本身所具有的“跨越性”,他能跨越海峽兩岸的距離,汲取大陸文學運動的有益成分推動臺灣文學運動的發展,單就這一點來說也極其難能可貴。同時,這部作品以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的視角對中國新文化運動進行較為客觀的評價,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并對當時的文學環境進行分析與反思,給大陸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史以新的啟發。這部日據時期臺灣作家所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史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它的人文情懷,因為它的先進理念,因為它的臺灣味道。就像戴國輝在《葉榮鐘日記》的序中所言:“‘媚日與‘哈日軟骨癥候群彌漫于全臺灣的當今,有良知的欲知鄉土歷史的真正愛國者特別需要睿智老報人、藹然風范者——葉榮鐘先生的全集,當為燭照及激勵來尋正出路的。”
參考文獻:
[1]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M].東京:東京印刷制本株式會社,1930.
[2]葉榮鐘.葉榮鐘日記(上)[M].臺中:晨星出版社,2002.
[3]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8]王富仁.“新國學”論綱[J].社會科學戰線,2005(3):85-110.
[9]徐紀陽,朱雙一.魯迅臺灣接受史論綱[J].當代作家評論,2015(6):54-61.
[10]付祥喜.日據時期臺灣人編寫的兩種“中國新文學史”——蔡孝乾和葉榮鐘的《中國新文學概觀》[J].現代中文學刊,2015(3):96-104.
[11]張重崗.葉榮鐘的戰后思考[J].文學評論,2016(4):102-110.
責任編輯:于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