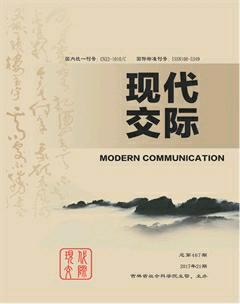雅俗共賞
鄒華
摘要:雍正粉彩在清代粉彩中具有獨特的美學特征,在中西文化及技法的沖擊下,呈現出雅俗共賞的特點。其雅在于構圖與意境上對傳統美學的模仿與超越,其俗在于題材對俗世感情及心理的迎合。本文在界定雅與俗的基礎上,對雍正粉彩雅與俗的體現及此種特征出現的原因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雍正 粉彩 雅 俗
中圖分類號:H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21-0082-02
粉彩,即具有粉潤之感的色彩,其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礎上,采用部分琺瑯彩制作工藝而創造的一種釉上彩品種。粉彩瓷的出現與康熙時期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皇帝本人對西方工藝美術濃厚的興趣等有很大關系。粉彩瓷在其審美上有著與琺瑯彩、五彩、淺絳彩不同的特點。粉彩瓷的特點在許之衡的《飲流齋說瓷》中有精辟的描述:“軟彩又名粉彩,謂彩色稍淡,有粉勻之也。硬彩華貴而深凝,粉彩艷麗而清逸”。粉彩瓷也正因為此特點,歷來深受國內外陶瓷藝術鑒賞家和收藏者的推崇與關注。清人陳瀏亦在《陶雅》中盛贊粉彩“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鮮嬌奪目,工致殊常”。粉彩瓷始于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達到頂峰,尤其是雍正粉彩制作工藝考究,呈色豐厚多變,彩料濃淡天然,呈現出雅俗共賞的特性。
一、雅與俗的界定與轉化
作為審美范疇,“雅”與“俗”其語義本身是相對的。在中國美學發展史上,雅俗之爭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禮樂制度的建立。西周時期所謂的“雅樂”是指正統的音樂,即無論從審美意蘊看,還是從審美表達看,都符合禮樂規范,能體現儒家所極力稱頌、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精神一脈傳承的政治倫理教化審美觀念的宮廷音樂。與“雅樂”相對的是“俗樂”,指古代各種民間音樂,又稱“世俗之樂”,或表現激昂憤怒的情感,或表現受壓迫的呻吟,或表現對故國和親人的懷念,或表現男女愛情。“俗樂”的出現雖然給當時的“雅”審美觀念巨大的沖擊,但是“俗樂”中所表現出的大眾的真實情感,成為推動審美追求和藝術發展的巨大動力,促使中國的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呈現出“雅俗并舉”的發展狀況。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雅”的概念逐步細化,“古雅”“高雅”“文雅”“典雅”“淡雅”“和雅”“清雅”等概念逐漸被提出。[1]雖具體側重點略有不同,但歷代文學及藝術領域對“雅的追求”從未停止。
二、雍正粉彩瓷中的雅與俗
雅從其概念誕生以來,便是文人墨客始終追求不懈的理念。歷代文人對雅的內涵都進行了豐富,初唐詩人陳子昂在改革詩歌創作時便提出應鄙棄“淫麗”“浮靡”,追求“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雍正粉彩從畫面構圖、造型、配色三者來看,正是摒棄了“淫麗”追求“頓挫”及“光英朗練”,符合中國傳統審美情趣中的“雅”。與乾隆粉彩相比,雍正粉彩在裝飾構圖中,十分注重留白,露出純凈潔白、玉質玲瓏的瓷胎,顯得輕盈飄逸。相較之下,乾隆粉彩則從足底到口沿、從色底到畫面進行了多種裝飾手段,略顯厚重繁縟。且雍正時期陶瓷彩繪藝術造詣甚高,粉彩瓷繪與中國國畫中的工筆重彩畫風日趨一致,“畫中有詩”的中國畫體之構圖融入粉彩裝飾中。雍正粉彩常融“詩、書、畫、印”為一體,精美的粉彩都有與畫面內容相關的詩句及閑章相呼應。如清雍正粉彩梅花紋盤(圖1)便題有“數枝橫翠竹,一夜遶朱欄”[2]。與畫面相呼應。且雍正粉彩可將層巒疊嶂濃縮在一個細小的碗心,將萬紫千紅的花鳥再現于一件細小瓷瓶的外壁。正如惲南田在《題潔庵圖》中說:“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丘一壑、皆潔庵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其意向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將以尻輪神馬,御冷風以游無窮。真所謂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垢秕糠,綽約冰雪。時俗齷齪,又何能知潔庵游心之所在哉!”
雍正粉彩在常見花卉題材,如梅蘭竹菊松的基礎上,增添了蝴蝶、草蟲、飛鳥等題材,并取其諧音、寓意進行不同組合。如石榴代表多子,蝙蝠取其諧音“福”與海水紋組合為“福如東海”,喜鵲站在梅枝上取其“喜上眉梢”之意。中國傳統文學常把雙飛的蝴蝶作為自由戀愛的象征,這表明人們對自由愛情的向往與追求。蝴蝶被人們視為吉祥美好的象征,被用于寓意甜美的愛情和美滿的婚姻,雍正粉彩中蝴蝶的大量出現亦為世俗情感在陶瓷上的體現。同時,雍正粉彩題材中出現了大量世俗場景的再現,如粉彩仕女嬰戲盤(圖2)中將傳統的仕女、童子題材放入實際生活場景中,兩雞相斗,仕女與童子饒有興致地觀察斗雞,人物、公雞與周圍的家具、裝飾物等構成了栩栩如生的俗世生活畫面。粉彩戲曲人物筆筒(圖3)則突破傳統青花人物雅的局限,將俗世男女作為主體,實則為大眾感情即“俗世”感情的藝術化。
正是雍正粉彩瓷在意境及審美中對傳統“雅”的追求,和在題材上對俗世感情及心理的映射,構成了雍正粉彩的“雅俗”共賞之特征。
三、雍正粉彩瓷能夠雅俗共賞之原因
(1)政治經濟背景的完備。
自1644年清軍入關,經過順治的過渡,到康熙時政治經濟基礎已趨穩固,到雍正時,整個社會呈現出全面繁榮的景象。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推動了制瓷工藝及藝術處理方法的不斷改進。據《清檔》記載,雍正六年(1728年)“琺瑯材料”試制成功,不僅燒煉出9種西洋彩,還配出9種西洋彩中沒有的顏色。[3]這些琺瑯材料除宮廷琺瑯專用外,多余材料都提供給景德鎮,這對于增加花色品種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而花色品種的豐富,為雍正粉彩瓷題材多樣化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
(2)西洋技法的影響。
粉彩瓷脫胎于琺瑯瓷,而清宮琺瑯最初受歐洲畫琺瑯的啟發,在康熙皇帝親自主導下,以歐洲畫琺瑯為參考對象,加上中國傳統瓷器彩繪、掐絲琺瑯制作技術為基礎,自行研發試驗而來。粉彩的產生,受琺瑯彩砷的啟示,并借鑒琺瑯彩的制法,在含鉛玻璃質溶劑中引入砷作為乳濁元素,制成一種白色粉末,俗稱“玻璃白”。正是“玻璃白”的出現為陶瓷彩繪畫面中“留白”“渲染”“陰陽”“濃淡”的實現提供了基礎。雍正年間,以年希堯為代表的畫師,沿襲西洋透視學,在定點透視和平面上處理三度空間等方面都深受西洋技法影響。
(3)中國畫的影響。
至清代,文人畫日益占據畫壇主流,山水畫及水墨寫意畫盛行。在文人畫創作思想的影響下,雍正粉彩釉上彩的畫法,如中國畫之粉本一樣,繪人物衣褶、花卉等畫面紋飾上用洗染方法,且有陰陽向背濃
淡厚薄之變化。雍正粉彩在款識、書法、題詩上也都借鑒中國畫之韻致。以董誥、張宗蒼、金廷標、蔣廷錫、鄒一桂、惲南田為代表的名家,其山水、嬰戲圖、花鳥等“勾、皴、點、拓、洗”技巧在雍正粉彩裝飾中運用頗多。[4]在上述的畫家中創造性地恢復了“沒骨花鳥畫法”的惲南田,其作品構圖簡潔,設色清麗,意旨高潔,于絢爛中求平淡自然。此種畫法成為宮廷主流畫風,皇家審美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官窯生產,在陶瓷領域為迎合雍正的審美,刻意模仿惲南田。因此,雍正時期的粉彩裝飾極大地受到文人畫的影響,其構圖、用色、意境都走向高雅。
四、結語
陶瓷與世間任何其他事物相同,并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雍正粉彩在時間順序上承康熙、下接乾隆。從工藝上,脫胎于琺瑯瓷,融中西之所長。但雍正粉彩既沒有被琺瑯淹沒,卻呈現出不同于康熙與乾隆的獨特美學,其要義正在于雍正粉彩的雅俗共賞。
參考文獻:
[1]李天道.中國美學之雅俗精神[M].中華書局,2004.
[2]鄒曉松.傳統陶瓷粉彩裝飾[M].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3]江和先,鄧春英.論雍正帝與粉彩瓷藝術的興盛及風格[J].中國陶瓷,2012(4):63.
[4]張玉霞.惲壽平花鳥畫對雍正粉彩瓷的影響[J].中國陶瓷,2016(5):80.
責任編輯:于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