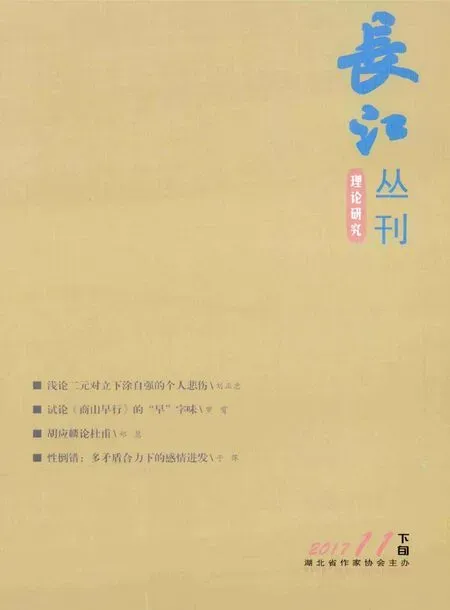胡應麟論杜甫
鄭 慧
胡應麟是明代的文壇大家,但目前對于胡應麟的研究,探討他的詩論思想以及文獻學成就是熱點,很少有對個案的分析。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胡應麟詩論著作《詩藪》對杜甫評價的材料約一百六十條,考據專著《少室山房筆叢》涉及杜甫的考辨有十余條。本文從胡應麟對杜甫的評價、對杜詩的考證方面,分析了胡應麟對杜甫的情感態度,從而豐富明代對杜詩的評論研究。
一、胡應麟對杜詩的評價
胡應麟詩論著作《詩藪》對李白、杜甫的評價多于其他詩人,涉及李白的評論有八十余條,而涉及杜甫的評論約一百六十條,可見胡應麟對杜甫的尊崇、對杜詩的看重。
首先,胡應麟對杜詩地位給予了最高評價,認為杜甫是“大家”,其詩歌是“集大成”。如“備諸體于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于開元者,工部也。”(《內編》卷二)“杜后起集其大成”(《內編》卷五)“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內編》卷四)可見胡應麟充分肯定了杜甫的歷史地位。有時候,胡應麟評價杜甫時,言語中蘊含對杜甫的尊崇與追慕之情,有強烈的情感體驗,如“千古以還,一人而已”(《內編》卷四)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內編》卷四)說明胡應麟不僅站在客觀的角度評價杜詩,更對杜詩從心底傾慕。
其次,胡應麟常常李杜并提,二者共尊,充分肯定了李杜的詩才。如“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并,色相難求;杜唯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畜。”(《內編》卷四)胡應麟用形象的比喻,指出杜甫無事無物不可入詩的深廣,充分肯定了李杜二者的地位,比較了二者詩歌風格的差異。
胡應麟還從詩歌體裁、詩歌風格等方面,對李白、杜甫做了全面的比較,認為二者并尊,并無優劣。如“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杜,何必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毋事更屑屑也。”(《內編》卷六)從體裁上說李杜二者各有所長,李白擅絕句,杜甫擅律詩。又如“李杜二公,誠為勁敵。杜陵沉郁雄深,太白豪逸宕麗。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靡暢。廷禮首推太白,于麟左袒杜陵,俱非論篤。”(《內編》卷三)從風格上比較李杜,認為杜甫沉郁,李白豪放。不管是體裁,還是風格,胡應麟始終強調一點,二者各有擅長,不可以評價優劣。這在筆者關于胡應麟對李白接受的論文中已有闡釋,暫不贅述。
第三,胡應麟對杜甫詩歌體裁、風格、手法等各方面作了具體評價。
一是胡應麟特別推崇杜甫的律詩,他說“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內編》卷二)“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內編》卷四)可見胡應麟對杜甫律詩評價之高,認為杜詩非人力可至,獨步古今。他還用形象生動的語言來描繪杜甫排律的特點,“讀盛唐時排律……少陵變幻閎深,如陟昆侖,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匯汪洋。”(《內編》卷四)說明杜甫排律的變幻莫測、包羅萬象。
二是胡應麟認為杜詩風格多樣,如: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內編》卷四)
“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庭日”;幽野,則“風林纖月落”;餞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佩冷”;吊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內編》卷四)
“杜七言句,狀而宏大者……狀而高拔者……壯而豪宕者……壯而沉婉者……壯而飛動者……壯而嚴整者……凡以上諸句,古今作者無出范圍也。”(《內編》卷五)
他說杜詩眾體皆備、風格畢具,粗細濃淡、宏大幽婉,無所不包,并舉例說明杜詩每一種風格都能做到極致,即使同樣是“狀美”,也能變幻出不同的風格,所以由衷贊嘆“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古今作者無出范圍也”。
三是胡應麟對杜詩的句法、用典等藝術手法作了分析。如說杜甫用字:
“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內編》卷五)
“老杜字法之化者,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云’,坼、浮、知、見四字,皆盛唐所無也。”(《內編》卷五)
盛贊杜甫錘煉字句“古今獨步”,并舉例分析了杜甫用字出神入化、神采奕然。又如說杜甫用典: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內編》卷四)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杜用事入化處。……此老杜千古絕技,未易追也。”(《內編》卷四)
同樣,胡應麟既有整體說杜甫用典豐富而恰到好處、用語自然,不晦澀難懂,又舉例說明胡應麟用典出神入化,并感嘆這是杜甫“千古絕技”,不可學,不易學。
第四,胡應麟對杜甫部分詩作作了分析與評價,并將其作為詩歌典范。
例如胡應麟非常喜歡杜甫的《登高》,多次高度評價杜甫這首詩:
“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后無來學。”(《內編》卷五)
“若‘風急天高’,則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實一意貫串,一氣呵成……真曠代之作也。”(《內編》卷五)
胡應麟首先肯定了這首詩氣象宏大,內涵深沉,力量萬鈞,并從章法、句法、字法等嚴格的格律方面,認為杜甫《登高》是七律之最。句句皆律,字字皆律,又能一氣呵成。所以胡應麟贊嘆這首詩是“曠代絕作”。
又如胡應麟認為杜甫有很多詩歌可以作為后世學習的典范。“短歌惟少陵《七歌》等篇,雋永深厚,且法律森然,極可宗尚。”(《內編》卷三)說杜甫的歌行格律嚴謹,可以作為學習的榜樣。又如:
“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殿退朝》、《九日》、《登高》、《送韓十四》、《香積寺》、《玉臺觀》、《登樓》、《閣夜》、《崔氏莊》、《秋興八篇》,氣象雄蓋宇宙,法律細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內編》卷五)
胡應麟認為這些詩歌全篇可以效法、模仿,原因是氣象宏偉,法律森嚴。這與胡應麟的詩歌理論“體格聲調”“興象風神”是一致的。“體格聲調”就是格律等外在形式,“興象風神”就是氣象神韻等內涵。胡應麟論詩,一方面遵循“體格聲調”,看詩人詩作是否符合規范;另一方面,又將詩歌是否具有“風神”作為標準之一。這也表現在胡應麟論杜詩之中,不管是對杜詩總體的評價,還是對杜詩體裁、風格、技法的評價,都是其詩歌理論的闡釋。
杜詩是否合乎正法,是否作為詩歌典范,是否能成為后世學習的對象,也是從“體格聲調”“興象風神”這兩方面來考慮。把握胡應麟論杜詩的情況,就可以一窺胡應麟的詩學思想。
二、胡應麟對杜詩的考證、辨析
《少室山房筆叢》是胡應麟考據專著,內容豐富。其中,涉及杜甫的材料有十余條,主要是對杜詩出處的考證、辨析,尤其是對楊慎考證失誤的辨析占了絕大部分,均收錄在《藝林學山》之中。試舉幾例:
楊慎對杜甫《客至》中的“社南社北”作了考證,認為“舍”應當為“社”。楊慎說“韋述《開云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子美‘社南社北皆春水’句子正用此事,不知改為‘舍’耳。”胡應麟案曰:
“杜‘舍南舍北皆春水’,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此詩上以‘舍’字引起,下用群鷗而花徑蓬門,意脈直貫,若改為‘社’則并不沾帶矣。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餐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乃與鄰翁對酌,何耶?杜他日絕句云‘云生舍北泥’豈亦‘社北’耶?考杜集他本絕無‘社’字之訛,特用修讀書偶得此,遂白賴少陵耳。”
這里胡應麟用多條證據,指出了楊慎注釋杜詩“舍南舍北”出處的失誤。一是從詩歌所作之地認為不符,二是從格律上認為不合律,三是從前后句意邏輯認為不通,四是舉杜甫其他詩作為旁證,認為杜詩并無此種表達,因此楊慎將“舍”字理解為“社”是沒有依據的牽強附會。胡應麟條分縷析,邏輯嚴密,證據充分,可見其學問上的嚴謹態度。
又如楊慎注釋杜甫《游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中的“綠沉”說“綠沉色為漆飾槍柄耳”。胡應麟從作品出發,認為“綠沉”應指“鐵名”,而不是“漆色”,又舉了《西溪叢語》《唐百家詩》等多部論著進一步證明楊慎之誤,可謂論據充分,考據詳實。
再如楊慎認為“宋人以杜子美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胡應麟對此作了辯駁:
“以杜為‘詩史’,其說出孟棨《本事詩話》,非宋人也。若‘詩史’二字所出,又本鐘峻‘直舉胸臆,非傍詩史’之言,蓋亦未嘗始于宋也。楊生平不喜宋人,但見諸說所載則以為始于宋世,漫不更考,恐宋人有知揶揄地下矣:明人魯莽至此。”
胡應麟論證充分,層層遞進。首先,杜甫“詩史”的提法,始于唐代孟棨《本事詩話》,并非起源于宋。其次,“詩史”二字,也不是起源于宋。再次,楊慎沒有考證就引用,是因為他對宋人本身就有偏見,所以借此否定宋人。
類似的還有《少室山房筆叢》中的“太白子厚”“杜詩”“五云太甲”“孫洙”等多條辨析,可見胡應麟對杜詩出處的辯證,具體、深刻、細微。
綜上所述,胡應麟的詩論著作《詩藪》從“體格聲調、興象風神”的理論出發,對杜詩進行了全方面的評述,并對杜甫總體的詩歌地位評價極高;他的考據之作《少室山房筆叢》則對杜詩的出處或他人的考證作了辨誤,反映他做學問的嚴謹態度,這既可以窺見胡應麟對杜甫的評論以及他的詩學主張,也可以窺見杜詩在明代的傳播及產生的影響。
[1][明]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3]吳晗.胡應麟年譜[A].吳晗史學論著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4]冀勤.金元明人論杜甫[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