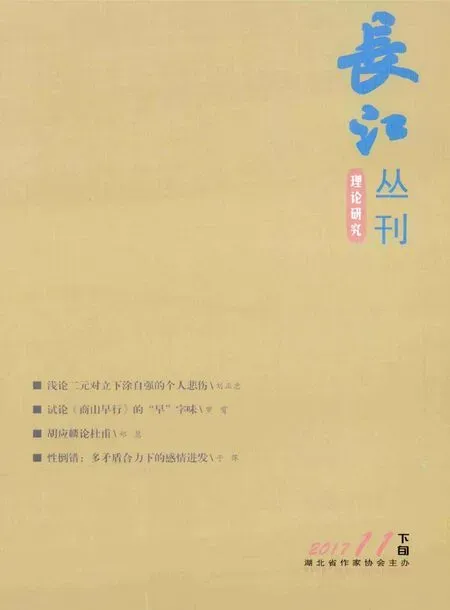恍兮惚兮,其中有像
——論夢境與藝術創造
王 旭
一、夢境為藝術創作提供新“能量”
夢有很強的生命力與想象力,它可以對事物、人物進行揉捏變形。如果說把夢境作為創作的源泉,那么題材范圍、創作思路會被無限的擴大,表現出來的可能是天馬行空的、有意味的。人們常說生活為藝術創作提供無盡的源泉,當然夢境與生活也是緊密相連的,希爾德布朗特提到“不管夢見什么,夢總是取材于現實,來源于對現實沉思默想的理智生活……不論夢的結果如何變幻莫測,實際上,總離不開現實世界。”比如亨利?盧梭的作品《夢》,作品描繪的是少女夢見自己在熱帶叢林的情景。畫面單純的、純真的風格散發著大的誘惑力,給觀眾的視覺帶來新的刺激與沖擊力,畫家在畫中探索著非理性的一面,從而獲得了更大的創作自由。畫家將現實中存在的事物并將其進行改裝、凝縮、夸張、倒置或重構的手法進行創作,體現出其獨特的靜謐。夢對畫面的滲入產生了神奇的效果,當然不僅僅是靜謐,也有奇怪荒誕的畫面。賓茲說道:“夢的內容十分之九是荒誕無稽的。”可見夢的內容千變萬化影響著藝術家的創作。在西方的諸多流派中,超現實主義就是將潛意識與夢的經驗糅合在一起,畫中常常表現的“無意識”的、“本能”的現象是區別其他畫派的主要特點。
二、夢境中的意象在創作中的體現
藝術創作的獨特性,重點在于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意象物化。夢糅合著現實生活中的支離片段,又受到內外部感覺刺激的影響。夢與創造性文學素材之間存在并不是偶然巧合,夢境中不同的事物卻有著相似的獨特的象征寓意,藝術家們通過藝術構思再運用獨特的方法、形式進行創作表達對現實生活的訴求感悟。《釋夢》中施萊麥契爾說到概念與意象的特點,清醒狀態的特征是思想活動以概念表現出來的,夢是以意象進行思維的。也正是因為夢的意象,藝術家可以構建出一個夢思的無序化與神秘自由的氣氛。米羅的作品《人投鳥一石子》,畫面中色塊的分割及對比色的應用,表面上看畫面充斥著人與鳥互動的歡樂愉悅氣氛,體現著單純性,其實這幅畫是對情欲的贊美。畫家的創作進入了精神學的領域時,就會觸及到心靈的最深處,將令人羞澀、隱晦難懂的形象以抽象的符號或是單純的線條表現出來。夢的象征意義不僅在作品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本我”的一種表現。童年的記憶與經驗也在米羅作品中有所體現。童年的經驗再現與米羅的創作似乎有著一定的聯系,畫中所呈現的書寫自動化現象似乎與夢的記憶過旺現象也有著相似之處。畫中無厘頭的散碎的耐人尋味的符號,從夢的角度來說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意象”的體現在中國古代也有所體現,中國畫梅蘭竹菊在繪畫中也有著不同的隱喻。不同國度、不同時代孕育著不同的文化與情感,關乎于“意象”在作品中的體現及傳達的情感也是別有風味的。
三、中西“夢文化“的哲學觀
夢具有原始與幼稚的特點,弗洛伊德指出夢實際上起源于某種罪惡之念,或迫切的性沖動,“罪惡之念”的說法似乎與戰國時期荀子“性惡論”相似,夢的工作將隱念改造為原始的顯夢。幼兒期是“原始”的一部分,因此一些畫家的作品中會出現類似孩童涂鴉的內容也不足為怪。西方的藝術家汲取夢境或潛意識的靈感,作品中都有體現“潛意識”、“本我”的特點。在中國,也有將潛意識的夢境結合繪畫進行創作的做法,比如85’新潮的藝術家們,雖沒有西方明確鮮明的特征,但有受到夢境或潛意識的影響。中國古老的傳統的文化思想也與夢境相聯,比如厚葬、占卜、“靈魂升天”等思想,比如《左傳?成公十年》記載晉侯夢大厲一事;《莊子》文中記載關于“夢”的敘事如“莊周夢蝶”的經典故事。其中,莊子夢“蝴蝶”實則代表了一種哲學思想,無論是周莊“夢蝴蝶”或亦是蝴蝶“夢周莊”,體現人與物之間的物化,不知是蝴蝶飛進周莊的時空,還是周莊飛進蝴蝶的時空,世間萬物都在不斷的變化中,將兩時空合二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個典故的蘊意無不充斥著道教的氣息,中國的夢文化似乎有著老子、莊子思想理論的引入。傅正谷先生在《夢賦》中概括了夢文化有著原型性、民俗性特點,并且這些特點都滲透社會的各個領域,在民俗中也起著重要作用。中西方的夢文化是有區別,兩種的文化底蘊的不同等等因素,各自綻放不同的光彩。
四、結語
無論是繪畫或是典故,夢賦予他們新的生命力,增添獨特韻味。一種流派或風格必須放在特定的時代才有它更大的價值與意義,西方的未來主義的命運注定是短暫的,之后轉變為超現實主義也是必然,也是因為他們瘋狂的無政府主義也結束了輝煌的十年。中國偏解夢,預示未來;西方偏釋夢,解釋過去。夢境、幻覺屬于潛意識的一種表現,他們在中西藝術中都有體現,都綻放著不同的色彩,在畫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恍兮惚兮,其中有像,萬物都是相互聯系的,關乎夢境的藝術作品也是可以相通的,也是可以跨越國界被理解的。
[1][奧]弗洛伊德.釋夢[M].孫名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2][奧]弗洛依德.弗洛依德心理哲學[M].楊紹剛,等,譯.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