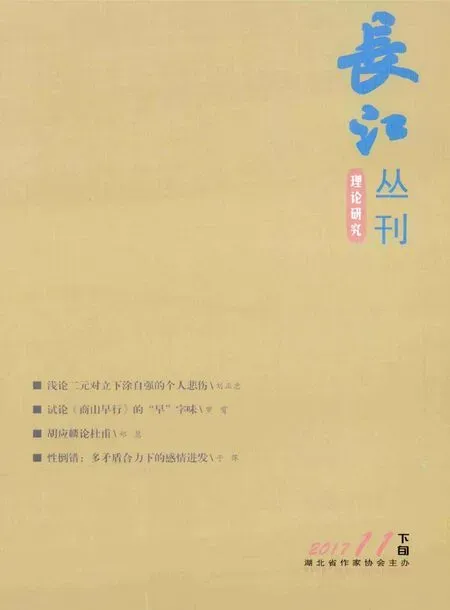舞蹈作品《羚羊的外套》中“象征”手法的應(yīng)用
曾佳露
一、“象征”的界定
象征手法是指通過(guò)某種具象化的形象或事物來(lái)含影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現(xiàn)某種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在空間的更迭之中我們能夠通過(guò)細(xì)微的邏輯聯(lián)系產(chǎn)生思維聯(lián)系,繼而拓展人們的聯(lián)想,在單一事物之中縈繞著不同的回味,與此同時(shí)又能夠給人以簡(jiǎn)練、形象的實(shí)感和質(zhì)樸詳實(shí)的感情走向。象征的本體意義和象征意義之間本沒(méi)有必然的聯(lián)系,但通過(guò)作者對(duì)本體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繪,會(huì)使藝術(shù)欣賞者產(chǎn)生由此及彼的聯(lián)想,從而領(lǐng)悟到藝術(shù)家所要表達(dá)的含義。
象征在修辭手法之中其實(shí)是一種較為隱晦的比喻,并非言語(yǔ)直敘而是通過(guò)邏輯連接進(jìn)行意象映射,是將一類(lèi)事物轉(zhuǎn)化為另一種更豐富、更有價(jià)值的事物的一種技巧,正因?yàn)檫@一特點(diǎn)在藝術(shù)作品之中我們較多的使用著“象征”這一手法。象征打開(kāi)了讀者或觀眾的思維,使其開(kāi)始因視覺(jué)或聽(tīng)覺(jué)的感觸而想象,那么比喻同樣可以將他們拉回現(xiàn)實(shí),回到作品想表達(dá)的深刻意義當(dāng)中。
二、《羚羊的外套》中“象征”的體現(xiàn)
在作品《羚羊的外套》道具將“象征”的意味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而該作品的編導(dǎo)者正是在這樣一種抽象與具體的把控間,進(jìn)行著意象與觀念的輸出。當(dāng)我們?cè)谶M(jìn)行古典舞訓(xùn)練時(shí)“劍”、“水袖”、“團(tuán)扇”、“傘”、“手絹”等道具都是一種肢體外延的出現(xiàn),在立體的空間中最大限度的拓展舞者的情感長(zhǎng)度與空間占有狀態(tài),配合至不同的舞姿造型當(dāng)中,內(nèi)在意蘊(yùn)的呈現(xiàn)方式便更加凸顯。
舞蹈作品《羚羊的外套》起初的整體基調(diào)以綠色為主,給人以平靜祥和,自然穩(wěn)定的狀態(tài),羚羊家族在這一片綠意之中更是顯得無(wú)比幸福,同時(shí)也為作品后部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埋下了一個(gè)戲劇沖突的伏筆。編導(dǎo)通過(guò)“偷獵者”的槍響,徹底打破了羚羊家族安逸并且快樂(lè)的遷徙。“孕婦羊”倒地,并且流產(chǎn)。在“孕婦羊中槍”的舞段中編導(dǎo)者運(yùn)用了紅色的絲綢來(lái)表示流產(chǎn)。鮮紅的絲綢從“孕婦羊”的肚子里緩緩的流出。在整個(gè)黑暗的色調(diào)里出現(xiàn)最鮮亮的一抹紅綢。使得整個(gè)舞蹈都陷入了恐懼和死亡的狀態(tài)之中,為這之后的舞段沖突做了一個(gè)很好的鋪墊。在人的性格走向之中,“恐懼”的極致便是“憤怒”羊群們的悲憤與恐懼交織上升,而“羚羊王”為了保護(hù)“羊群”也中槍身亡。當(dāng)“羚羊王”落入黑色的綢子上,羊群跟隨著黑綢子一起運(yùn)動(dòng),這時(shí)的黑綢子象征著盜獵者捕殺它們用的黑網(wǎng),通過(guò)這一道具的使用描繪著羊群不可靠近的部分,甚至意象化著“恐懼”的源點(diǎn)。
羚羊?qū)儆谂继隳颗?苿?dòng)物,它特殊的體型與姿態(tài)對(duì)于舞臺(tái)呈現(xiàn)而言十分困難。編導(dǎo)一反常態(tài),通過(guò)芭蕾的輕盈干凈的足尖腳下動(dòng)作來(lái)模仿羚羊的蹄子的走路基本的韻律,而作品的基本手勢(shì)是四指并攏,大拇指捏到中指的第二處關(guān)節(jié)。在作品的運(yùn)行過(guò)程之中幾乎沒(méi)有出現(xiàn)全身直立的狀態(tài),多數(shù)以上半身與下肢形成九十度直角的狀態(tài)來(lái)完成動(dòng)作語(yǔ)匯,將羚羊優(yōu)美的后背線條表現(xiàn)出來(lái),這樣舞者用特殊的動(dòng)作語(yǔ)匯就可以表現(xiàn)出羚羊的基本體態(tài)。“膝蓋微屈;膝蓋的動(dòng)率向上,指尖觸碰地面;手背發(fā)力”這一動(dòng)作語(yǔ)匯象征著羊群遷徙過(guò)程中小幅度奔跑的靈敏姿態(tài),體現(xiàn)羚羊的敏捷與活躍。
三、《羚羊的外套》中“象征”的意義
在舞蹈作品的構(gòu)建過(guò)程之中,我們常用服裝、道具、動(dòng)作語(yǔ)匯和形象塑造比喻形象,用來(lái)展現(xiàn)編導(dǎo)所要傳達(dá)的意圖并且揭示作品創(chuàng)作的深刻內(nèi)涵,如萬(wàn)素所編創(chuàng)的《家長(zhǎng)里短》、黃奕華所編創(chuàng)的《說(shuō)蘭花》和田露編創(chuàng)的《翠狐》等等,而東師舞蹈作品《羚羊的外套》就是將文學(xué)修辭手法與舞蹈創(chuàng)作藝術(shù)縱橫交織的一大佳作。
古代的文人墨客用梅蘭竹菊來(lái)抒發(fā)自己深深地君子情懷,用青竹松柏表達(dá)自身的剛毅性格。《羚羊的外套》中“外套”一詞,其實(shí)不僅僅是該標(biāo)題的核心詞匯,與此同時(shí)在象征的作用下也傳遞著作品主題的內(nèi)旨意象。整個(gè)作品之中筆者最為偏愛(ài)的是編導(dǎo)的那個(gè)“分鏡頭”處理,一連串近乎瘋狂的獵殺聲中,那幾張沾滿血跡的羊皮猶如生產(chǎn)線一般傳送出現(xiàn)著,傳送帶是靜止空間中空間流轉(zhuǎn),是流逝時(shí)間中的固定流逝,一天一撥,周而復(fù)始,人類(lèi)就是不斷的在靜止的空間與永恒的時(shí)間中完成著自己的犯罪。編導(dǎo)通過(guò)外套的外在形象象征著人類(lèi)對(duì)自然的破壞,同時(shí),也是“外套”連接著虛實(shí)的空間。《領(lǐng)養(yǎng)的外套》這一作品在空間的使用上通過(guò)“虛”“實(shí)”兩點(diǎn)貫穿出現(xiàn),“虛”——是我們無(wú)法真實(shí)見(jiàn)到的獵殺生產(chǎn)的血腥場(chǎng)景,人們用藏羚羊唯一的“外套”制成外套,滿足自己的虛榮;“實(shí)”——那些已經(jīng)被奪去“外套”的藏羚羊們,倒地抽搐即將死去,當(dāng)他們失去自己的“外套”時(shí)便會(huì)死去。正是這極具象征意味的“外套”將“虛榮”與“生命”進(jìn)行聯(lián)系,從而告訴觀眾人類(lèi)貪婪的欲望對(duì)整個(gè)大自然是多么的不公平。
在快速發(fā)展的現(xiàn)如今,人類(lèi)用了多少動(dòng)物唯一的“外套”滿足自己的私欲和虛榮,使許多物種瀕臨滅絕。如果說(shuō)這個(gè)作品的前半部分訴說(shuō)的自然界溫情友好的一面,羚羊視角的選擇讓我們感受到了難以言表的喜悅,隨著槍聲的響起后半部分的羚羊視角是我們感同身受,已經(jīng)無(wú)法在麻木不仁的羚羊旁觀,那樣的切身之痛,猶如驚雷一般。
四、結(jié)語(yǔ)
在舞蹈作品中,用象征體現(xiàn)表象意義,再借助隱喻表達(dá)作品的更深層次含義。舞蹈作品《羚羊的外套》用“外套”為作品創(chuàng)造了多樣的象征意義,使作品賦予人更多的聯(lián)想,同樣也用“外套”隱晦地揭示了人類(lèi)對(duì)待動(dòng)物殘酷的暴行,并且站在動(dòng)物的立場(chǎng)上對(duì)人類(lèi)做了一次心靈的拷問(wèn),反思人類(lèi)到底對(duì)動(dòng)物的這唯一一件外套做了什么。它們就只有這一件“外套”,為什么我們還要這么不知足的去爭(zhēng)搶?zhuān)?dāng)我們?cè)诳催^(guò)這個(gè)作品之后不禁地會(huì)問(wèn)問(wèn)自己以后還穿皮草嗎?
- 長(zhǎng)江叢刊的其它文章
- 海南省中小學(xué)校園足球聯(lián)賽體系的發(fā)展模式
- 高職國(guó)際貿(mào)易專(zhuān)業(yè)《國(guó)際市場(chǎng)營(yíng)銷(xiāo)學(xué)》課程教學(xué)模式改革探析
——基于跨境電商視角 - 對(duì)尼泊爾漢語(yǔ)教師志愿者如何做好YCT考試推廣的幾點(diǎn)建議
- 從社員狀況看吉林省解放區(qū)合作社的發(fā)展
- 關(guān)于構(gòu)建“互聯(lián)網(wǎng)+”大學(xué)英語(yǔ)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的問(wèn)題和建議
- 自貢地域文化圖形與周邊產(chǎn)品開(kāi)發(fā)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