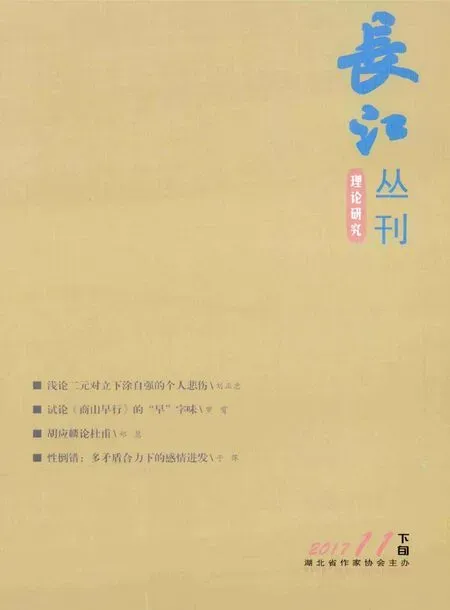從段祺瑞的性格看其仕途沉浮
張曉林
“三造共和”擺脫了血腥殺戮的殘酷,一切都在“和諧”的氛圍中發展。這一切都離不開段祺瑞沉機觀變的性格影響下,對紛繁復雜的政治局勢的洞悉與把握,不僅善于把握時機,還能審時度勢,創造機會,乘勢而動,做出適當的政治判斷,順應時勢發展。“三造共和”可謂是其一生榮耀。
一、三造共和:沉機觀變的性格成就其一生榮耀
“一造共和”的實現,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袁世凱的發縱指使……袁世凱恍悟南北終是兩家,及決計從清室入手。段祺瑞始而積極與南方停戰議和,繼又多方脅迫清廷。第二,段祺瑞對波詭云意的政治風云及袁世凱用意的洞悉與把握……才會有此既順應時勢、又遂袁心愿的“通變達權”之舉。第三,段祺瑞個人動機的驅使……。”
袁世凱的地位穩固后,稱帝的野心日益顯露,段祺瑞對此甚是反對。段祺瑞深知洪憲帝制不得人心,為避免落得背主求榮的罵名,便稱病辭職。段以退為進,表面的無關緊要,實則窺趨著全局的發展大勢。隨著討袁聲浪的愈演愈烈,袁世凱不得不請自己的老部下段祺瑞出山,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再創共和”。可見,在復雜的政治局勢下,段祺瑞沉機觀變的性格起著重要作用。
段祺瑞認識到,北洋守舊派睹新政府之改組,深懼不利于己,便造就了決議復辟的張勛。再加上自身昔日的威望,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便找到了復辟狂張勛。待張勛到京后,立即組織討逆軍,對其打的措手不及,此即“三造共和”。這一切都與其沉機觀變的性格息息相關,使其能在復雜的局面下,做出正確的政治決策,扭轉時局發展,成就自己一生的榮耀。
二、府院之爭:不甘雌伏的性格使其大權在握
對德宣戰問題,直接促使“府院之爭”達到白熱化,在加上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參與,形成了黎元洪與國會為一方,段祺瑞與內閣為另一方的相爭局面。面對黎元洪的毫不相讓,段祺瑞亦毫不示弱。黎元洪自恃國會、美帝國等的支持,于23日免去了段祺瑞的總理之職。段不甘心權力的喪失,臨行去天津前通電全國,強調“共和各國責任內閣制,非經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署名仍用國務院總理段祺瑞。”寥寥數語,蘊含著無限殺機。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從中使然,段祺瑞便找到了復辟狂張勛這枚棋子,張勛以調停名義進京,策動清室復辟,及至段祺瑞在馬廠誓師討逆,復辟短命而亡,段祺瑞即回京復任總理之職。府院之爭,終以黎敗段勝的結局而收場。事實證明:“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則更不可動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
三、用人方法:剛愎自用的性格最終使他虎落平陽
段祺瑞在用人方面恪守“用人不疑”的古訓,只要他認為可靠的,就信任有加,甚至偏信、專信、獨信、袒護有加。段祺瑞過度的偏信,專信,一味袒護下屬的過錯,使其部下個個有恃無恐、飛揚跋扈,以徐樹錚尤甚,仗著段祺瑞的偏信,“事事以己意為段意,指揮黎氏畫諾。”處處為段祺瑞樹敵。段祺瑞對徐樹錚的寵信,最終引起北洋內部,以及其他軍閥的不滿,在直皖戰爭中兵敗如山倒,付出慘痛代價。
“段一生事業,固由徐助其成,亦實敗壞與徐一人之手,此公論也。”由此可見,段祺瑞的用人方法上,偏執專信,剛愎自用,一方面,贏得了為其奔走效命的忠心部下;另一方面,不知不覺中為群小所包圍,導致他在危難之際孤立無援。
四、結語:敏銳要強助其興,偏執專信使其敗
總之,段祺瑞政治上的起浮跌宕是很耐人尋味。他審時度勢、把握全局是政治頭腦,使他避免了在政治中摸著石頭過河的危險,在詭譎復雜的政治中可以游刃有余。他那不甘雌伏的要強性格,使他面對劍拔弩張的政治局勢,仍可淡定從容的應付一切,要強的性格使其在針鋒相對的政治角逐中,可以伺機而變,保障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被動搖。此外,他恪守“用人不疑” 古訓,對部下的絕對信任,使部下甘心為他所用,是其政治成功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但是,其要強的性格,在政治中又表現出專斷獨橫、傲慢無禮、剛愎自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其與合作者的矛盾。同時,他對部下的偏信專信,不知不覺中又為群小所包圍,為他四面樹敵,這些都導致他在政治上的孤立,危險之際孤立無援,使他在政治上一次次的跌入谷底,最終無緣政治。
[1]莫建來.評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J].歷史檔案,1993(02).
[2]程舒偉,侯建明.北洋之虎——段祺瑞[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210.
[3]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態和異態—關于黎元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的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7(3).
[4]馬克思.致路?庫格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3.
[5]來新夏.北洋軍閥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241.
[6]張國淦.北洋軍閥直皖系之斗爭及其沒落[A].杜春和,等.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