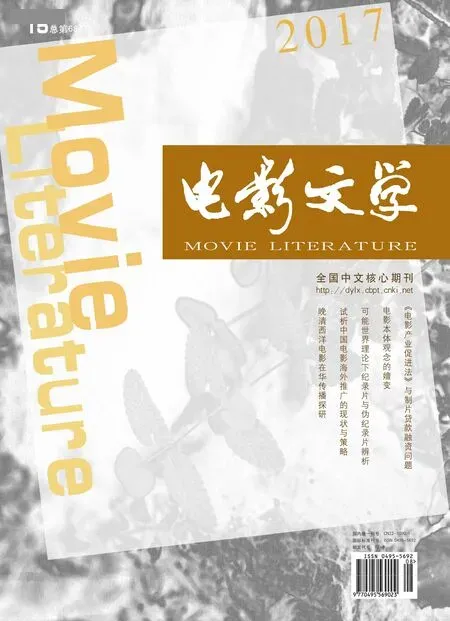電影《烈日灼心》審美價值考察
鞠維光 齊慧姝
(吉林藝術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犯罪懸疑片是商業電影時代的重要類型片,這種準類型片憑借豐富的美學體驗具有相當大的商業價值,尤其是經過數字技術和動作場面的加工處理,能夠滿足時下觀眾對于奇觀化影像的心理需求。電影《烈日灼心》是一部典型的國產犯罪懸疑片,導演曹保平融合了文藝片和商業片的藝術特質,讓這部電影具有迷幻的、吸引人的特質。片中既有犯罪現場血腥的視覺刺激場景,也有懷疑、猜測與推理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緊張的破案過程,還有結局反轉之下人性批判的溫情時刻。電影《烈日灼心》具有從多個角度出發的審美價值,值得進一步詳細地解讀和探究。
一、懸疑之美
導演曹保平橫跨影視界,拍攝了眾多膾炙人口的優秀電視劇和電影,《烈日灼心》并非曹保平的第一部懸疑片,早在2008年他就曾執導懸疑愛情片《李米的猜想》,在文藝片和商業片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電影《烈日灼心》相對于《李米的猜想》更加血肉豐滿、驚險刺激,圍繞著一樁滅門慘案展開敘事,引出了三個身份各異的結拜兄弟共同撫養一個孤女的故事,段奕宏扮演的警察伊谷春更是以偵破此案為最高目標,兄弟三人和警察伊谷春的命運經由七年前的這樁滅門案聯系在了一起。
《烈日灼心》在敘事過程中鋪設了多個懸疑點。首先,影片開始用大量觸目驚心的黑白畫面展現了七年前發生在福建西隴的滅門慘案,被奸殺的裸體女性、死相慘烈的老人、滿地的血液,以及驚慌逃竄到樹林里的四個人,其中一人不小心跌落懸崖,另一個人在逃跑的過程中不小心被樹枝刺瞎了眼睛。電影《烈日灼心》從一開始就營造了恐怖肅殺、危機四伏的氛圍,從兇案現場逃走的四個人將恐怖畫面制造的緊張感加強,這意味著犯罪分子逃走了,并未被繩之以法。逃竄過程中的種種意外,更是將敘事氛圍中的緊張情緒推升到最大。
轉眼七年后,當年逃竄的四個人只有三個人幸存下來,低調地開始了新的生活。影片從開始部分展現了犯罪現場,交代了犯罪分子始終逍遙法外,就此埋下了懸念——犯罪分子看似平靜的生活始終隱藏著不確定的危險因素,一方面是他們自身的危險性,另一方面是警察對七年前滅門案的破案是否會繼續。
然而,七年后的三個人卻是以令人意外的形象出現在鏡頭之中。鄧超飾演的辛小豐是一名協警,但出勤時卻比有編制的正式警察還要賣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在外出辦案的時候常常是傷痕累累,他的行為表現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名協警應當有的樣子。郭濤飾演的楊自道成了一名出租車司機,他開著出租車行駛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樂于助人,不計回報,甚至很多時候會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幫助別人。就算是遇到打劫自己的劫匪,他依然能夠選擇寬恕和原諒,即便是在警察伊谷春已經站在自己的車窗外,他依然決定放過這些打劫自己的亡命徒。高虎飾演的陳比覺表現出瘋瘋癲癲的癡傻狀態,似乎七年前的事件對陳比覺造成了無法挽救的精神創傷。三個人經歷過七年前的事件后,似乎形象都有180°的大轉變,其中的原因是導演曹保平留給觀眾的懸念,觀眾更傾向于猜測三個人是為了贖罪而轉變了形象,不斷做好事彌補他們當年犯下的錯誤,但辛小豐和楊自道兩個人極端的行善行為又與一名罪犯的贖罪心理不符,這其中的矛盾也正是困惑觀眾的懸念。
警察伊谷春的出場激發了片中的主要懸念,段奕宏飾演的伊谷春無法放下七年前的那起案件,當時他也是福建西隴的一名普通警察,跟著帶他的警長(師父)親眼看過犯罪現場,現場的血腥場景慘不忍睹,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帶著師父對這起案件的執念希望能夠找到線索,偵破此案。《烈日灼心》的大部分懸念都是在伊谷春的手上破解的,他一直嗅探著辛小豐、楊自道身上“罪犯的味道”,想盡一切辦法將他們二人和傻子兄弟與福建西隴的滅門慘案聯系在一起,他有著身為一名警察特有的直覺和警惕。
當懸念一層一層被剝開,辛小豐和楊自道等人的身份被揭穿,他們往日做出的善行被人理解,殺人兇手由于另外一件案子落網后對這起殺人案的輕描淡寫,都給觀眾以極大的心理震撼。正是影片鋪設的層層懸念,才給觀眾制造了難以自拔的懸念體驗的審美期待,影片的懸疑設置是十分成功的。
二、人性之美
電影《烈日灼心》改編自女作家須一瓜的長篇小說《太陽黑子》,導演兼編劇曹保平對小說中的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改動,唯一不變的是對人性之美的肯定與贊頌。須一瓜的小說《太陽黑子》是關于“救贖”的故事,七年前的福建西隴滅門殺人案只是作為一個虛化的大背景出現在小說中,小說更關注的是辛小豐、楊自道等人在“激情犯罪”之后的經歷——他們的內心煎熬、精神折磨和靈魂救贖。于是,在當年犯下的大錯面前,辛小豐和楊自道每天都努力做好事,十分極端地做好事,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幫助別人。人性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矛盾整體,人性中有善也有惡,人性的多面性本身就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作家須一瓜在小說中通過三人的“救贖”行為,表現了他們人性中的善良,展現了他們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電影《烈日灼心》雖然保留了小說中的救贖主題,但更傾向于表現人性之美。雖然辛小豐等人看似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但是滅門殺人案過后的這七年里,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經歷著內心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他們三個人始終沒有結婚,共同撫養患有心臟病的小女孩尾巴。他們帶著對福建西隴被殺害的一家人的愧疚,將他們所有的愛都給了這個跟他們毫無血緣關系的小女孩。
小說版本的故事當中,楊自道是核心人物,警察伊谷春只是作為穿針引線的線索人物出現的,并不像電影中那樣擔當起了主要人物角色。電影《烈日灼心》中的伊谷春更像是導演曹保平塑造的大眾審美下的警察角色,他心思細膩、對犯罪嗅覺靈敏,他的道德標準是與大眾道德標準相符的,他代表著絕對正義的一面,而不是小說中有些模糊了道德邊界的男性人物形象。在伊谷春咄咄相逼的心理攻勢之下,辛小豐和楊自道不斷地露出馬腳,不斷地透露出他們與當年福建西隴的滅門慘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警察伊谷春的眼里對于辛小豐和楊自道的善行善舉并沒有給予過多的重視,起碼沒有滿足觀眾的心理期待,這也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辛小豐等人的人性之善是被大眾忽視的,他們不求回報的行善與救贖并沒有得到大眾的認可。
辛小豐在成為一名協警之后,像一個“亡命之徒”一樣抓捕犯人,遠比帶有編制的正式警察更加賣命。在伊谷春調到辛小豐的派出所當警長之后,他目睹了辛小豐辦案時的奮不顧身。一次在追捕偷盜建筑鋼筋的小偷時,辛小豐追著小偷就走進了積水的建筑工地里,身為協警的他沖在最前面,一不留神腳被卡在建筑工地鋼筋的縫隙里,一下被拖入水面之下,伊谷春拼盡全力才將其救出。經歷過生死關頭之后,伊谷春對辛小豐越來越感興趣:是什么促使這樣的一名協警完成了超出分內之事?直到影片結尾,伊谷春親手將辛小豐送上了死刑臺,在辛小豐和楊自道被執行死刑后,也是伊谷春第一時間知道辛小豐只是強奸當年那起案件中的年輕女性,實施強奸的過程中對方突發心臟病身亡,滅門案的真實兇手是當年失足落崖的神秘男性,而楊自道和陳比覺也只是從犯而已,并沒有實質性的犯罪行為。
透過伊谷春的雙眼,觀眾看到了辛小豐內心的愧疚與掙扎,他一方面借自己的職務之便為社會大力打擊犯罪,一方面又與結拜兄弟楊自道和陳比覺一起撫養孤女尾巴,為了治療尾巴的病不惜盜取犯罪現場搜集到的金錢證物。在辛小豐等人的心中有一個極其嚴格的道德天平,他們按照這桿天平嚴格規劃著自己每天能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制造他們心中道德天平的,正是他們人性中無法磨滅的善。也正因如此,辛小豐和楊自道寧可被誤解而執行死刑,也不愿意養女尾巴背負一輩子的道德債,在長大成人步入社會之后抬不起頭。
三、視覺之美
商業電影離不開視覺奇觀的制造,促使觀眾走進電影院觀看電影的主要動力就是大銀幕給予自己的感官刺激。犯罪懸疑片也不外如此,在縝密的破案過程當中,需要盡力制造一種視覺上的奇觀化審美體驗,讓觀眾能夠透過電影語言獲得更多的信息,并非一味地依靠演員的對白才能看懂電影。
導演曹保平在電影《烈日灼心》中運用了手持攝影的方式,呈現出半紀實的影像質感。經過影片一開始的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兇殺現場鏡頭展示之后,手持攝影帶來的搖晃感就制造了緊張的情緒,這種情緒從影片開始到結束始終縈繞在觀眾心頭。導演曹保平希望營造一種半紀實感,讓觀眾感覺影片中發生的人和事都有可能是真實發生的,而非虛構。為了避免觀眾與片中呈現的所謂真實的距離感,手持攝影的搖晃感制造了一種情緒代入的主觀視角,攝影機正如同觀眾的雙眼,在現場監視著鏡頭中人物的一舉一動。
影片《烈日灼心》在手持攝影的過程中,不斷地拉伸鏡頭,尤其是在鏡頭中只有兩個人的情況下,鏡頭的拉伸不僅代表了觀眾的觀察視角,也將發起對話的人的視角代入其中,當鏡頭推近另一個人的時候相當于審視對方的反應、等待對方的答案,與此同時,觀眾也可以更加細致地看到演員的表情和小動作,參與偵破疑點的懸念解密過程中。
同時,該片在很多畫面的表現上,都選擇了一個偷窺視角,這種鏡頭語言與鏡頭拉伸的藝術效果如出一轍,偷窺視角不僅能“隱秘地”窺探人物的情緒變化,更加能夠表現出半紀實的鏡頭真實感,賦予鏡頭主觀偷窺的情緒和身份狀態。
《烈日灼心》的鏡頭語言營造的視覺美學狀態令人著迷,這是建立在懸念迭起的敘事過程之上的鏡頭語言。從影片開始交代的滅門慘案現場就對“誰是兇手”的最大疑點埋下伏筆,觀眾隨著警長伊谷春的視角和步伐一步步地接近了“真相”,偵破案件的真實的情緒代入感給觀眾極大的感官刺激。同樣的鏡頭語言,最終在結尾劇情反轉之后,前面代入錯誤情緒和情感的鏡頭畫面,都衍生出了截然相反的意義,辛小豐、楊自道和陳比覺為了贖罪犧牲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這種間接傷害和間接補償是否能夠等價,觀眾能夠感受到辛小豐等人靈魂中的善良和美麗,也正是這種鏡頭的真實美學給予觀眾的思考。
四、結 語
經歷過七年前的滅門慘案之后,辛小豐成為一名協警,終日賣命辦案,每天都冒著最大的危險奮斗在打擊犯罪第一線。楊自道成為一名出租車司機,拾金不昧、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已經成為他生活的中心,每天究竟能夠賺多少錢并不重要。陳比覺則在前文交代的樹枝戳瞎眼睛的情節下,成了瘋瘋癲癲的“傻子”。三個人為了一樁并非與其有直接關系的殺人案,在七年的時間里無時無刻不在期待著靈魂的救贖。導演曹保平將三個“罪人”的贖罪行為帶給人們的思考,不僅停留在法治和道德層面,更是提升到人性之上,希望觀眾透過《烈日灼心》的每一個鏡頭畫面都能夠感受到人性中至真至純的真實情感,以及那容易被人忽略的真實。電影《烈日灼心》不僅是一部在犯罪懸疑類型片上有著懸疑審美價值的作品,在人性關注與審判、視覺美學之上,都存在極大的審美價值和研究價值,影片同曹保平前作《李米的猜想》一樣,游走在文藝片和商業片的邊緣,是當前國產電影市場中不可多得的優秀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