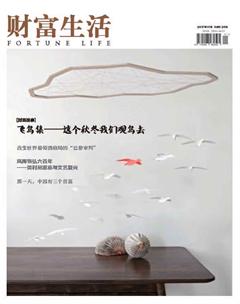風雨恢弘六百年——貝利尼家族與文藝復興
長夜之飲
提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豪門,人們總是首先想到美第奇家族,而近日于上海拉開帷幕的“奇跡:貝利尼家族與文藝復興特展”,又讓人們對貝利尼家族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生出了了解與好奇。此次大展由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意大利貝利尼博物館、達芬奇理想博物館共同合作,貝利尼博物館館長、貝利尼家族第21代傳人路易吉·貝利尼(Luigi Bellini)為中國觀眾帶來了橫跨6個世紀,包括“文藝復興三杰”真跡在內的459件藝術品。無論你是否已經親臨現場觀賞過這些文藝復興時期的杰作,都可在本文中一品文藝復興與貝利尼家族的那些事兒。
人文之光
1830年的某一天,在一封由W·戴斯(W.Dyce)與C·H·威爾森(C.H.Wilson)合寫給米多班克勛爵(Lord Meadowbank)的信中,寫作者提及了一場曾經發生在意大利的藝術運動,并以法文詞“重生(renaissance)”為其冠名——根據《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記載,這是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開端的五百年后,首次在英語及世界語言范圍內獲得了明確的指稱。
文藝復興,現通常指歐洲14世紀至17世紀的歷史時期,以及該時期內的文化藝術發展運動。它自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境內的文化運動發端,隨之擴散、席卷整個歐洲,被視為中世紀與現代世界之間的橋梁,也是開啟現代文明的一束晨曦。
文藝復興的是人文主義(Humanism)的再復興,其根基溯源自古羅馬時期的人本主義(Humanitas)與古希臘哲學,前者出自政治家西塞羅(Cicero)與文豪格利烏斯(Gellius)的著作,后者的代表人有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與他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這種思想很快就在藝術、建筑、政治、科學與文學中扎根,傳播——從畫家尊重線性透視原理、建筑師重新研配出混凝土配方開始,一場復古以求新知、面向人文與未來的革新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
作為一場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提倡古籍與古希臘、羅馬時期知識的再學習,打破了拉丁語的文化壟斷,重新賦予各類地方語言使用權與重要性;透視與其他作畫技術的發展為更為自然、寫實的作品提供了創作可能;教育改制逐漸在歐洲興起,神學獨斷的局面就此改觀。政治上,文藝復興奠基了現代民主的發展;科學上,觀察與歸納推理的方法被廣為傳授。
更為重要且明顯的,文藝復興為世界文化貢獻了諸如萊昂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與米開朗琪羅·博那羅蒂(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這樣的巨匠。在他們的人生軌跡與存世作品中,人類得以窺得文明本身的智慧、理想與浪漫是何等無遠弗屆。
14世紀起,在文藝復興心臟的佛羅倫薩(Florence),美第奇(Medici)家族對文明與奢華的追求帶動了藝術品的瘋狂投資;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陷落后,最后一批繼承著羅馬文化的希臘學者紛至沓來,渡向歐洲。這股裹挾著文明與藝術的風暴洋洋灑灑地從佛羅倫薩吹播到熱那亞(Genova),到博洛尼亞(Bologna)與米蘭(Milan),最終越過亞平寧山脈(Appennino),拍岸在威尼斯(Venice)這座千島之城。
生于威尼斯
英國詩人拜倫(Byron)曾這樣描述他眼中的威尼斯:“我自童年便深愛著她,這座深埋我心的夢幻之城(I loved her from my boyhood—she to me was as a fairy city of the heart)”。時至今日,當我們以現代的目光去審視這座具有千年歷史的城市,便很難不對古人的智慧與創造力發出驚奇的嘆息。
身處古羅馬文明的腹地,意大利境內大大小小的古城中,威尼斯或許是唯一一座與羅馬毫無關聯的城市——它始建于公元四世紀,西羅馬帝國已然覆滅,來自歐洲腹地、阿爾卑斯山下的倫巴第人(Lombards)向南入侵,進入亞平寧半島,位于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西北岸的原生居民不堪其擾,漸漸搬離海岸線,在沿海瀉湖中的島嶼與泥灘上安家落戶,這便是威尼斯的前身。
威尼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一個地理與城市意義上的“中心”:它是由瀉湖淺水區里的數十以至數百個定居點不斷擴張而來。威尼斯所處的瀉湖與外海有三個通道相連,大自然是最為精確而公正的計時器,每日潮汐涌入瀉湖一次,再退去一次,形成一次沖刷城市、清理運河的水循環,一月潮起潮落六十次、一年七百三十次,一千五百年來從未中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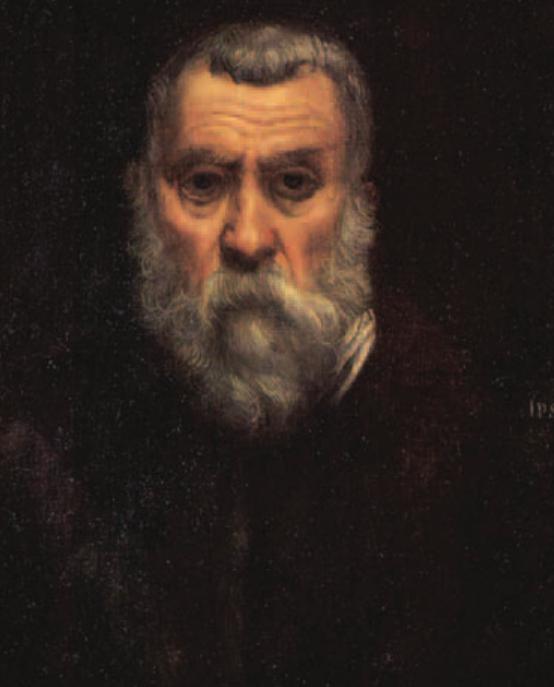
最初的威尼斯本島上,只有一座教堂、一方廣場、兩座雨水井。隨著移民不斷進入城市,威尼斯人從內陸伐來木材,加工成長長的木樁打入泥灘之中,在此之上鋪設板材、磚石,再建立地基,修建房屋。深埋入泥的木樁隔絕了氧氣,可以百年甚至千年維持不腐,而現在的威尼斯正是建立在這一片名副其實的“地下森林”之上,擁有一百四十二座島嶼與四百三十八座橋梁,可謂一座以木為基的海上浮城。
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作為亞德里亞海的咽喉要沖,它背靠廣袤的歐陸,航線直通北非與中東的黎凡特(Levant)地區,影響力甚至遠播黑海沿岸。在城市建立之初,威尼斯與當時的地中海霸主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聯系緊密,文化藝術發展受拜占庭風格的影響十分深刻。然而,隨著商業的發展帶來巨額財富,從九世紀起,力量不斷壯大的威尼斯便嘗試著脫離拜占庭的陰影。
1204年,遠征的十字軍出人預料地洗劫了作為同盟方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一蹶不振,而參與十字軍東征的威尼斯則趁機在地中海壯大,徹底取代了拜占庭帝國在地中海貿易與軍事中的地位,就此迎來城市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威尼斯的海軍與商船頻繁地往來于亞、歐之間,來自的東方的財富如雨般傾瀉在圣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上,金碧輝煌的圣馬可大教堂(Basilica San Marco)至此成為了城市冠冕上的一顆明珠。
此后的二百年間,威尼斯盡情地享受著它獨立而顯赫的地位。意大利半島特殊的地理與歷史因素造就了小國寡民式的權力分裂,威尼斯作為一個寡頭政體的“共和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來自四面八方的商人與手工藝者則不斷推動著威尼斯文化與藝術的發展——
1430年,喬瓦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這名威尼斯學派(Venetian school)的奠基人與推動者,出生在一個藝術世家之中。
威尼斯學派鑄造者
從十五世紀的后半葉起,威尼斯興盛起一種特殊的作畫風格。有別于盛行意大利一時、受達芬奇、米開朗琪羅與拉斐爾(Raphael)廣為使用的風格主義(Mannerism),威尼斯畫家吸收了一定的早期尼德蘭繪畫(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影響,并在畫作中運用大量明亮的色彩,添加一定的東方元素與柔和的視感,塑造出一種與眾不同且影響力極強的藝術風格。
從喬瓦尼·貝利尼的工作室開端發展,經歷喬爾喬內(Giorgione)、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委羅內塞(Veronese)與巴薩諾(Bassano)等人的傳承與發展,一百多年間,威尼斯學派已經成為威尼斯藝術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城市雋永不滅的精神財富。
與宋朝時的“三蘇”類似,喬瓦尼·貝利尼出生在一個畫家滿門的藝術世家。他的父親雅科波·貝利尼(Jacopo Bellini)是當時威尼斯的著名畫家,主持設計、裝飾了很多威尼斯的建筑;其畫作現存真跡很少,有一些存留的速寫作品被大英博物館與盧浮宮收藏,其中優秀的線性透視手法、豐滿的裝飾紋樣與明亮的飽滿的色彩均為后期威尼斯學派的標志特點。
喬瓦尼·貝利尼自小在父親的工作室與房子中成長,與比他年長僅一歲的兄長、雅科波的長子真蒂萊·貝利尼(Gentile Bellini)長期維持著兄弟情深、亦師亦友的良好關系。盡管在后世的認知中,喬瓦尼·貝利尼取得的藝術成就更高,但在當時的藝術鑒賞圈子中,更為藝術投資人與鑒賞家喜愛的是其兄長真蒂萊的作品。
從1474年起,真蒂萊·貝利尼成為了威尼斯總督的官方肖像繪制人。與貴族的頻繁接觸帶給了真蒂萊更多作畫的機會,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描繪大場面的畫作,尤其是關于威尼斯會堂(Scuole Grandi of Venice)的作品,其中大量神態各異的人物形象足以供后世想象彼時威尼斯的貴族生活。1479年,奧斯曼帝國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向威尼斯尋求一位藝術家,真蒂萊便被威尼斯政府送去了土耳其。他在次年歸來,同時將東方風格的元素帶入了畫作之中。他被視為是西方畫作中東方主義(Orientalist)的奠基人與代表人。
另一名對喬瓦尼·貝利尼產生影響的畫家是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他是一名古羅馬考古學的學生,是雅科波的女婿,喬瓦尼的姐夫。像當時眾多的畫家一樣,曼特尼亞在透視上做出了全新的嘗試,并成功使用降低天際線的方式給畫作增加恢弘的儀式感。作為一名對古羅馬藝術研究深刻的藝術家,他的畫作充滿磚石與金屬的質感,人物也往往顯得堅硬甚至冷酷無情,顯示出一種雕塑向畫作靠攏的繪畫傾向,也對喬瓦尼·貝利尼早期的畫作產生了鮮明的影響。
作為一名站在眾多藝術巨人肩膀上的畫家,喬瓦尼·貝利尼一生中作畫風格的不斷演變,便是威尼斯學派從發端漸至成熟與定型的過程。在藝術家眾多的威尼斯,喬瓦尼出名并不算早,近三十歲時才有完成度很高的獨立作品問世。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欣賞者很容易捕捉到他對于宗教的沉思與對個人情懷的悲愴(pathos),以及代表性的,柔和而浪漫的陽光色調。他早期的作品中,從組成與風格中,仍能看出對姐夫安德烈亞·曼特尼亞的學習痕跡。
1470年開始,喬瓦尼接到了獨立的工作邀約,與他的兄長真蒂萊一起在威尼斯會堂供職、學習。逐漸的,他的畫作開始擺脫曼特尼亞線條中金石般的質感,變得更加柔和、明亮。到了1505年,《圣扎卡里亞祭壇畫(San Zaccaria Altarpiece)》全然展現了喬瓦尼成熟的藝術創作能力與威尼斯學派的魅力:高視角下,體態整潔又互相聯動的人物合理地分配于空間之中,動作透露出一種寧靜祥和又高貴恢弘的氣質。這幅畫作被稱為是威尼斯學派的代表作,也是文藝復興全盛時期(High Renaissance)的經典作品之一。
喬爾喬內是喬瓦尼·貝利尼的第一個藝術繼承人。作為一名天資極高的畫家,他在典型的威尼斯學院風格畫作中加入了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與暈涂法(sfumato),這兩種技法都是萊昂納多·達·芬奇的拿手好戲,而喬爾喬內也從不掩飾達芬奇對他的影響。一度,喬爾喬內的影響超越了與他同齡的提香,以及眾多的威尼斯學派畫家,甚至他的老師喬瓦尼·貝利尼本人,但他不幸在1510年染疫去世,時年三十三歲,比老師喬瓦尼的逝世尚早六年。
喬爾喬內之后,威尼斯學派迎來了齊名的“三杰”: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羅內塞。
在他們三人中,提香最為年長,也是將喬瓦尼·貝利尼的風格繼承得最為完整的畫家。作為文藝復興全盛時期最杰出的畫家之一,在他所處的時代,提香被稱為“群星中的太陽”,其畫作兼工肖像畫、風景畫及神話、宗教主題的歷史畫,存世有三百多幅,其中頗為著名的《戴安娜與阿克泰翁(Diana and Actaeon)》曾售出五千萬英鎊的高價,并在世界多座博物館內均有副本珍藏。
丁托列托曾經是提香的學生,但有曾學畫十天就被遣返的逸聞,一種說法是提香過于嫉妒他的才能,另一說是提香覺得他已經可以自立門戶。雖然如此,丁托列托一直對提香的藝術成就頗為仰慕,曾在自己的畫室上書寫上“米開朗琪羅的素描和提香的色彩(Il disegno di Michelangelo ed il colorito di Tiziano)”來自勉。他的恢弘作畫風格被稱為“擁有瘋狂的熱情(Il Furioso)”,其中戲劇性的透視和光線效果使他成為巴洛克藝術的先驅。
委羅內塞的全盛期位于提香與丁托列托之間,他早年屬于風格主義,后來受提香影響很深,漸次發展出屬于自己特點:極度鮮明色彩,恢弘的人像,博大的場面與不乏生氣的寧靜。法國藝術批評家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于1860年寫道:“委羅內塞是最偉大的使用顏色的專家,甚至比提香、魯本斯(Rubens)和倫勃朗(Rembrandt)都要偉大,因為他可以用自然的色調表現光線,現在的學院還用明暗的對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