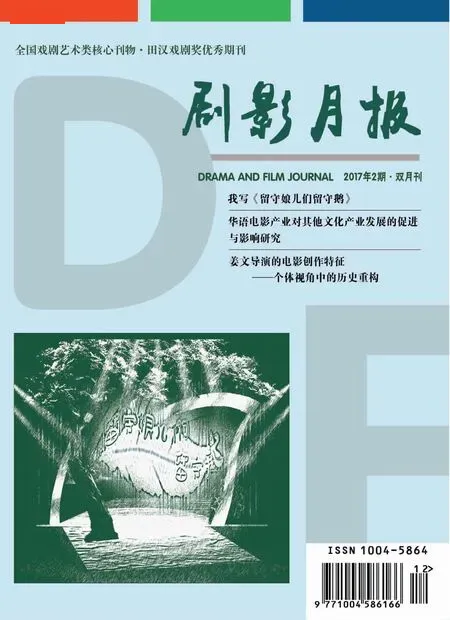戲曲電影如何審美
——以昆曲電影《十五貫》為例
■馬旭苒
戲曲電影如何審美
——以昆曲電影《十五貫》為例
■馬旭苒
昆曲電影《十五貫》拍攝于1956年,根據浙江《十五貫》整理小組整理本改編而成,導演淘金,主演周傳瑛、王傳淞等,影片講述了無錫肉鋪老板尤葫蘆的女兒被誣告是貪財弒父,最終冤屈得以昭雪的故事。影片汲取了原作的精華,又充分發揮電影的獨特手段,用實景渲染氣氛,突出了故事情節上的觀賞性,既保留了原舞臺作品的主旨,又挖掘出新的現實意義。導演淘金在《攝制戲曲影片“十五貫”雜記》中說:“電影版《十五貫》的改編遵循了四項原則:第一,必須突出強烈的主題思想;第二,保持人物性格的鮮明;第三,要使故事情節清楚完整;第四,不能削弱舞臺上精彩的表演。”①事實上,搬上電影銀幕后,昆曲《十五貫》基本遵循了導演的幾個原則,其情節結構、主題、人物形象塑造等都沒有大的改變,與舞臺演出保持一致。舞臺版《十五貫》曾經轟動一時,昆曲電影《十五貫》則是戲曲電影的一個較為成功的范例,時至今日,仍為人們津津樂道。從舞臺演出到銀幕呈現的藝術再創造,讓戲曲通過電影藝術的手法,達到了電影化的目的,也讓戲曲觀眾和電影觀眾都得到了美的享受。
一、重戲與重影:從沖突說起
有“重戲還是重影”這個問題的提出,說明戲曲藝術和電影藝術在藝術手法上和審美追求上有著本質的不同。戲曲作為反映生活的一種藝術形式,要求在舞臺有限的空間中,在演出有限的時間里,充分表現戲里人物的生活。戲曲藝術本身是“求真”的,更是“求美”的,梨園界有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這種追求,叫做“不像不是戲,太像不是藝”。因此,戲曲藝術公開表明舞臺的假定性,承認戲就是戲,對舞臺空間和時間的處理采取了超脫的態度,既不追究舞臺空間的利用是否和于生活尺度,亦不追究演出時間是否合乎情節時間的長度,而是依靠分場的結構體制和虛擬的表現手法,在一個沒有什么裝置的舞臺上,創造出獨特的意境,對生活作出了廣泛的形象性概括。戲曲觀眾對這種藝術形式非常熟悉,因此他們去看戲往往也是懷著這樣的審美預期,看演員如何“做戲”做得好。電影藝術所追求的真和美,則是另外一種東西。盡管電影藝術也存在著它的假定性,而這種假定性似乎與戲曲還有暗合之處,比如通過蒙太奇來實現的鏡頭之間的變化和連接,在一定長度的銀幕時間之中,表現電影情節的時間。通過鏡頭的變化,讓銀幕上呈現的東西展現出細節的真實,乃至追求整體的真實性。因此,電影要讓觀眾在普通的二維銀幕上得到真實性的體驗和觀感,它所采取的藝術方法,必然與作為舞臺藝術的戲曲是相互背離的。
昆曲電影《十五貫》中,處處可以看到這樣的矛盾存在,矛盾的主要結果就是戲曲“表演性”的弱化。這種弱化首先體現在戲曲舞臺念白或唱詞的減少。在影片一開頭,我們看到一個精心搭建起來的江南小鎮,導演構筑的是一個完整的電影時空,將時間地點交代得非常清楚。尤葫蘆唱著“離開她家才黃昏,一路行來更已敲”的唱詞,再次點出故事的時間。原本在舞臺上,戲曲的唱詞包含很多指示作用,包括時空關系及人物關系、人物心理等,到了大銀幕上,許多原本必要的臺詞變得不再必要,轉由布景及鏡頭的運用來交代,所以舞臺藝術的“表演性”必然會弱化。細細品味“從黃昏到更敲”的唱詞,不難發現,在舞臺演出中,它為觀眾制造了一個想象的空間,由這種想象甚至能夠生發出獨特的美學體驗,而電影則弱化了這種想象空間,用真實的場景填滿了想象的部分。其次,表演性的弱化也表現在虛擬動作、程式化動作的減少,比如戲曲舞臺上,原本靠虛擬動作或表演程式來完成的敲門、開門、關門、上樓、下樓、行船、走馬、整冠等,借助于電影實景的門、樓梯、橋等,則不需要進行虛擬表演了,如果還要使用舞臺上的那一套虛擬的程式化動作,則與電影的藝術形式格格不入。第三,表演性的弱化,是電影藝術方法的必然結果。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不會讓觀眾隨便觀看場面的任何一個部分,他只把他最想要呈現的東西呈現給觀眾。而這一點,則是舞臺藝術做不到的,舞臺藝術在這樣的框架里,形成了自己的要求,就是每一個在場上的演員身上都必須“有戲”,而且渾身都是戲。一個好的戲曲演員,哪怕在舞臺上沒有動作、沒有唱詞,只是“一戳一站”在舞臺上,也有他的作用。那么戲曲電影在完成戲曲向電影的轉化過程中,舍棄了部分對于電影敘事無用的東西,如蘇戍娟和她父親的對話,為了表現二人的情緒,尤其是襯托蘇戍娟的情緒,為情節做鋪墊,鏡頭每次只給一個人,而且注重面部表情的特寫,通過鏡頭的切換與時間的延展,來完成這樣戲劇性的互動。作為習慣欣賞戲曲的觀眾,由于審美習慣和可能期望看到這一場景的全貌的想法,這也便是演員渾身都是戲的部分原因。
二、戲曲電影:讓沖突逐漸融合的藝術
戲曲藝術是一門綜合藝術,它是詩、樂、舞的融合,電影藝術也是一門綜合藝術,讓兩種綜合藝術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達到和諧統一,就必須找到他們之間的平衡,制造出一種新的形式美,甚至是一種全新的意境。這種形式美應該是介于電影和戲曲之間的,也就是說,二者都必須舍棄一些東西。以唱做為例,我們說“聽”曲、“看”電影,說明戲曲在某種程度上,不是用來看的,而是用來聽的,在劇場里也可以看到大批閉著眼睛單純以“聽”的方式來欣賞戲曲的觀眾。那么當戲曲搬上銀幕,戲曲電影中則不可能完全以“唱曲”為主題,而是要加上戲劇動作來推動電影情節的發展。戲曲唱腔的減少和電影動作的增加,也要達到平衡,讓觀眾不至覺得單調或冗余。如前面所述,在戲曲電影中,戲曲的“表演性”往往已經弱化了,那么推動情節發展,讓電影變得“好看”的部分,一定是電影的手段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從矛盾沖突說起,完全的融合似乎不可能。但是,電影又恰恰是一門包容性很強的藝術形式,可以說,它已經成功地表現了許許多多其他的藝術形式。“一個真正的電影工作者是意味著這樣一個人,他對無論什么樣的題材,即使是非常抽象的、純心靈的或純感情的,都能馬上把它表達出來,而且是卓越地通過電影的鏡頭形象,通過光線和陰影以及在電影畫面中活動的那些形象把它表達出來的。”②基于此,我們認為戲曲電影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成為可能。對戲曲電影來說,從來先有戲曲,后有戲曲電影,作為一個喜歡看戲也喜歡看電影的普通觀眾,我對戲曲電影的審美期待是以戲曲為本位的,也即是我認為,在戲曲電影當中,應該以戲曲的藝術追求為體,電影的藝術手段為用。電影在呈現戲曲藝術的過程中,要充分尊重和利用戲曲的藝術規律,倘若戲曲的藝術規律與電影的藝術手法,在大處有矛盾,導演應當適當照顧戲曲的藝術手法,勿讓觀眾迷失在電影語言本身里。
歸根結底,戲曲電影仍然是以表現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戲曲為根本,否則便不是戲曲藝術片了。那么,在戲曲藝術片中,讓戲與影的沖突達到融合,不妨借助戲曲當中的“節奏”。在傳統戲曲里面,念白有調,動作有式,鑼鼓有經,這些程式化的規定里,無不包含著“節奏”這一重要的因子,如果戲曲電影能夠充分借鑒傳統戲曲本身的這種強烈的節奏性,以戲曲的節奏為依托,讓各個角色之間的唱念圓融、人物動作渾然一體、鑼鼓經連續不斷,也許就能制造出一種嶄新的形式美。細細品味昆曲電影《十五貫》中的念白,那節奏的韻律貫穿始終,讓人回味悠長,導演沒有將他們改變成平鋪直敘的生活語言,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昆曲的藝術特色。這一點是很難做到的,需要戲曲電影導演具有極深厚的戲曲功底,又能夠充分運用電影語言來配合戲曲進行表現。
昆曲電影《十五貫》在戲曲電影的審美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公認的成績,今天看來它仍然不過時,甚至有一些現代性的東西在里面。但是,《十五貫》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如今,戲曲與電影徹底的融合依然很難達到,或許是因為戲曲藝術本身就面臨著現代審美的挑戰,不少圈內人士都認為中國傳統的戲曲藝術不符合現代審美,于是在一出戲搬上銀幕時,又該以怎樣的準則去做,似乎就更難分辨了。傳統戲有傳統戲的追求,現代戲有現代戲的追求,面對這種復雜的局面,我們很難制定出一個統一的規范。而戲曲電影的導演如果不懂戲,用不好電影語言,不但制造不出全新的美感,還有可能做出四不像的作品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要感激像昆曲電影《十五貫》這樣一批優秀的作品。期待戲曲電影在審美的探索中等來下一個春天。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陶金.攝制戲曲影片“十五貫”雜記[J].中國電影雜志.1957,(5):28-32.
②(法)阿杰爾,H.著;徐崇業譯.電影美學概述[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2
[1]浙江省“十五貫”整理小組整理;朱素臣.十五貫[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2]陶金.攝制戲曲影片“十五貫”雜記[J].中國電影雜志.1957,(5):28-32.
[3](法)阿杰爾,H.電影美學概述[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
[4]黃克保.戲曲表演研究[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5]高小健.中國戲曲電影史[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6]高小健.戲曲電影藝術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