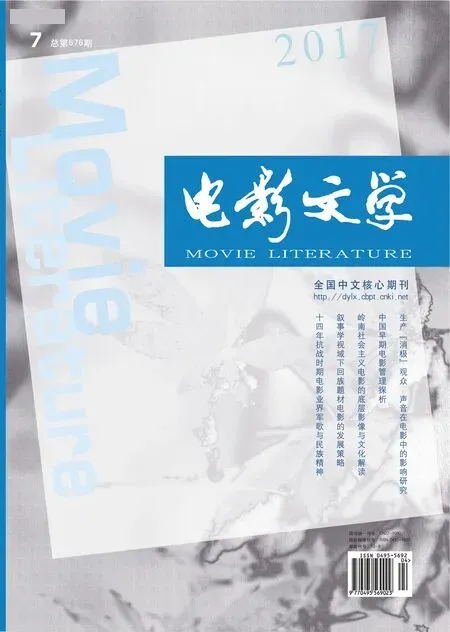論《七月與安生》的電影改編
張靜靜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387)
《七月與安生》是網絡作家安妮寶貝從1998年10月開始在網絡上寫作和發表的一部短篇小說,為安妮寶貝的代表作之一。《七月與安生》收錄于作品集《告別薇安》,于2001年出版并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不僅如此,2011年該部作品改編為話劇搬上了舞臺,2016年9月又改編為電影,成為2016年度國產電影中不可多得的優秀之作,口碑和票房雙豐收,在當下矯情、狗血、無病呻吟、脫離現實而飽受詬病的青春片中獨樹一幟,給諸多套路化的青春故事帶來一股清新之風。
論及影片大獲成功的原因,當然包括諸多因素,如作品《七月與安生》在網絡文學中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清新的影像風格、不一樣的青春故事、演員的出色表演、導演細膩的拍攝風格等,但或許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在于電影劇本的成功改編,相對于原著故事來說,改編提供了一個更豐富、更深刻、更復雜的影視文本。這樣的改編不僅在原作者安妮寶貝那里得到認可,也在諸多原著讀者那里得到一致好評。在當下持續火熱的網絡小說IP改編熱中,改編的電影作品良莠不齊,而讓人驚喜的是,電影《七月與安生》的改編卻獲得了觀眾和業內人士的一致認可。它的成功改編提供了一則我們思考影視改編的成功個案,可以讓我們深入思考以下問題:何種意義上的改編是成功的?影視改編的文本與原著文本之間又呈現出何種復雜的關系?
一、《七月與安生》小說文本的風格
按照通常影視改編所選擇的文本風格來說,安妮寶貝的作品并不適合改編。她從1998年開始創作,其小說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印記,她的文字有著詩化和散文化的風格,簡潔,情緒化,并不以故事取勝,也沒有畫面感很強的文字描寫,個人獨語式的敘述方式,多短句,段落也短,字里行間滲透著一種淡淡的憂傷和孤獨的意味,她的故事多喜歡圍繞著宿命、漂泊等主題寫出游走于當代大都市的年輕人寂寞孤獨的靈魂,凸顯他們靈魂無所歸依的精神世界,整體上有著頹廢、陰暗、抑郁的氛圍,往往給年輕讀者帶來共鳴共情的閱讀效果。一般的電影改編多選擇故事性和畫面感強的小說,這樣的改編相對容易,而安妮寶貝的故事缺乏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矛盾沖突,情緒化的文字給改編帶來更大難度。我們可以從下面節選于小說《七月與安生》中開篇的一段文字中窺斑見豹:
“七月第一次遇見安生的時候,是十三歲的時候。
新生報到會上,一大堆排著隊的陌生同學。是炎熱的秋日午后,明亮的陽光照得人眼睛發花。突然一個女孩轉過臉來對七月說,我們去操場轉轉吧。女孩的微笑很快樂。七月莫名其妙地就跟著她跑了。”[1]
本段文字敘述了故事主人公七月和安生13歲初次相識的場景,這里沒有濃墨重彩的細節描繪,缺乏栩栩如生的畫面感,對話為間接引語式,故事情節并不緊湊,文字偏向內心化與情緒化,這也是作品《七月與安生》通篇的整體風格。但十分可喜的是,這部作品的電影改編能夠克服小說本身不利于改編的風格,順著小說的氣質,善于對原本篇幅較短的小說做加法,將原著中相對簡單的故事情節復雜化,不僅改編后的故事充滿反轉和懸念,而且講述故事的方式頗有創新,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更加豐富,從而使得影片主題內涵的深度得以拓展。
二、《七月與安生》的成功改編
小說中的故事情節相對簡單,七月和安生是一對閨密,故事的講述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的線性發展加以展開。開篇講述了兩人的初次相識,之后兩人慢慢長大,成為一對形影不離的伙伴,但因命運的安排,兩人愛上了同一個男人。作品并未花費太多的筆墨去描寫這二女一男的情感糾葛,接著安生選擇退出,遠走他鄉,家明回到七月身邊,兩人結婚。故事的結局是,安生懷了家明的孩子,回到家鄉,最后因難產死去,七月和家明撫養著安生留下的孩子。可以看出,小說的情節相對簡單,基本上未超出一般言情小說的套路,兩女愛上同一個男人,其中一個退出成全另一人,未婚先孕,難產而死這樣的情節也沒有太多的新意。
電影改寫后的情節則復雜得多,從一個簡單的三角戀故事衍生出更多關于人物命運和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電影大致上保留了小說已有的情節梗概,兩個女孩因為偶然的機緣相識,慢慢長大,愛上同一個男人。影片故事的前半段基本上以小說情節為主進行設置,但影片添加了全新的后半段故事,情節開始反轉,本打算與家明結婚的七月逃婚,放棄安穩的生活,背上行囊,過上了安生曾經的生活,而安生在歷經顛沛流離后,結束看似自由自在的生活,找了一個體貼忠厚的男人結婚而回歸安穩的家庭生活,兩個形影不離的姑娘最終成為對方。不僅如此,影片中故事的關鍵處及最終結局做了改動,原著中的七月對于安生與家明的關系毫不知情,只是臨近故事尾聲才得知真相,而影片中的七月在送別安生時通過安生脖子上掛著的玉牌已知道真相,但一直裝作毫不知情,故事的最終結局更讓小說中的七月代替安生難產而死,安生獨自撫養著七月與家明的孩子。除了添加和改動的故事情節外,影片中故事的講述方式也不落窠臼,添加了七月與安生互寫明信片的部分,用明信片的內容帶出情節,同時打散了原著中的線性時間線索,以回憶的方式穿插著兩位閨密的相識相知,相互嫉妒、傷害又最終和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添加了《七月與安生》的同名小說,安生所寫,署名七月,由這本小說開始進入回憶,串起整個故事的發展,小說描述的情節正好對應著影片的故事情節,影片利用小說故事的講述,巧妙地構造了一個相對規整又有新意的敘事結構。可以說,經過這樣的改編,原著中尋常的青春故事有如脫胎換骨般富有新意,影片的故事節奏緊湊、不拖沓,主人公的成長過渡更加自然,電影中的故事結構更精致,情節發展的矛盾沖突更突出,更能吸引觀眾。
跟原著小說相比,電影對于兩個女孩的性格塑造有了更豐富的呈現,對于兩人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也有更深刻的表現。可以說,經過改編后的情節安排,原本單薄的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間的關系有徹底的升華。電影把瑣碎、偶然的故事通過具體可感的鏡頭語言呈現出諸多細節,從而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突出女主角之間的性格沖突和變化,實在比原著高明很多。從人物形象來看,小說中的七月和安生的性格一直都不變,七月是乖巧和溫柔的,按部就班地上學、高考、上大學,與家明戀愛,畢業之后找份穩定的工作;安生是叛逆和飛揚的,性格孤僻,桀驁不馴,四處漂泊,十六歲離家,從海南到廣州,又從廣州到廈門,她學畫畫,后又到上海做房地產銷售,之后又一路北上,去大興安嶺和漠河,去西安和敦煌,用家明的話說:“安生是個不漂亮的女孩。但是她像一棵散發詭異濃郁芳香的植物,會開出讓人恐懼的迷離花朵。”[1]安生明明知道七月和家明的關系,但卻依然與家明關系曖昧,兩人愛上同一個男人,最后為了七月,安生退出。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相對單薄,七月與安生從故事的開始到結束都一直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性格。但經過影片改編后的故事情節,兩人的性格更豐富,兩人之間的關系也更復雜。從表面上看,七月與安生是不同的人,七月安穩,安生自由,影片前半段基本圍繞著這些性格特點展開,但影片通過情節的添加和反轉使兩人的性格塑造有了更多維度的呈現。影片中七月看似溫柔,但溫柔之下藏著一份城府和自私,雖然知道安生和家明的關系,但一直不戳穿真相,只是裝作毫不知情。兩人之間更復雜的關系隱藏在影片的后半段,一是通過浴室里兩人之間矛盾集中爆發的那一段,兩人彼此指責、妒忌、埋怨,相互戳穿,相互傷害;二是安生看似叛逆,但厭倦漂泊后向往的是七月的安穩,而七月在逃婚后卻踏上了安生曾經的人生軌跡,兩人又互相向往對方。這些改編的最成功之處是更好地表現出兩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她們不僅是閨密,是情敵,也是彼此的影子。尤其在影片的最后,鏡頭回到兩人初次相識砸壞報警器的情形,揭示出真相,七月從來不是我們認為的七月,而安生也不是我們想象的安生。總之,經過改編后,人物的性格不再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情節的發展有了變化,人物性格更加立體飽滿,兩人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凸顯得更集中,更加富有戲劇性。
三、《七月與安生》成功改編的啟示
電影《七月與安生》對于小說的改編是全方位的,盡管保留著原著中的人物關系和部分情節,但故事的最終結局、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節發展都有別于原作。相對于原來篇幅較短的小說文本而言,電影對原著故事情節的改編變動最大。相比較而言,原著的情節相對膚淺和單薄,缺乏戲劇性沖突的張力,不足以支撐一部影片的需求。而電影通過增添和修改原有故事情節的方式,使得原本簡單的情節有了足夠的細節,令人物的性格變化更自然,也更能凸顯人物的復雜性格和關系。可以看出這樣的改編并非符合“忠于原著”的標準,但確實改編后的影片已大大超出原作的藝術水準。
文學與電影依賴于不同的傳播媒介,一個依靠文字,另一個依賴于圖像,但在一個多世紀的電影發展史中,二者之間一直保持著親密無間的關系,諸多電影作品直接來自于對文學作品的改編。長期以來,相當多的業內人士主張判斷改編是否成功的標準在于改編作品是否“忠于原著”,并以此判斷一部電影的優劣。事實上,“忠于原著”只是一個描述性術語,并不是一個評價術語。仔細考察“忠于原著”的改編觀念,發現其背后的理論出發點有以下幾種:一種觀點認同文學相對于電影的優先地位,電影即改編自文學,文學在先,電影在后,改編后的電影應忠實原著,尤其是在涉及經典作品的改編時更加強調要忠實原著;第二種觀點是擔心在圖像化時代,以影視為代表的視覺文化的壟斷和霸權地位導致影視作品對文學作品的吞噬和擠壓,忠實于原著成為制約視覺文化擴張和壟斷的法寶;第三種觀點是對于文學作品過分商業化的胡亂改編憂心忡忡,因此強調原著對于電影改編的制約力量。事實上,文學文本的電影改編是對作品的重新解讀,文學作品注重文學性,電影講究視覺性,改編者會出于藝術和現實條件的考量去選擇哪些因素可以轉換成聲音和影像的媒介,“每一次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不僅意味著一次再創造,而且意味著一次后結構主義意義上的重述”[2]。同時,文學作品承載著復雜的意蘊,并沒有一個統一可行的標準來衡量什么樣的改編是忠于原著的。說到底,任何一種改編都是對原作的重新解讀,改編者的藝術追求、審美趣味、藝術理解力,包括現實條件,都決定、制約著改編后的影片風格,影片改編的成功與否是由多種因素所決定的,并不完全取決于是否忠于原著。
那么,何種意義上的改編是成功的?電影改編是“將其他形式的文藝作品改編成電影劇本的藝術創作過程”[3],作為藝術的不同類別,文學是作家個體藝術才華的結晶,電影是依靠鏡頭影像和蒙太奇的剪輯完成藝術創作,文學作品有文學的評價標準,電影有電影的評價標準。一次成功的電影改編其效果取決于多種因素,包含故事、演員、導演、影像、配樂等。以《七月與安生》為例,通過電影改編之后,故事情節承載的關于悲喜交加的人生命運、人生選擇,相愛又相恨、相互嫉妒又相互成全的姐妹情誼,偽裝與面具下的人性深度等主題有了更深刻的呈現,從而影片的主題也得以超出一般三角戀的言情故事而得以升華。總之,電影改編應超越單純的“是否忠于原著”之爭,從影視藝術自身的特點及影視作品是否深度揭示出人、人性及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標準來衡量,或許這樣才會有更多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改編作品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