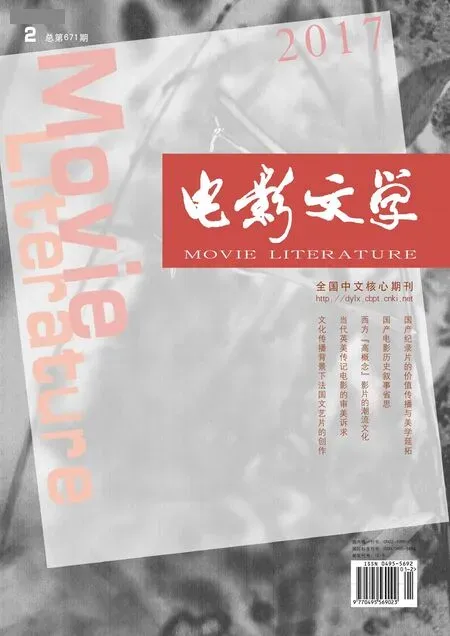霍建起電影的視覺語言分析
唐旭軍
(桂林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在當代電影導演中,霍建起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沉默,低調,韜光養晦,為當代中國影壇貢獻了諸如《那山那人那狗》《暖》等具有多重闡釋空間又別具一格的藝術文本。霍建起電影中常常散發出一股只屬于東方的幽遠和飄逸感,鏡頭渲染出的光影細致、考究、含蓄,猶在畫中,顯出濃郁而真切的中國風味,給本土電影帶進新鮮的風氣和獨特的景象。可以說,其作品中對于視覺語言的把握和掌控,借助視覺語言對“鄉土中國”的講述,具有經典的垂范意義。
霍建起實可稱得上是一位典型的“作者導演”。視覺語言的編制與呈現是其最大的印記。他所有的秘密幾乎都隱藏在視覺語言、光影的編造之中。本文試從技藝、效果、容受三個角度,對其特質做簡單論述。
一、視覺語言的技藝:攝影美學與蒙太奇技術
霍建起的鏡頭語言和畫面呈現,有著別具一格的風范。在他的電影里,攝影機不再只是一個工具,而是和他的視覺世界合為一體不可須臾分離之物。畫面的每一次轉換,鏡頭的每一次運動,影像之中的那些層次復雜的山水、小橋、樹木、矮屋、麥子、河流,乃至人物的一衫一履,都在不斷地改變著景深,給予畫面復雜的空間分隔和縱深,巧妙地規避一般影視因為日常、農村題材限制而帶來的平面感。這是獨屬于霍建起的攝影美學和蒙太奇技藝。
首先,霍建起造就了東方電影攝影美學的新典范。他的電影,攝影機的運動無處不在又無聲無息無影無形,真正的渾然天成、舉重若輕。霍建起的電影畫面,攝影機幾乎完全支撐起了整個畫面的空間構圖,尤其是一些大場面的布景,他樂于也善于運用升降鏡頭拉提至縱深幽長的大遠景,賦予畫面雄厚遼闊的感覺,仿佛是高空航拍的紀錄片布景,又有著其難以企及的情感視覺存注其中,景、物合一,情、韻兼具,展示的是饒具特色的“中國風”,是嫵媚萬千的人文、山水、鄉村情懷,是一望可知的“霍式攝影機美學”。《那山那人那狗》的畫面里,隨著攝影機的移動和鏡頭的處理,如詩如畫、蒼茫溫情的影像緩緩出現:蒼穹之下,彌漫霧氣的晨曦、陡峭的山路、蔓延沒有邊際的群山、清澈緩緩流淌的溪水、層層締結的梯田、處處安詳坐落的湘西民居、茶樹邊上若隱若現的少女……攝影機在制造美景的同時,也在制造情感,醞釀著詩意和溫暖的人間情懷。這是霍建起電影里最常采用的視覺語言方式,即隨著攝影機的移動,掩映之間,設置出明麗而暢順的動感,接著,將鏡頭放置在一個精致的畫面上,仿佛某種超越性的目光在深情凝視,背景、人、物體、虛幻而真切的氣氛,都被安放在各得其宜的位置上,展現出霍建起在電影藝術上所獨具的那種沉穩深情的氣韻和暖意。霍建起依靠其攝影機創造出了其獨有的美學風范和一個溫暖、清新、洗練、厚重的視覺世界,讓觀者沉迷在那個“前現代的中國”氣氛中無法自拔。
其次,霍建起運用出神入化的蒙太奇剪輯技藝,營造出特殊的視覺情緒。他的電影可以明顯地看出主要仰仗視覺的語言支撐整個電影情緒,幾乎完全由攝影機運動、構圖、剪輯來交代推動劇作的發展,而不是像一般導演那樣基本依賴敘述來交代情節。在這樣的視覺語言布置下,霍建起的電影表現出了沉默,在這樣的視覺沉默之中,蘊藏著深沉的情緒。好像《秋之白華》,楊之華在秋意瀟瀟中去探望瞿秋白的住所,畫面清凈白亮,楊之華驚訝地發現該地殘垣斷壁,四處荒草蔓延,中間赫然一座四方小樓。緩步而進,白楊樹上的一只喜鵲歡叫,楊之華凝視少許,突然一聲呼喚,楊差點在臺階上跌倒。這樣的一組鏡頭,氣氛營造上寫意而舒緩,視覺上明暗相宜、動靜得體,節奏感控制得恰到好處,是典型的蒙太奇組合,將鏡頭沉淀為安靜狀態的長鏡頭和硬切的剪輯法,極大地發揮了分鏡的功能,展示出一股溫情、寫意、浪漫、有格調的視覺語言。這是霍建起本身畫家出身、深諳視覺美學的不經意抖露。
二、視覺語言的效果:敘事與隱喻結合的美學境界
作為一種敘事的藝術,電影依靠鏡頭來講述所講是它最基礎的職能,然而,但凡出色的電影,絕不會把其作為唯一的職能來完成。幾乎所有的優秀電影導演都會在敘事的進行之中頑強地追求影像視覺之上的隱喻功用,致力于表現電影的隱喻性和敘事性的交互統一。在霍建起的電影里,視覺語言的完美安排最終也是為了隱喻的完成。攝像操作之中,電影的表意從來不是獨立地取決于一個個孤立沒有靈魂的影像片段,而是取決于影像、視覺之間的關系組成,表達最廣泛、最深切的含蘊。比如,在《暖》里,主角和鄉親們圍坐吃飯飲酒的片段,酒杯被反復地端起,并給予幾個特寫的鏡頭。原本,作為視覺語言而言,一個酒杯僅僅只是表現這個物件的原態,但在霍建起的視覺安排里,酒杯借助蘊含的關系,既可暗示時光的醞釀,也可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指示:無聊、不安與焦慮。在此,霍建起為影像建立起了一套互相指涉的隱喻關系,也傳達出超越記錄之外的美學意義。這在所有霍氏電影作品里,幾乎是標簽一樣的視覺表達存在。
首先,視覺語言向影像語言轉換,實現隱喻功能。任何一部電影的創作,都必然是一個將視覺語言轉換成影像語言的轉換藝術,是建構一整套和視覺語言相互適應的視覺代碼,完成從孤立的視覺表意走向影像表意的視覺和隱喻變異。視覺語言是靜態的、孤立的、能指的、感官的,影像語言是動態的、組合的、所指的、隱喻的。霍建起作為一個學美術出身的導演,尤其注意電影畫面中視覺元素的表意功用。在他的掌控之下,電影的視覺始終在介入劇情之中,在強化視覺語言的前提下完成敘事和向影像語言的轉換,從而實現隱喻功能。《那山那人那狗》就是成功轉換的典范:一路的風景,橋、溪、稻、山,一幕幕的視覺探尋,也在找尋內心風景,透露出別樣的情緒和田園牧歌式的嘆詠;父親過河時小心翼翼地保護郵件不被打濕,一陣風吹來他死命地奔跑追趕,到了村莊有如撫摸寶貝一樣細心整理,諸多視覺畫面傳達出老郵遞員更豐富的形象,而每一次送件員的到來在影像語言的隱喻功能上承載的其實也是閉塞鄉村人的一份希望;兒子走過河流,背起老邁的父親,視覺上突然呈現黃亮的色調,影像語言仿佛在傳達兒子肩負起自己責任的信息;風吹的信件、跟隨父親的追逐,夜里鋪排隔天的信件、村姑探頭出現、放牛娃高歌吶喊等等,都在一晃一動的視覺上昭示著希冀……凡此,皆是影像語言轉換后實現隱喻功能的表征。
其次,視覺語言表意形式的巧妙擇取。在霍建起的電影里,他總是如此地善于擇取和電影之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題材、主題、視覺畫面相適應的影像表意形式,從而使得電影語言和視覺語言一起與它的故事形態、敘事過程、敘事對象組成高度視覺化、純粹化的“電影故事”。《那山那人那狗》是一部以真實的視覺美學和隱喻系統為主旨的影片,出于這樣的意圖設計,電影里幾乎沒有出現特寫的鏡頭安排,敘事的整個過程都是以平行的視點為基準,布置適應的中、近景鏡頭和畫面,與之相適應的是清一色的無技巧化剪輯。直到末尾,當兒子背負著那些信件悠然走向山路之中,他的臉上才出現未曾有過的安詳與甜蜜的神情,眼中迸發出此前未有的志得意滿。同時,銀幕之上伴隨著不曾投射過的特寫鏡頭。這些鏡頭景別的突變是視覺語言的突然轉向,是表意形式的隱喻功能放大。正是霍建起電影在視覺語言表現力度、強度、范圍上的突出特點。
三、視覺語言的容受:信息的傳達與接收
就“讀者反映”批評理論而言,觀者在銀幕前觀看時,是語言、心理、視覺相互交流的過程。電影的觀看,和其他任何的敘事性作品一樣,制作者和接收者是互為前提的。作為電影的制作者,其所要表達的全部主旨和意圖需要寄托于和觀看者共同享有的編碼、解碼機制來溝通、完成、塑造。從這個意義而言,一位優秀的導演,不僅僅是善于借助視覺語言來“講”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善于掌握某種秘訣或媒介來與觀者“共同使用代碼”(艾柯語)的人。霍氏影片的話語形態上不是那種使得觀者始終處于消極閱讀、品味、觀看的“封閉體系”,而是在電影構成的序列上歸屬于“連鎖并置類型”。其作品《那山那人那狗》《秋之白華》《暖》《情人結》,都是這種敘事結構的產物。敘事上的鋪排式、并置式、連帶式的電影語法,使得其影片的觀者始終處在對于故事不斷探尋、聯想、期待之中。可以說,霍建起的影片制作,正是擇取了這樣一種視覺語言的編碼方式來建構自身影片和觀者的交流、溝通機制。其意圖依靠此傳達,觀者所有的感悟也有賴于此而認知。
一方面,霍建起在視覺語言的情境設置上,使得觀者成為置身于黑暗中探尋世界的訪者。探尋的渴望和觸動成為電影觀賞機制的構成要素。如在影片《暖》《情人結》《秋之白華》中,都有著不同形態的探尋情境,即都展現了在現實中被疏離、遮蔽、隔斷起來的情境。特別是《暖》中的林井河,其視覺語言和敘事語序的部署,本身就是探尋者的角色。他實際上成為觀者的化身。從城中回鄉,在路口偶遇過去的初戀情人,已經完全不同往昔的暖,他屢屢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探尋自身、暖、鄉村、社會的變遷。視覺畫面中泥濘的、荒草叢生的小路,古雅安靜的徽式建筑,風中搖曳的黃色蘆葦,幾場絲絲雨景,還有那個如今邋遢、粗魯的瘸子村婦與當初能歌善舞的姑娘的對照,在微雨飄飄的深巷井河和暖的對望,都成為視覺語言制造過程中探尋的路徑和窗口。這是霍建起運用視覺語言的編碼構成對觀者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霍氏電影善于借助視覺語言,編制較強故事性的敘述主線來完成溝通。說到底,電影是一類企圖祛除現實語境和敘事語境的藝術,它唯有不斷地借助視覺語言的編碼來銜接現實和敘事語境之間的橫溝。霍建起的幾部作品,無論其潛藏的文化意蘊、價值隱喻歸屬于何處,就敘事的表層結構而言,都是擇取了故事性強的敘事主題來構建主線。《那山那人那狗》是一個郵遞員在閉塞的山村成長感悟的故事;《秋之白華》是革命年代家國情懷掩蓋下的情感糾葛;《暖》直接講述了男女之間的情愛主題、掙扎沖突,與人性、人情處處壓抑又生機不斷的展現。在霍建起的視覺編碼中,這些矛盾沖突更加凸顯,同時也構成了敘事層層推進的動力。《暖》的開首,林井河騎著自行車載著老師穿過蘆葦,來到浮橋上,偶遇暖的視覺安排中,霍建起給予了畫面非常顯著的特寫:飄揚的蘆葦、緩緩的潺流、暖的衣飾、蹣珊的步履……視覺語言的編碼上也特意凸顯了敘事的強度和對觀者帶來的震撼力。正是這樣的視覺布置,更加親切地、具化地、鮮明地走進觀者的內心,暖、林井河、父親、楊之華這些銀幕上的人物,也永恒地“生活”在一個由視覺語言編碼制造的敘事體系之中。
綜上,就霍建起電影來說,視覺語言的編碼是其最具特色之處。但是,作為一個有浩然雄心、自視甚高的導演,他始終自覺地將視覺語言放置在一個輔助的位置上,而立足于思想內容的表達和深化,巧妙地運用相關視覺技巧,講述一個又一個“過去中國”的故事,試圖重建“文化中國”“鄉土中國”的往昔記憶。品評霍氏電影理應立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