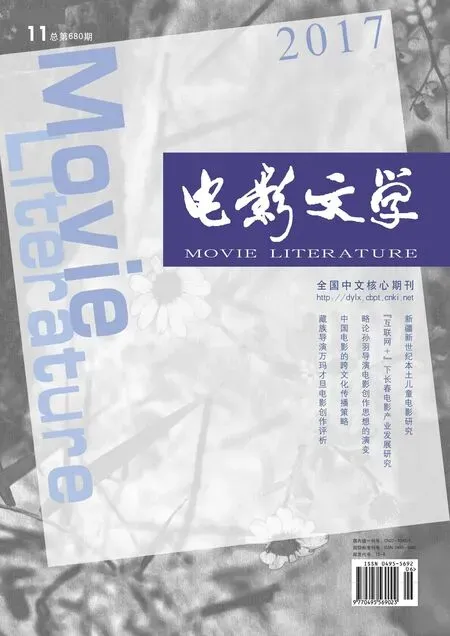論《我的戰爭》悲劇品格的熔鑄
杜 偉 (海南師范大學,海南 海口 571158)
一、流變與堅守:從《團圓》《英雄兒女》到《我的戰爭》
隨著時代的發展,一個國家的戰爭觀念也在不斷變化,2016年拍攝的《我的戰爭》(彭順導演)表達了對志愿軍英雄的深切懷念和崇高敬意,這部影片真實地描述了戰爭的殘酷和戰士的勇敢無畏,是影視界奉獻的“民族記憶”。《我的戰爭》和《英雄兒女》在片首分別注明“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和“取材于巴金小說《團圓》”,但是兩部電影改編和取材的手法迥然不同,一個基本采用原著框架,展示了20世紀60年代樂觀的英雄主義;一個卻只借用了原著的個別情節,更多地關注殘酷戰爭中“人”的情感與生存狀態,展示生命的脆弱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悲劇情懷表現得深切而真實。這種變化顯示著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美學品格的不斷深化與進步。
《團圓》是巴金深入朝鮮戰場采風而創作的中篇小說,1961年發表在《上海文學》雜志上,后來長春電影制片廠把這部小說拍攝為電影,改名為《英雄兒女》。王成堅守陣地、不畏犧牲的精神感動了幾代人,“向我開炮”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電影格調定位于革命樂觀主義,展示了我軍的勇敢和敵軍的怯懦。當王成手持爆破筒沖進敵陣時,敵人竟嚇得目瞪口呆,完全是一副丑角模樣。由于時代的原因,影片不可能去展示戰場的殘酷和志愿軍將士的慘重傷亡。
限于時代原因,《團圓》和《英雄兒女》中都沒有出現愛情故事,但是善于描繪感情的巴金還是給讀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間。有論者認為,小說中王芳與小劉的親密關系“都是在同志之愛的名義下進行的,也并不是小說表現的重心,但它卻在秘密中給兩個年輕人留下了一些感情的空間”[1]。《團圓》的結尾是小劉勇敢炸掉地堡,炸斷雙腿后還希望繼續戰斗。《英雄兒女》則以小劉等戰士勇敢奪取敵人陣地作為“光明的尾巴”,遮蔽了小說中小劉和王芳的親密關系。甚至為了突出中朝友誼的政治目的,把受傷的王芳被小劉從前線背下的情節改為被朝鮮金大爺救回。《我的戰爭》則恢復了《英雄兒女》中被意識形態遮蔽的情感故事,甚至做了更大膽、更感人的處理,結尾的“死亡之吻”只能是當代人思想觀照下的“戰爭”,絕不會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戰場上,但是這種“藝術虛構”既符合感情邏輯,又符合當代的意識形態,壯烈犧牲和情感悲劇博得了觀眾的感動和眼淚,體現了藝術的感染力,也體現了不同時代的審美期待。
對“父女團圓”情節的逆反設計也是《我的戰爭》的創新之處。王文珺在突圍中死去,劉詩文痛哭著將其埋葬,團長默默接過鐵鍬:“她是我女兒!”讓團長的女兒和普通戰士一樣犧牲,實質上是對《團圓》和《英雄兒女》中“父女團圓”俗套情節的一種反撥,既打破了觀眾對老電影的閱讀期待,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又從意識形態上肯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無私磊落。事實上,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就犧牲在朝鮮戰場,團長女兒王文珺的犧牲更能顯示我黨領導的高風亮節和官兵平等的精神。此情節設計具備高度歷史價值與美學意義,也增強了影片的悲劇意蘊。
60年歲月流變,但是《團圓》《英雄兒女》和《我的戰爭》仍然牢牢堅守著勇敢的軍魂和不屈的民族精神。不同的是其美學風格受到所屬時代影響而具有不同表現,從20世紀60年代的昂揚樂觀轉變為沉郁和悲壯,從“革命浪漫主義”轉變為深刻的現實主義,這種轉變標志著對以往戰爭片老套路的超越,影片“以其獨特的美學思考和藝術處理在中國戰爭片史上具有獨特價值”[2],標志著中國戰爭片風格的初步成熟。
二、真實描繪傷亡和恐懼,展示戰爭的嚴酷性
中國以往的戰爭片為了鼓舞士氣,往往對我軍傷亡描寫較少,重點描繪我軍的勝利和英雄事跡,如《英雄兒女》中雖然王成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但是陣地上很少看到戰友的尸體。電影最后的情節是在王成英雄精神的感召下,戰友們奮勇殺敵,我軍大炮怒吼,坦克推進,小劉等沖破敵人的鐵絲網,竟然毫無死亡和中彈發生。真實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由于我軍武器落后,沒有海空軍支援,傷亡慘重,傷亡人數達到36萬,[2]《我的戰爭》就展現了戰爭中我軍的劣勢和大量傷亡的真實狀況,當觀眾還沉浸在第一個場景“車站出發”的歡樂和川話的幽默中時,第二個場景“軍列遇襲”突至而來,面對第一軍事強國的飛機大炮,志愿軍戰士傷亡慘重;“五義亭阻擊戰”中,大斧子剛剛用血肉之軀炸毀了敵人的坦克,敵人的大批坦克馬上從山后鉆出來;“小鎮被圍”一節則描述了美軍的狡猾和狠毒,在倉庫里設置詭雷給九連和文工隊造成大量傷亡。
在描繪傷亡慘重的事實之外,《我的戰爭》還如實描述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及其克服恐懼的過程。對死亡和戰爭的恐懼與厭惡,對生命、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是人類的本性,如果戰爭片一味地表現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而忽視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恐懼與傷害,那么電影就會失去真實性,不能真實表現作為“歷史局中人”的真實情感。我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戰爭片大都有此缺憾,韓國的戰爭片《歡迎來到東莫村》描述了韓國的兩個逃兵出于恐懼逃離部隊,他們在偏僻的東莫村巧遇北韓和美軍飛行員,敵對的士兵在淳樸善良的村民的影響下,恢復了人性,放下武器,對互相殺戮的戰爭進行了反思,他們對和平有著共同的向往,甚至互稱兄弟。為了保護村民不受屠殺,他們主動拿起武器與襲擊的美軍戰斗直至死亡。故事固然是虛構的,但是傳達的情感卻是真實的,每個人都不是天生的英雄,影片對戰爭恐懼的描寫是符合人類真實情感的。
對戰爭恐懼的細節描寫絲毫沒有減弱人們對志愿軍英雄的敬重,而是告訴觀眾一個真實的“人”的戰場感受,更加激發了觀眾的愛國之情。即使是身經百戰的孫北川也是如此熱愛生命,影片中他三次提到老家,提到家鄉的母親。第一次是在“車站相逢”一節,孫北川和孟三夏憑借鄉音認出了彼此是隔一條河的達縣老鄉:“達縣親妹子”。第二次是為救孟三夏排雷時:“不管咱倆哪個以后先回去的話,都記得到對面家里去看一眼。”第三次是孟三夏在奔赴戰場救治傷員時讀孫北川的信:“津貼費,幫我交給我娘,天塌了你都不要忘了。我家住在玉林鄉草梁子村……我家分了八畝好地,在后山根兒……跟你在夢里一塊回家鄉。”小而言之這是對母親和家鄉的愛,大而言之就是孫北川們心中具體的祖國,是他們舍生忘死保衛的神圣之地。戰爭毀滅了一切希望,主人公雖然不懼犧牲,但對母親、愛人和家鄉的思念多次出現,使得觀眾與主人公產生情感共鳴,實質是譴責戰爭、渴望和平的潛意識的曲折表達,同時也為志愿軍參戰維護和平的正義性做了最好的注解。
三、熔鑄悲劇品格,展示民族精神
從電影發展史上看,電影悲劇品格的形成標志著一個國家電影文化的成熟。戰爭電影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的《大決戰》系列電影場面宏大但旨在顯示領導人的運籌帷幄,對戰爭的悲劇性表現不夠。2007年首映的《集結號》(馮小剛導演)可以說是新世紀戰爭電影中悲劇品格的代表作。《我的戰爭》繼承了這種悲劇的風格,表現了殘酷的戰爭對于生命、幸福等美好事物的毀滅和傷害。有學者認為:“影片雖是戰爭片的形態,但卻選取了一個愛情片的架構,這是敘事層面出現的一個重大錯位。”[3]其實這是對電影抒情主體的一種誤解,《我的戰爭》并非特定一個人的戰爭,而是一代人的戰爭,所以展示的是一個群體的美好情感被戰爭毀滅的悲劇故事。影片中遭到毀滅的不僅有愛情(孫北川與孟三夏、劉詩文與王文珺),還有父子之情(老爹與小神仙)、父女之情(王政委與王文珺)、戰友之情等。作為富有“青春熱情”的作家,巴金在《團圓》中雖然沒有像《洼地上的戰役》那樣描寫感人的愛情,但也描寫了深蘊的父女之情、戰友之情,甚至寫出了朦朧的愛情,主人公是王芳和王文清。《英雄兒女》立足英雄敘事,“將國家倫理作為唯一的真理,建構起意義的單一性和純粹性”[4],取消了小劉與王芳可能的愛情故事。《我的戰爭》則大膽演繹了被戰爭毀滅的愛情故事,在悲劇中實現了個人情感和國家立場的完美結合。
朱光潛先生認為:“一部偉大的悲劇不僅需要表現巨大的痛苦,還必須表現對災難的反抗。沒有對災難的反抗,也就沒有悲劇。引起我們快感的不是宿命的災難,而是反抗,命運可以摧毀偉大崇高的人,但卻無法摧毀人在反抗中所表現出來的偉大崇高。”[5]有論者把中國傳統的悲劇精神總結為這樣幾句話,即“邪惡勢力可以碾碎我們的骨頭,但決不能壓彎我們的脊梁。身軀倒下了,靈魂仍然要戰斗”[6]。可以說,武器裝備落后的志愿軍戰士擊敗當時最強大的美軍確實是一個奇跡,《我的戰爭》中的孫北川身經百戰,當然明白對手的強大,甚至預感到自己犧牲的命運,但是他們奮起反抗,“我們是為了勝利而來!”影片贊美了這種敢于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也真實地描寫了我軍的巨大傷亡狀況——這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構成一幅戰爭史的真實畫卷,志愿軍處于劣勢,但有保家衛國的無畏精神,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更有舍生取義的悲劇情懷——一個抗爭不已的民族,終于取得勝利,也熔鑄出不屈的國魂和軍魂。
托爾斯泰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有一個經典情節——安德烈在奧斯特里茨戰場受傷后仰望藍天追問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的戰爭》也借此設計了“仰望藍天”或曰“犧牲前的追問”的場景。在攻擊537高地取得最終勝利時,孫北川深受重傷,他和張洛東躺在戰場上緊緊偎依,望著藍天白云和飄散的硝煙,“你說,我們今天做的事情,以后會不會有人記得?”這個“臨終提問”的悲劇意義是跨越影片、跨越時代的,實質是對當代社會和觀眾的一種考問,志愿軍英雄用生命換取的勝利在很多年后竟然遭到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無端質疑。[7]電影最后的獻詞是“謹以此片獻給為共和國英勇獻身的前輩們!”忘記了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此部電影喚醒了一個民族關于英雄的記憶,也是對遺忘和質疑英雄的“逆流”的一種嚴正回答和有力抨擊。
魯迅先生認為“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戰爭毀滅了人類的幸福和生命,所以從本質上看,悲劇和戰爭是一致的,對于人類來說,戰爭永遠都是悲劇。《我的戰爭》如實展示了志愿軍的傷亡,展示了人們對戰爭的恐懼。正因為真實,電影中悲壯的情節才可信。電影超越了以往戰爭影片“假大空”的俗套,立足民族特色,用豐富的手法拍攝出富于悲劇品格的戰爭故事,展示了不屈的軍魂和國魂,踐行了“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8]的藝術宗旨,堪稱我國當代戰爭片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