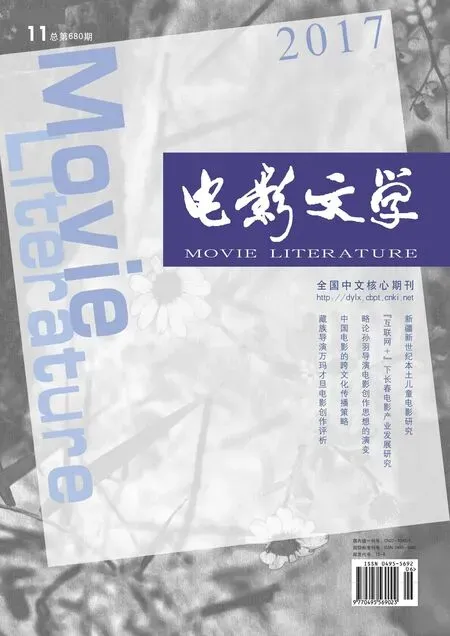小說《寵兒》改編電影的文化隱喻
房麗穎 (河北傳媒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1998年由喬納森·戴姆執導的好萊塢影片《寵兒》用影像的方式為現代觀眾講述了美國蓄奴制時期,黑人女奴賽絲為保護女兒不再遭受奴隸主的玷污和摧殘,被迫殘忍地殺死親生女兒后,在痛苦深淵中日復一日忍受著回憶和鬼魂的折磨,最終在小女兒丹芙與黑人社區的幫助下走出生活陰影的故事。作為由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同名小說的改編電影,影片《寵兒》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人物、情節和主題,同時還采用隱喻性表述,以抽象的敘事為這部哥特式故事增加了更多的負重感,同時也為現代觀眾認識美國血腥的歷史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因此,本文通過對影片中奴隸制、女性意識及民族文化等內容的隱喻性表述的分析,探究影片《寵兒》深刻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魅力。
一、跳躍時空隱喻奴隸制的黑暗殘酷
作為后現代小說改編的電影作品,《寵兒》打破了傳統敘事時空線性規律,而是讓販奴船、藍石街124號等不同時空跳躍穿插于故事情節中,不僅有助于觀眾全面了解故事情節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賦予了時空情景更多的隱喻作用,讓觀眾認識到美國奴隸制度的陰魂不散及黑人生活狀況的悲慘,對于揭示影片主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例如,影片中不斷跳躍出現的非洲販奴船,既讓讀者了解主人公等黑人的身世,也成為黑人集體慘痛記憶的空間隱喻。影片《寵兒》作為一部飽含沉重歷史的電影,導演喬納森·戴姆將鏡頭延伸至遙遠殘忍的奴隸貿易和黑人作為奴隸制度犧牲品的歷史事實,讓賽絲等主人公成為六千萬死去黑奴的代表。影片中黑人主人公賽絲作為販奴船幸存的黑奴,見證了黑奴在大西洋的悲慘經歷。販奴船狹窄骯臟的夾板、船艙、死尸堆等空間意象在電影中時不時出現在賽絲和寵兒的記憶中,不僅讓主人公不斷遭受創傷記憶的侵蝕,引發觀眾對黑人的同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影像化的方式揭開了美國奴隸制度血腥的面紗,為現代觀眾更為清晰地認識奴隸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可以說販奴船這一跳躍的空間已經成為黑奴集體記憶重要的空間表征。
除此之外,電影中“甜蜜之家”的空間影像作為賽絲個體的創傷記憶空間也以跳躍的方式在影片中不斷閃現,成為揭露奴隸制度殘酷的重要意象。影片中“甜蜜之家”作為奴隸主安排給主人公賽絲的家,雖然號稱“甜蜜”,但無論賽絲、黑爾、薩格斯還是保羅、西克索,在這個所謂的“甜蜜之家”生活得都不幸福,甚至在日后,很多主人公回憶起此地的生活時仍然心有余悸。導演在影片中采用極具后現代風格的重復空間敘事,巧妙地讓這一場景呈現在賽絲等人物的腦海中,尤其是賽絲出逃之前在學校被白人搶去奶水并遭遇毒打的情節,在電影中前后跳躍出現十余次。電影用這種違背敘事習慣的空間跳躍凸顯了美國奴隸制度違背人倫等殘忍行為,同時為奴隸制的社會環境冠以“甜蜜之家”的諷刺性名稱,隱喻了美國奴隸制的虛偽,也增加了影片的反諷效果,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作品的內涵深度和批判意識。
除了販奴船和“甜蜜之家”外,導演在影片中還經常將“藍石街124號”這一主要的場景跳躍地浮現在賽絲的回憶中,隱喻奴隸制的陰魂不散和弒嬰案發生的必然性,對美國奴隸制度的批判達到最高潮。電影中賽絲出逃后和薩格斯租住在藍石街124號,但是她們僅在此地過了28天的自由幸福生活。為防止女兒繼續淪為奴隸制的犧牲品,賽絲在藍石街用極端手段將女兒殺死。電影在構建這個悲劇故事時,讓觀眾隨著空間的不斷跳躍參與到故事建構中,用不同的時空記憶隱喻奴隸制度的頑固和危害性,同時喚起觀眾對黑奴的同情。同時在影片中,因為藍石街124號空間不斷浮現在諸多人物的腦海中,讓主人公賽絲不僅受到白人的歧視,更受到黑人同胞及愛人的嫌棄,此時124號成為賽絲的心魔,同時也影響到賽絲女兒丹芙的成長,讓她和母親一樣封閉在恐懼和自卑中,成為創傷記憶的囚徒,更成為美國奴隸制度的犧牲品。總之,《寵兒》一片中,跳躍的空間意象既承擔了回憶敘事的功能,同時也具有隱喻作用,導演通過販奴船、“甜蜜之家”及藍石街124號的空間切換,既讓影片呈現出后現代空間化敘事效果,同時將空間和黑奴生活、對奴隸制度的批判結合在一起,以空間變化凸顯黑奴的悲慘,讓觀眾對黑人的命運產生更多的憂患意識。
二、不同命運隱喻黑人女性意識覺醒過程的艱辛
電影《寵兒》中導演將拍攝視角集中在祖母、賽絲和孫女三代美國黑人女性人生命運和悲慘經歷上,以三代人不同的命運漸進式地隱喻奴隸制度下黑人女性意識覺醒雖然艱辛,但是一直在成長的歷程。
首先,作為第一代黑人女奴,薩格斯在影片中雖然有關為奴數十年的經歷,但是導演卻沒有賦予她絲毫主體意識,乃至于薩格斯也認為自己走起路來像三條腿的狗。薩格斯為奴60年雖然生下了8個子女,但是當她的子女被賣掉或繼續當奴隸時,薩格斯沒有表現出憤怒,而是默默地接受了白人主人的安排。導演在薩格斯生活中穿插入非常多的痛苦回憶,如被販賣、毒打,這種重復性的創傷記憶讓薩格斯不敢,甚至不想去反抗,成為缺乏價值感和歸屬感女性的典型代表。當薩格斯在兒子的幫助下重獲自由之后,已經習慣被奴役的薩格斯居然被眼前自由的生活震驚了,甚至不習慣自由地呼吸和說話。然而此時電影卻沒有讓其自我意識得到發展,反而讓她再一次見證了黑人奴隸制逼迫賽絲將孫女殺死的悲劇及周圍男性的冷漠,而這種殘酷的情節則再一次將她打入被奴役的深淵,剛萌芽的自我意識及價值觀被徹底摧毀。可以說,導演喬納森·戴姆用薩格斯無法逃避的命運,既隱喻了奴隸制對黑人女性生理和精神的摧殘,同時也隱喻了黑人女性意識的完全喪失。相較于薩格斯主體意識的喪失,主人公賽絲在電影中顯然具有更為強烈的反抗意識。但是由于對奴隸制過于恐懼,賽絲身上的女性意識及女性反抗精神仍然是無意識和被動的,同時也是極端的。相較于原著,主人公賽絲無論在形象上還是性格上都更接近現代女性。為避免孩子受到奴役,她寧可不依靠男性只身逃走,母愛和對自由的渴望讓其女性意識超越了薩格斯。但是電影仍然遵循原著,讓賽絲無奈之下選擇殺死女兒,用極端的方式為女兒爭取自由。電影用賽絲這種極端的反抗,隱喻第二代黑人女性的覺醒,賽絲也成為一心保護家庭及尋求自由身份女性的典型代表,然而極端的弒嬰行為同時也隱喻其女性意識是被動的,她所追求的不過是自己的獨立,這種女性意識仍然較為樸素,具有局限性。最終賽絲也只能掙扎在痛苦的深淵中,并沒有真正實現自己的夢想。與薩格斯喪失自我意識、賽絲被動無意識追求主體身份相比,電影則賦予第三代黑奴丹芙更為現代的女性主體意識。電影中,丹芙主要通過主動的自我追尋,成功地擺脫種族歧視的歷史陰霾,甚至成為當代自強獨立女性中的一員。導演喬納森·戴姆沒有讓丹芙遭受奴役壓迫,但是卻采用哥特式情節改編,讓丹芙與鬼魂寵兒形成跨時空交流,并逐漸形成對奴隸制度的批判意識,在思想上走向成熟。導演在丹芙身上注入了更多現代女性的思想元素,讓其更加獨立,不再像其祖母和媽媽一樣依賴男性。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具備了更多的獨立意識。電影用丹芙隱喻女性完全可以尋求屬于自己的身份,實現性別、種族、家庭的平等。同時,電影中丹芙也逐漸認識到黑人身份和黑人社區的關系,并充分利用黑人社區幫助母親擺脫寵兒鬼魂的糾纏,和母親一起實現了真正的自由。導演在電影中由三代女性的不同命運及選擇隱喻女性意識覺醒過程的艱辛,同時這種遞進式的女性意識構建歷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為現代觀眾帶來不同的心理沖擊,引導觀眾對不同時代的女性及女性遭遇形成客觀的認識,有助于觀眾女性主體意識的發展。
三、非洲意象元素隱喻對黑人民族文化的尋根之旅
《寵兒》受到原著作者非洲文化的影響,在故事中存在大量具有典型的非洲文化的影子,導演喬納森·戴姆在影片中沒有將這些非洲元素予以完全刪除,而是將好萊塢電影元素與非洲意象結合在一起,以大量非洲元素引導觀眾展開民族文化的尋根之旅。
電影《寵兒》雖然是好萊塢電影,但是借鑒了非洲文化中樸素的自然觀,賦予某些自然元素強大而神秘的力量,與黑人民族文化形成了天然的契合,象征著電影導演及黑人對民族文化的憧憬。例如,非洲神話中“水”這一令人崇敬的自然元素,在影片中被賦予一定的神秘力量,尤其在鬼魂寵兒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影片中鬼魂寵兒無論是首次出現還是最后消失,都與一條神秘的河流相關,而這種生于水、歸于水的故事情節,讓電影極具隱喻意味,象征著源于非洲民族文化的黑人,最終也必將尋回民族文化之根。電影還賦予俄亥俄河神秘的力量,只要奴隸越過該河就能獲得自由,這種哥特式的故事既讓電影充滿神秘色彩,同時也與非洲民族文化強烈的自然觀形成聯系,讓觀眾形成對民族文化的興趣。影片中丹芙生在俄亥俄河中,因此也具有非洲黑人傳統文化河水的神秘力量,可感知鬼神并與之交流。除了河流意象之外,電影還對非洲文化中代表神秘力量的植物進行了充分的利用,讓樹木、花朵等自然元素成為象征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引發觀眾對黑人民族文化的希冀。電影中導演讓植物成為黑人心靈慰藉及忍辱負重生存的力量來源,植物在很多情節中扮演著上帝的角色,引導主人公由毀滅實現再生。如保羅出逃時,詢問當地的土著居民怎么才能到達自由的北方,土著居民告訴保羅沿著花朵走就能到達其理想的終點。結果在花朵的指引下,保羅成功地逃脫奴隸制的統治,與賽絲團聚。同樣,賽絲背后樹形傷疤、丹芙的樹屋都與非洲文化傳統形成了天然的聯系,并讓主人公從這些非洲文化元素中獲得力量和安慰。電影采用這些非洲意象一定程度上讓觀眾不再局限在白人文化思維中,而是主動地對民族文化根源進行探索追尋。
除此之外,電影《寵兒》將原著故事進行了一定的精簡,但是仍然集中講述了寵兒借尸還魂回到人間的故事,這種極具非洲傳統神話色彩的故事內容與白人崇拜理性科學的主流文化形成了強烈的撞擊。電影打破了生和死、人和鬼的時空界限,采用碎片化的敘事將死者和生者置于同一敘事情節中,尤其是祖母薩格斯雖然1873年就已經去世,但是在影片中卻和主人公賽絲經常進行語言和感情交流,這種哥特式的表現手法也具有典型的非洲文化特點,與非洲文化傳統形成了直接的聯系。總之,電影《寵兒》通過對非洲文化元素的大量運用,不僅滿足了現代觀眾對傳統文化的渴求,而且隱喻了黑人民族文化的存在及黑人民族文化對黑人主體意識、文化身份的作用。
四、結 語
總之,1998年版電影《寵兒》因為受到原作者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民族屬性的影響,蘊含強烈的反種族壓迫意識、女性主體意識及黑人民族文化意識。但是,在藝術表現上導演喬納森·戴姆并沒有對美國奴隸制度進行直接性批判,而是采用隱喻性創作手段對故事主體進行深化。影片通過文化隱喻體系,對影片主題進行了多層次的闡述,為觀眾提供了更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間,對于提升影片的藝術性和感染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