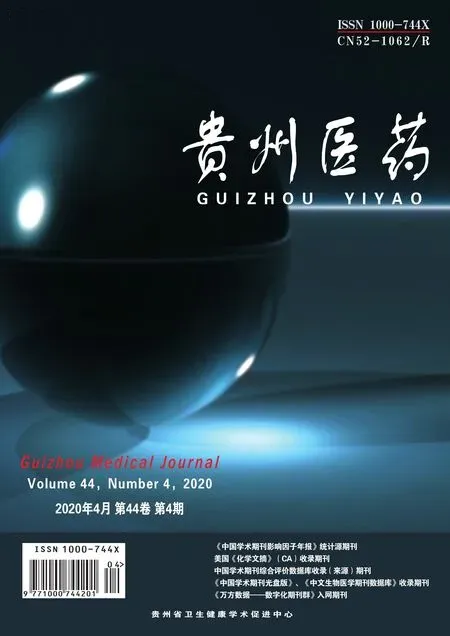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的療效分析及對免疫功能的影響
李彬 蔣新平 徐強 龔莉萍 楊玉臣
(上海市黃浦區(qū)香山中醫(yī)醫(yī)院推拿科 ,上海 200020)
支氣管哮喘是臨床常見的呼吸內(nèi)科疾病,是一種以慢性氣道炎癥為主要特征的疾病,多始發(fā)于4~5歲以前,具有發(fā)病率高、病程長等特點,臨床伴有氣促、喘息、咳嗽等癥狀,患兒呼吸道病癥強度和癥狀是隨著時間而變化[1]。近年來,中醫(yī)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已被廣泛運用于臨床,本文旨在探討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的療效分析,并觀察其對免疫功能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我院收治的支氣管哮喘患兒80例,隨機分為觀察組(n=41)和對照組(n=39)。觀察組男21例,女20例;年齡6~13歲,平均(9.25±3.14)歲;病程2~18月,平均(8.59±3.63)月。對照組男23例,女16例;年齡6~14歲,平均(9.21±3.12)歲;病程 3~19月,平均(8.61±3.59)月。納入標準:符合《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2]中的診斷標準;無其他嚴重疾病;無藥物過敏史;監(jiān)護人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嚴重肺部疾病者;對本次治療藥物過敏者;免疫功能異常者;患有感染疾病。兩組患兒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對照組給予刺絡治療:四縫、少商、耳尖進行針刺放血,使用毫針針刺,點狀出血即可,1周 1 次。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給予推拿療法:以清肺經(jīng)、補腎經(jīng)、清天河水、揉太陽穴、推坎宮、開天門、揉膻中穴、揉上俞穴、揉乳旁穴、揉乳根穴、按揉肺俞穴、按揉天突穴、按揉定喘穴進行按揉,每次15 min。兩組均治療3月。
1.3觀察指標 采集治療前、治療3個月后肘靜脈血4 mL,3 500 r·min-1離心10 min,提取血清,送檢IgG、IgA、IgM;肺功能采用流量傳感儀測定FEV1、FVC、PEF水平;中醫(yī)癥候積分:喘息、哮鳴音主證采取 0、3、6、9 計分方法,胸悶、咳嗽等次證采取 0、2、4、6 計分方法, 0 分表示無癥狀, 9 分或 6 分表示癥狀嚴重。 療效評定標準:顯效:中醫(yī)癥候積分減少95%;有效:中醫(yī)癥候積分減70~89%;無效:未見好轉(zhuǎn)或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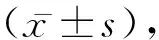
2 結(jié) 果
2.1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臨床療效顯效21例、有效16例、無效4例,總有效率為90.24%;對照組臨床療效顯效14例、有效13例、無效12例,總有效率為69.23%。觀察組臨床療效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
2.2兩組免疫功能比較 治療后,兩組免疫功能水平均得到顯著改善,且觀察組IgG、IgA、IgM水平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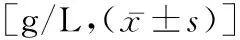
表1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免疫功能比較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比較,#P<0.05。
2.3兩組肺功能比較 治療后,兩組肺功能水平均得到顯著改善,且觀察組FVC、FEV1、PEF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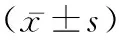
表2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肺功能比較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 ;與對照組比較,#P<0.05。
2.4兩組中醫(yī)癥候積分比較 治療后,兩組中醫(yī)癥候積分均得到顯著改善,且觀察組喘息、咳嗽、胸悶及哮鳴音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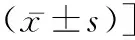
表3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中醫(yī)癥候積分比較[分,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 ;與對照組比較,#P<0.05。
2.5兩組哮喘發(fā)作、呼吸道感染比較 治療后,兩組哮喘發(fā)作、呼吸道感染均得到顯著改善,且觀察組哮喘發(fā)作、呼吸道感染次數(shù)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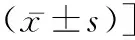
表4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哮喘發(fā)作、呼吸道感染次數(shù)比較[次,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 ;與對照組比較,#P<0.05。
3 討 論
小兒支氣管哮喘目前臨床治療主要以緩解癥狀和控制炎癥為主[3]。中醫(yī)認為小兒機體柔弱,氣血未盛,哮喘反復發(fā)作,肺氣耗散,痰熱耗灼肺腎之陰,故在緩解期可出現(xiàn)肺脾腎虛象;一旦大發(fā)作又表現(xiàn)為腎陽虛寒,或腎不納氣,因此治則以扶正為主[4]。刺絡放血可改變經(jīng)絡中氣血虛實狀態(tài),從而調(diào)整臟腑氣血陰陽的作用,針刺少商放血可祛肺經(jīng)之邪,刺絡放血療法可達肺、脾、腎同治[5]。但是其單一治療效果并不顯著,且對患兒免疫功能影響不大,故較多學者提出在此基礎上聯(lián)合治療,以提高臨床療效。小兒推拿法是中醫(yī)外治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根據(jù)患兒的情況選取穴位,以推、捏、揉等手法治療,具有補益肺氣、脾氣和腎氣,從而疏通經(jīng)絡、化痰定喘功效,最終可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6]。本文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患兒總有效率明顯對照組,提示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可提高小兒支氣管哮喘患兒的臨床療效。
研究[7]顯示,支氣管哮喘患兒多處于免疫功能紊亂的狀態(tài),因此增強患兒淋巴細胞的增殖功能,調(diào)節(jié)免疫應答,是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的重要途徑之一。IgG、IgA、IgM是免疫功能常用指標,IgG是血清主要的抗體成分,是唯一可以通過胎盤的免疫球蛋白,在機體免疫中其保護作用;IgA具有多種抗體活性,同時具有抗菌、抗毒、抗病毒作用;IgM是人的免疫球蛋白之一,血清中檢出IgM 提示新近發(fā)生感染,可用于感染的早期診斷[8]。本文結(jié)果顯示,觀察組患兒IgG、IgA、IgM高于對照組,提示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可改善小兒支氣管哮喘患兒的免疫功能。分析其原因是因為小兒支氣管哮喘的發(fā)生于機體免疫功能紊亂有關,而推拿療法則可激發(fā)患兒臟腑經(jīng)絡之氣血,促進周身氣血運行,進而調(diào)節(jié)機體免疫功能。本文結(jié)果還顯示,觀察組患兒的FVC、FEV1、PEF高于對照組,提示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可改善患兒的肺功能狀態(tài)。董昇等[9]研究也認為,推拿療法能通過對患兒夾脊穴和腎俞穴進行捏脊刺激,具有調(diào)和陰陽、健脾理肺之功效,從而改善患兒的肺功能。此外,本文結(jié)果還顯示,觀察組患兒喘息、咳嗽、胸悶及哮鳴音評分、哮喘發(fā)作、呼吸道感染次數(shù)均低于對照組,提示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可改善小兒支氣管哮喘患兒的中醫(yī)癥候積分,降低哮喘及呼吸道感染次數(shù)。由此說明推拿療法聯(lián)合刺絡治療小兒支氣管哮喘效果顯著,可有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