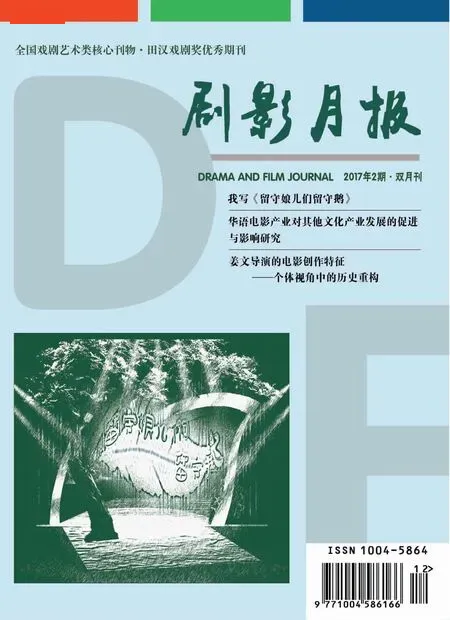黑奴制罪惡的揭露和控訴
——電影《為奴十二年》淺析
■陳海強
黑奴制罪惡的揭露和控訴
——電影《為奴十二年》淺析
■陳海強
《為奴十二年》是第一部直面美國南方黑奴苦難的電影。該片通過一個個震驚到令人發(fā)指的細節(jié)來對黑奴的苦難進行描寫。該片的成功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開,在藝術(shù)上同樣精雕細刻,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細節(jié)飽滿富有震撼力;人物語言富有音樂感;注重運用象征手法。
黑奴苦難 細節(jié) 音樂感 象征
《為奴十二年》是一部由英國非裔導演史蒂夫·麥奎因拍攝的美國電影,實際上這應算是一部合拍片,因為它的制作人員來自多個國家,講述的是一個帶有地方色彩的故事——美國黑奴制下黑奴的非人生活。要是較真的算起來,這是第一部直面美國南方黑奴苦難的電影。昆丁導演的《被解放的姜戈》雖然也講述了黑奴制的罪惡,但黑奴制的罪惡只被籠而統(tǒng)之地敘述了一番,甚至還是以一種不那么嚴肅的“娛樂”方式講述著。本片獲2014年第86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女配角獎;2014年第67屆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shù)學院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獎。這是和本片在思想和藝術(shù)上的卓絕表現(xiàn)密不可分的。
影片故事發(fā)生于1841年,為美國廢除黑奴制度的前幾年。所羅門·諾瑟普是個黑人小提琴手,他是紐約州的自由民。在豐厚報酬的誘惑下,他決定隨兩位樂師前往華盛頓表演,結(jié)果被賣往南方成為黑奴。成為黑奴后的苦難生活,多次逼使他決計逃走,但總是功虧一簣。他的第一個主人叫威廉·福特,秉性忠厚善良,但他手下的工頭約翰·提畢茲是個歧視黑人的惡棍,他們總是矛盾不斷。于是他被賣到第二個主人埃德溫·艾普斯那里,這是個反復無常的嚴厲的農(nóng)莊主,凡是完不成任務的黑奴每天都要遭到鞭刑,他手下有個女黑奴帕特西拼命工作,每天都能超額完成任務,她受到埃德溫·艾普斯的器重和迷戀。敏感的艾普斯夫人發(fā)現(xiàn)了此事,處處找帕特西麻煩,帕特西的生活更加艱難。所羅門·諾瑟普遇到一個正直善良的白人,向他傾述了自己的遭遇。在他幫助下,終于重獲自由。然而,十二年過去了。
黑人形象向來在美國電影中被不真實地敘述著,被稱為標志著世界電影由供人玩耍的科技游戲成長為一門獨立藝術(shù)的劃時代的作品——《一個國家的誕生》,被譽為“用光書寫出來的歷史巨著”,“這是一部種族主義色彩非常濃厚的影片,從它上映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美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響,在一些城市甚至引起騷亂。”[1]“這部影片也在美國電影傳統(tǒng)中樹立起一個很壞的模式:黑人在好萊塢電影中要么野蠻殘忍,要么逆來順受。”[2]而在好萊塢第一巨片《亂世佳人》中,黑人在奴隸制下的苦難同樣不見蹤影。“觀眾從銀幕上看不到一點白人奴隸主和黑奴之間的矛盾,相反地卻在戰(zhàn)爭的災難中相依為命,同舟共濟。”[3]斯皮爾伯格的第一部嚴肅作品,即表現(xiàn)黑人題材的《紫色》,在獲得11項奧斯卡提名的盛況下,最終居然一無所獲顆粒無收。這恐怕再一次證明了好萊塢乃至美國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現(xiàn)象確實存在。《為奴十二年》撥開云霧,還歷史以真相,還黑人以真面目。
《為奴十二年》是一部直白、有力、雄渾、憤怒的作品。透過影片,我們能感受到導演對于他的同胞曾經(jīng)遭遇苦難的悲憫,對于黑奴制的憤怒。他是通過一個個震驚到令人發(fā)指的細節(jié)來對黑奴的苦難進行描寫。黑奴所遭遇的苦難可以分兩個層次來敘說。第一層是無休止的工作和肉體的摧殘。黑奴們毫無自由可言,他們每天被規(guī)定了工作的內(nèi)容和數(shù)量。達不到目標者,等待他們的是皮鞭。工作稍有懈怠,皮鞭就從后面過來了。他們的食物每頓只有一點點,住的是木板屋。主人們一不高興,可以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他們。他們只是主人的“私人財產(chǎn)”。他們不再是人,如同牲口般被對待。第二層是他們?nèi)缤唐匪频谋豢醋觥拔铩薄T诤谂灰资袌觯麄儽粍児庖路邮苜I主的挑選,被當做“物”出售。洗澡的時候,他們不管男女,皆在一處,人的尊嚴消失殆盡。總之,在黑奴制度下,黑人只是一些干活的牲口。可以說,導演是有意選取了各種代表黑奴制罪惡的細節(jié)來使我們感性的去感受黑奴的苦難,它使觀眾震驚,使觀眾憤怒。觀眾自然而然得出結(jié)論,這種罪惡的制度該遭天譴,早該廢除了。導演更在影片中塑造了一個正義的白人形象巴斯對此進行直接的譴責:“奴隸制毫無公平和正義可言。法律也未必都是對的。假設他們頒布新法,剝奪你的自由,讓你變成奴隸。你怎么看?法律會變,但普世真理是不變的。有一個事實,簡單明了,只要是真理,就對所有人適用。不論是白是黑,在上帝眼里是一樣的。”
該片的成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高爾基說,“文學是人學”。作為敘事藝術(shù)的電影同樣也是以人為中心的。“比較起來,人物是劇作構(gòu)成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尤其在現(xiàn)代影視創(chuàng)作中,事件的選擇、安排大多是為了實現(xiàn)人物刻畫的目的的。”[4]所羅門·諾瑟普是個優(yōu)秀的黑人形象。他是個小提琴手,他懂河道的工程設計,不同于一般的黑人,他還會閱讀寫文章,更是相貌堂堂,風度翩翩。這樣一個幾近完美的人橫遭這一慘禍,不能不使人倍加同情。魯迅曾經(jīng)說過,悲劇就是美的毀滅。毫無疑問,所羅門·諾瑟普就是一個美的形象,他本該做出不凡的成就,過上幸福的生活。然而,黑奴制把他毀了,生生奪走了他十二年的時光。在他本該釋放生命華彩的年紀,卻終日在皮鞭下茍延殘喘。亞里士多德說,悲劇引起人們憐憫和恐懼。我們憐憫于諾瑟普的不幸,恐懼于他的苦難。人物的形象和演員的外形也是密切相關的。出演所羅門·諾瑟普的是來自英國皇家劇院的戲劇演員切瓦特·艾加福特。導演曾說:“我理想中的人選,要儒雅有禮,充滿人性魅力,即使在某些極端的環(huán)境下備受煎熬,他也必須要在痛苦的掙扎中探尋自己的底線,具有這種特質(zhì)和表演張力的,非切瓦特·埃加福特莫屬。”切瓦特·艾加福特出色完成了這一任務。憑借此片精湛的表演他獲得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shù)學院獎最佳表演獎。
威廉·福特是個“相對善良”的黑奴主。他并不歧視黑奴,他只是利用他們干活。他也會接受黑奴提出的更好的建議。在安息日,他會誦讀圣經(jīng)給黑奴聽,目的其實是軟化黑奴的造反心理,使黑奴死心塌地為他干活。對于表現(xiàn)出色的黑奴,他甚至會給以適當?shù)莫剟睢F┤缢_門·諾瑟普成功開辟了一條河道的捷徑,為此他獎勵所羅門一把小提琴。但他所有的行動仍以利益為轉(zhuǎn)移。在所羅門遇到威脅時,他不是放他自由,而是將他轉(zhuǎn)手賣給另一個黑奴主。約翰·提畢茲是個白人工頭,骨子里充滿種族歧視思想,認為白人優(yōu)越于黑人。他自編的歌謠充滿種族歧視:“黑鬼黑鬼跑啊跑,撕開襯衫跑啊跑。只要逃跑,鬼就來找。黑鬼快跑,別被抓到。”他自視高人一等,要黑奴稱呼他主人。他不懂河道工程,被黑奴所羅門比了下去,從此處處和所羅門為敵。他們終于打了起來,約翰·提華茲卻反被所羅門教訓了一頓,他找來幫手,準備吊死所羅門。這是一個惡棍式充滿種族歧視的白人。埃德溫·艾普斯是個種植棉花的農(nóng)莊主,豢養(yǎng)了許多黑奴,被稱為“黑人殺手”。他在管理黑奴上以嚴厲出名,他給黑奴規(guī)定了每天的工作目標,達不到標準者,要遭受鞭刑。他的農(nóng)場上有個黑奴姑娘帕特西,每天都能超額完成任務,他親切地稱她為“田中女王”。暗地里,他愛著這個姑娘。但種族思想使他不可能和她產(chǎn)生正常的男女愛情。他在某一個黑夜里奸污了她。他對妻子已無愛情,真正愛的是帕特西。由于妻子從中作梗,他又不可能得到帕特西。他的單向度的愛在時間的流逝中扭曲了。后來,他在虐待帕特西中表達愛,這是個復雜而心理扭曲的人物。巴斯是個好的白人,他是加拿大人,從事木匠手藝,云游四方。他善良,同情黑奴,抨擊黑奴制,富有正義感。正是他的好心幫助,所羅門才終于脫離黑奴的苦難生活。
該片在藝術(shù)上同樣精雕細刻,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細節(jié)飽滿富有震撼力。“細節(jié)描寫是對客觀表現(xiàn)對象的某些局部或微小變化所進行的細膩描寫。”[5]“離開了細節(jié)描寫,就不存在電影劇作。只有進行具體、獨特、生動、深刻的細節(jié)描寫,才能構(gòu)成作品的真實性。”[6]該片在揭露黑奴制的罪惡上就是靠一個個感性的細節(jié)來達到的。如約翰·提畢茲為了報復所羅門·諾瑟普,找來幫手,準備將他吊死。在另一個工頭阻止下,他們憤憤離開。可是所羅門的身體仍被吊著,他只能靠惦著腳尖支撐身體。他就這樣被吊了不知多少時間。可見,黑奴是毫無人身權(quán)益可言的,他們隨時可能大禍臨頭。又如所羅門有一次借買東西之機,準備逃走。逃走路上,他遇到一群白人正準備私刑處死兩個黑奴。可見,處死黑奴在黑奴制下是司空見慣之事。此外,值得一談的細節(jié)還有許多。其二,人物語言富有音樂感。片中許多人物的說話腔調(diào)富有節(jié)奏感,仿佛歌謠一般。約翰·提畢茲的種族思想是通過一段歌謠來體現(xiàn)。埃德溫·艾普斯喜歡縱酒狂歡,半夜里把黑奴們喊起,和黑奴們一起唱歌跳舞。威廉·福特在安息日給黑奴誦讀圣經(jīng),他的姿態(tài)神情猶如教堂里的牧師,語調(diào)抑揚頓挫。干活時,為了減輕勞累,黑奴唱的是動聽的勞動歌。為了給去世的黑奴做禱告,黑奴們聚在一起,哼唱傳統(tǒng)的禱告歌曲。其三,片中有不少象征。“象征手法是以外界存在的某種具體事物當作標記或符號,表現(xiàn)隱含哲學思想的具體內(nèi)容,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和表現(xiàn)力。象征符合藝術(shù)審美的具象特征,它使抽象意蘊同具體形象相融合,賦予形象以超越自身意義的更為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7]“它往往具有暗示性,需要通過聯(lián)想體驗形象所傳達的含義,調(diào)動讀者的多種感官從各個角度去捕捉形象的意義。”[8]如在所羅門被賣為黑奴的船上,鏡頭有兩次對著快速轉(zhuǎn)動的船槳,配合畫外沉悶單調(diào)的轟鳴聲。這里暗示的是黑奴們不詳?shù)那熬啊S秩缢_門托安斯比寄信,可是對方出賣了他,他只好燒掉信。信在黑暗中燃燒,慢慢熄滅,這象征的是他得救的希望破滅了。再如所羅門憤怒地砸碎小提琴,這象征他對白人完全失去好感。
假如沒有那位善良正義的巴斯的協(xié)助,所羅門·諾瑟普是不可能逃離南方蓄奴區(qū)而重獲自由的。即使他逃離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十二年也回不來了。片尾的字幕顯示:他想要起訴,討回公道,卻因證據(jù)不足而敗訴。這就使全片始終籠罩著抑郁而憤激的情緒。它是嘆息,更是控訴,控訴黑奴制的罪惡。它是傾訴,更是確認,確認著黑人們曾經(jīng)的苦難。“而真正的電影則與之相反,它是讓人們確認:確認歷史,確認真實,確認自我,確認現(xiàn)實,最終確認時間。”[9]“我們還沒有忘記,古巴的溫貝托·索拉斯創(chuàng)作的革命電影中,革命對象不只是包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獨裁政權(quán)、階級壓迫,它還包括性別歧視、種族壓迫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社會現(xiàn)實。”[10]“一部關于歷史的電影杰作,最終超越電影,因為它不只屬于現(xiàn)在、屬于電影界,更是屬于歷史、屬于永恒、屬于全人類。電影歷來就是這樣,她可以使人迷醉,也可以使人警醒;可以使人忘卻,也可以使人銘記;可以使人冥想,也可以使人追思。”[11]
(作者畢業(yè)于南京藝術(shù)學院影視學院,影視批評學專業(yè)碩士)
[1][3]鄭雪來.世界電影鑒賞辭典(續(xù)編)[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2]王宜文.世界電影藝術(shù)發(fā)展史教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4]王麗娟.影視鑒賞與影評寫作[M].江蘇: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6]許南明.電影藝術(shù)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7][8]鄭克魯.法國文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9][10][11]賈磊磊.電影學的方法與范式[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