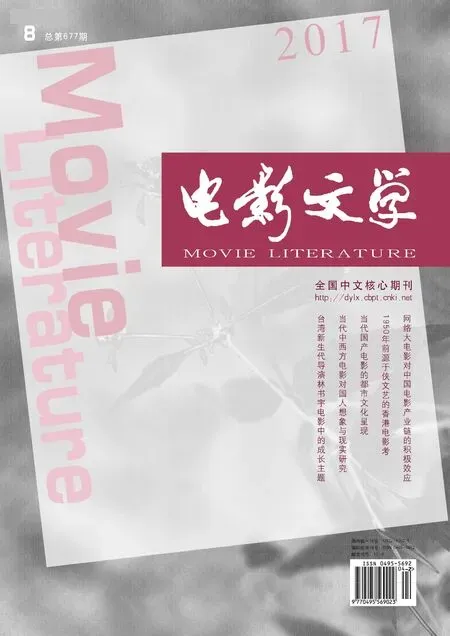“后喻電影”的青年文化特質與美學趣味
葛小華(黃河科技學院,河南 鄭州 450063)
一、青年主體下中國電影的視域位移
近年來,電影欣賞觀眾趨于多樣化,而電影創作在表現手法上也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傳統模式。跨界創作與跨屏傳播成為電影市場上的主流,中國電影新力量的迅速崛起,直接導致電影界不可控制的震蕩,具體表現為絕佳的票房成績。這主要歸結為 “邊緣”地帶、帶有“抵抗性”的青年亞文化正在默默并且有力地影響著當下中國電影的創作方向和方式。
在早期,動漫創作通常被稱為ACG。而“二次元” 則代表著二維平面設計。它們創造的虛擬角色和虛擬情境,都可使受眾直通理想的精神世界,再加上中國電影觀眾的低齡化與“網生代”觀眾的壯大,二次元文化逐漸成為青年亞文化的表征形態,影響著中國電影新力量的審美邏輯。一些區別于傳統電影的新鮮的電影,不論在題材設定,還是在表現形式上,都取得了絕佳的成績,受到觀眾的喜愛,然而它們之間并沒有交集可言,但它們有本質上的共同點:二次元文化是它們的內在基因。
中國電影的新力量,也代表著中國導演的年輕化,這也讓二次元成為中國新電影當中日益突出的審美文化標準。它也因此受到青年觀眾的喜愛,從而上升到青年亞文化審美層次的高度。想要解碼青年亞文化進入中國電影內部的路徑就必須充分把握青年亞文化群體的文化形態和審美邏輯。
二、后喻電影的青年文化特質
觀禮中國電影時不得不引入“青年亞文化”的議題,是因為它與中國電影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可抹殺的聯系性。這種聯系性,也關聯著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并成為最為重要的核心議題。2015年,48.7%的同比增幅顯示了中國電影市場活力突增,而2016年上半年電影票房成績的下滑,讓電影業界對于中國電影的長期發展引發了深刻的思考。在他們看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如果想要積蓄更多的力量,只有依靠消費主體青年。換言之,作為藝術與文化高度表現形式的電影,不應該被畫上年齡代際屬性。尤其對于藝術片而言更應如此。它的受眾絕不以年齡來劃分,而作為產業的電影對“年齡”“代際”有更多的選擇性和迎合性。這種由于“年齡”挑剔帶來的焦慮則成為中國電影新的尷尬點。很明顯,當下中國電影創作并未從根本上契合青年群體的審美文化訴求,但從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整體角度來看,這種矛盾性,并未引起電影業界足夠多的重視。電影創作者與電影消費者之間的這種矛盾性,將直接影響到電影產業的未來。電影界的業內人士,應該對此問題給予高度的重視,而非忽略。
網絡自制劇的新型創作者們紛紛在大銀幕上嶄露頭角,代表著以亞文化形態流行于虛擬空間的二次元思維表達方式,而這一新型文化特質已滲入并影響著中國電影的文化趣味,極大地擴充著電影的審美文化空間,同時也挑戰著電影審美的包容度。討論至此,如果說,從目前來看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主要問題,與其說是消費創造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矛盾,倒不如說是亞文化這一現象正在成為主流趨勢而逐漸地融入中國電影中來,并作為新的發展元素引領著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
如何界定青年亞文化呢?相對于認同主流價值的青年文化,“亞”則與主流文化區別開來,其最顯著的標志為“抵抗性”“風格化”和“邊緣性”。因其帶著似有似無的敵意挑戰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或者反對主導結構的束縛和壓制,青年亞文化往往被置于主流文化的“權力”關系中加以層層審視。事實上,中國內地青年亞文化正在作為電影產業新的發展元素,并入其中,并日益成為一種新的審美文化,逐漸影響著人們的欣賞口味。
作為一種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化現象,青年亞文化已經成為影視文化生態中的重要文化資源。可以預見,青年亞文化在與網絡媒介充分交融之后將會對主流電影文化產生積極影響和刺激,與主流電影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動。比如主流電影文化讓渡出一部分創作空間,而網生青年亞文化以溫和的方式進入主流電影創作,那么中國電影的審美文化空間將會得到豐富和拓展,同時也為中國電影的“持續”發展提供動能。
三、后喻電影的美學趣味
即使青年亞文化對中國電影的影響存在爭議,仍然無法忽視它作為新生事物不可抑制、不斷放大的影響力。網生文化與青年亞文化交融后形成的審美趣味正在成為主流電影審美文化的重要補充。在此,本文須借用“后喻”概念來補充解讀青年亞文化在電影業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所謂“后喻文化” 完全是由青年作為知識的傳播者,向年長者進行傳輸的過程。這種現象通常情況下被稱為反向社會化或“文化反哺”。在電影業中由網絡新生代為核心的電影創作群和消費群的崛起,表示“新型”審美正在生成。在此作用下電影所呈現出來的面貌,也因此具有文化反哺的特質。從而這一階段的電影被稱為“后喻電影”。 這種特質現象的出現在當下中國電影中掀起了新的波浪。由它所引發的電影與靜、視角等問題,超越了原有的局限性,它讓電影創造的空間更為廣闊。
在“后喻電影”觀念下,我們更多關注的不是青年群體對當下電影的一種消費,而是在消費的過程中所引發的第二次生產模式的產生。也就是說,在互聯網語境下,所有有關電影產業方面的動漫、游戲、動畫等多種形式,都可通過互聯網,作為網上資源來進行第二次應用。從而激發出新的創作模式或經驗來源,在互聯網空間中成為另外一種對于世界的體驗方式。這種體驗方式的產生,并非只是簡單的文本形式,通過互聯網形式而進行傳播或體驗。它是經由網生代中的某一文化訴求而成為第二次創作的資源。網生代會根據自己的世界觀策略性地構建他們自己的影像意義體系,當這一現象被高速發展的中國電影產業捕獲后,其在理論層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所以,從這一角度看來,“后喻電影”具有前所未有的原創性意味。
“后喻電影”,通常情況下是指互聯網在電影中所扮演的角色程度,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多元化,以及青年亞文化的崛起,這三大因素的并置,讓中國電影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觀眾對于電影的審美標準也隨之做出了不同的反應。進一步說,隨著網絡媒介的迅速普及化,電影當中的青年亞文化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其中,青年亞文化的普及度,就是它最為顯著的現象。二次元以及一批非主流小電影,在虛擬空間的推動下,引發了一批觀眾的響應。盡管作為小的電影力量存在于網絡中,但網生文化的魅力,以及電影產業發展的新力量背景,使得這些小電影不但沒有遞減的趨勢,反而呈現出進入主流電影的勢頭。在電影業界中,對于網生代這一新興名詞給出了最為恰當的解釋。在他們看來網生代就是通過互聯網以及電影產業的多元化和青年亞文化而產生,它是這三大背景元素的產物。它與網絡移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隨著網絡媒介的迅速普及化,觀眾被分成兩代人。而其中的網生代,便是指那些在網絡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他們這一代人中,網絡計算機一直伴隨著他們的成長,并將影響到他們的審美口味。而作為網絡移民,則更具有傳統的欣賞模式,對于電子化信息,他們更多的是做出了排斥性反應,更不喜歡超鏈接功能應用。而網生代則是一直在自覺通過自身的發展來構建起新的網絡文化,并成為主流趨勢存在其中。另一方面,網絡移民,則更喜歡將帶有批判性、價值性的東西作為保留,而不是作為傳播的手段放置到新媒介中間。與網生代相比,網絡移民對于互聯網的感覺更多地趨向于麻痹,簡稱“網感缺失”。伴隨著網絡媒介的迅速發展,網絡媒介也逐漸在電影產業中迅速融入,網生代們更是開始行動,通過網絡平臺構建起新的電影模式。在他們看來,這種網感的存在,應作為電影產業發展新的力量與創作源泉存在其中,他們堅信這會給電影產業發展帶來新的活力與生命。
那么問題來了:應如何定義和認識網生群體的新型影像文本?青年群體通過對原有的電影元素進行重構,從而創作出“前文本影像資源庫”,再加上“網生代” 在互聯網中所取得的經驗,融入自身的創作意圖以及創造邏輯,從而完成并產生新的電影影像。這就是網生代在素材資源層面的特點。已成熟存在于市場的電影可以作為“前文本”的形態存在,通過網上群體的第二次創作以及技術性加工,從而讓原本沒有新意的電影,經過巧妙的拆組后成了一個全新文本,它的意義在于網生代們通過一些視頻、音頻制作軟件,從而為電影創作出了新的味道,讓電影具備了不一樣的審美情趣。然而從“網生代”所創作的電子資源來看,可供他們使用的媒介資源可謂多種多樣,這已經不再是電影文本這樣一種簡單的形式所能匹敵的。他們完全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平臺尋找到不同地域空間的各種資料來進行新的組合、新的創作。他們將這些音頻、視頻資源進行第二次整合,從而形成與前文本完全不同的再創作影像。一些網絡自制劇也紛紛開始在電影大銀幕上嶄露頭角。他們通過二次元這樣一種新的方式,將他們的作品帶入到大眾的視野。他們是作為一種小群體出現的,然而他們所掀起的二次元創作浪潮以及在互聯網上所引發的潮流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因此也被大眾稱為“精眾”。 而作為網絡游民一代,因為他們對媒介文化的無所適從,以及對新力量存在的不可感應性,因此,面對大量的信息資源以及來自于網絡信息化的資源整合,使得他們越發對“前文本影像資源庫”無感。
然而,這些來自于不同地域、不同媒介平臺的雜亂信息經過網生代的第二次創作之后,這些在網絡移民看來毫無價值意義與感應的“前文本影像資源庫”,反而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形式存在,而是作為網生代的一種跨媒介敘事可能。美國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對于由青年亞文化形式所產生的粉絲文化現象進行了關注。他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將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流,并認為粉絲生產的“盜獵”文本增加了敘事視角的多樣性。換言之,盜獵文本并非要試圖尋找來自于不同媒體之間的交匯點,而是借由這些交匯點的存在來進行再次敘事的可能。例如,在由美國DC公司和漫威兩大漫畫公司所創作的英雄人物形象中,觀眾并非完全滿足于單個英雄人物形象的存在,相反,他們在觀看眾多英雄人物形象之后,反而更多地聯想到當英雄人物之間發生碰撞的時候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于是DC和漫威就以此問題作為契機,推出了《超人大戰蝙蝠俠》《美國隊長3:內戰》兩部電影,這不僅僅是對影迷們的一種積極性反應,也是對前文本進行第二次創作的成功范例。它就是通過二次元粉絲結合了有趣的ACG元素,從而產生了新的影像,進而激發了更多觀眾新的觀賞沖動。
四、結 語
面對中國電影“新力量”的崛起,特別是更多青年力量的融入,他們將作為一種新的創作群體,引領著中國電影新的潮流發展,“后喻電影”觀念僅僅是對這一新型影像及審美文化形態的嘗試性概括。在此之外,理論上仍存在諸如作為青年亞文化,它將在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它會給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帶來怎樣的沖擊。而將網絡話題與青年亞文化相結合是否真的妥當?“粉絲作品”是否真的能顯現出如人們所預計的價值性?等等,這些潛在未知的風險值得中國電影業不斷改構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