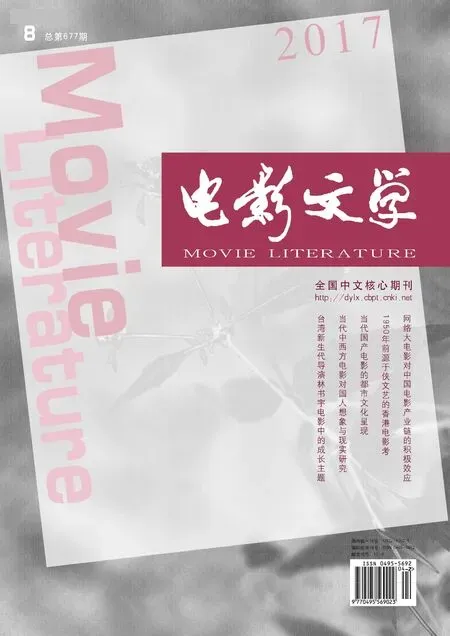英美恐怖電影的宗教原型解讀
鄒 艷 (保定職業技術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恐怖電影是在百年影壇中盛行不衰的電影類型之一,它的長期風靡背后絕不僅僅是因為電影人特殊的熱情與執著,還與社會特有的文化烙印有關。而在恐怖電影中,英美恐怖電影又在表現形式、慣用題材等方面迥異于日本等東方恐怖電影。從英美恐怖電影中,可以看到大眾心理的折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西方人的宗教情結與宗教信仰。
一般來說,對英美恐怖電影影響最深的宗教非基督教莫屬。自古羅馬時代起,基督教就深刻地影響著西方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基督教教義便是人們行事的基準之一。基督教以《圣經》為宗教典籍。為了達到使人分辨善惡是非、了解罪與罰的目的,《圣經》中的大量敘事都能夠激發人們的恐懼心理。部分電影人看到了基督教的影響力以及基督教帶給人的敬畏心理,將宗教原型、宗教理念引入恐怖電影的創作中來。只有對這些宗教原型進行解讀,我們才能有效地把握英美恐怖電影的特色,從而進一步將其與其他地區,擁有其他審美風貌的恐怖電影區分開來。
一、吸血鬼原型
吸血鬼(Vampire)的傳說起源于歐洲,千百年來都是西方文學創作中與恐怖、邪惡掛鉤的意象,時至今日依然為人們津津樂道。盡管最早將吸血鬼題材搬上大銀幕的是德國電影,即F.W.茂瑙的《吸血鬼諾斯費拉圖》(1922),但后來英美恐怖電影顯然將這一題材運作得更為成熟,英美挾電影工業發展與語言的優勢使吸血鬼文化不斷隨大眾文化的發展、都市消費大眾的需求而變化、豐富,《暮光之城》(Twilight,2008)等能夠充分適應當代觀眾娛樂與休閑需求的電影便是例證。
在《圣經》中,猶大僅僅為了30枚銀幣就將耶穌出賣,導致了后者的死亡,對此猶大選擇了在日落之時上吊自盡,但因為其罪孽深重,于是死后變為可以長生不老但是卻注定孤獨的吸血鬼。日落、銀幣與背叛等元素使得吸血鬼原型帶有不能見陽光,害怕十字架與《圣經》,銀幣是吸血鬼的克星等特點。如在尼爾·喬丹的《夜訪吸血鬼》(InterviewwiththeVampire:TheVampireChronicles,1994)中,吸血鬼路易、斯塔特以及克羅地亞都無法直面陽光,因此他們只能在夜間出來游蕩,白天的時候,他們就和阿蒙等吸血鬼一起躲在劇院的地下。在外形上,他們纖細、蒼白,有著小小的尖牙。
另外,吸血鬼就原型而言,是被貼著邪惡的標簽的。《圣經》中的該隱故事被基督教研究者認為也是吸血鬼形象的來源之一。該隱是亞當與夏娃的長子,他曾經因為嫉妒而殺死弟弟亞伯,為此受到了上帝的詛咒,被流放到非洲,以吸食人血為生。謀殺親弟弟與吸陌生人之血無疑意味著對他人的暴力凌虐。部分英美恐怖電影中也延續了原型的這種定位,如在《夠僵行動》(Vampires,1998)中,吸血鬼王華生等人便是反面形象,他們手段殘忍,威力驚人,且具有奪取圣物十字架的野心,不少神職人員也被吸血鬼腐蝕,如地位崇高的主教就曾大言不慚地說自己只有與魔鬼結盟這一條路可走。他們以邪惡來襯托正面形象獵殺者杰克的正義一面。而部分電影則對吸血鬼抱有同情之心,如《暮光之城》里吸血鬼中出現了“素食吸血鬼”、《夜訪吸血鬼》中的吸血鬼有著明顯的同性戀傾向等,這些是電影為迎合日益多元化、日益包容的社會思潮而對原型做出的改變。
二、亞當(夏娃)原型
如果說恐怖電影中的吸血鬼原型是一個站在觀眾對立面的恐怖意象,吸血鬼給觀眾制造的恐懼感在于觀眾擔心自己將面對吸血鬼,那么亞當(夏娃)原型則顯然是一個使觀眾產生自我投射意愿的意象,此時觀眾擔心的是自己淪為這樣的角色。相對于吸血鬼類的恐怖意象而言,亞當(夏娃)原型與人類的關系更加接近,對觀眾來說這類角色帶來的恐懼感是更難逃避的。亞當或夏娃原型體現的是基督教中的原罪說。《圣經》中明確指出“原罪乃是眾罪之源、眾惡之母。它隨著亞當的過錯而進入世界,又隨著人類的繁衍而代代相傳”。在原罪說中,首先原罪是不分對象的,不管人位于哪一階層、哪一群體,他都是有原罪的;其次原罪是不分時間段的,人自出生起便有原罪,只有死亡是原罪的終點;最后,原罪主要體現在七(七是一個在基督教教義中反復出現的數字)個方面,即好色、饕餮、驕傲、嫉妒、懶惰、貪婪和憤怒。
有的恐怖電影表現的是人類犯下的其中一兩種原罪。如弗蘭克·德拉邦特執導的《迷霧》(TheMist,2007)中,小鎮被淹沒于一場迷霧中,并且迷霧中還有怪物,主人公戴維和他的兒子與其他人一起被困在超市里,超市里的人一個個或精神崩潰,或開始從意識上控制別人。戴維屬于其中最堅強的人,他最后帶著兒子、一個彼此喜歡的女人以及兩位老人抱著最后一搏的心態沖出超市,在聽到怪物的嚎叫聲后,絕望的戴維終于開槍打死了身邊人,因沒有了子彈而坐以待斃,不料等來的卻是救兵。換言之,如果他不開槍他和兒子是完全可以一起獲救的。在電影中,戴維本人盡管是一個正面人物,但是他也與亞當一樣擁有原罪,他曾經因為顧慮自己的兒子而不愿意送一位女士回家,結果他自己的兒子死了而那位女士和她的孩子卻活著,戴維為自己的自私和怯懦付出了代價。至于其他人,如妄圖走上神壇的卡莫迪太太、進行試驗的軍方與科學家等,他們犯下的是傲慢、貪婪的罪,他們都有因認為自己的能力十分強大而試圖取代上帝的嫌疑,他們無論是秉承宗教抑或是科學,所創造的都是海市蜃樓,都無法給人類帶來幸福。
與之類似的還有克里斯多夫·甘斯執導的,根據游戲改編而成的《寂靜嶺》(SilentHill,2006)。在電影中,寂靜嶺的惡劣環境是與人們在當地的采礦行為有關的,這種開采帶有貪婪的罪惡。而被施以烈火焚身之刑的小女孩兒阿蕾莎則是暴怒、嫉妒罪惡的化身。她在被燒之后,憑借強大的仇恨孕育出了“表世界”和“里世界”,表世界用來困住她仇恨的人,里世界則時不時釋放出妖魔鬼怪來折磨他們。最后在大仇得報,曾經迫害過她的女教主貝拉被鐵絲掏空了內臟后,阿蕾莎并沒有因此罷手,而是讓自己的靈魂占有了女主人公蘿絲女兒的身體,將這位母親永遠地困在了表世界中,這是她嫉妒蘿絲女兒的一種體現。有的恐怖電影則將七宗罪全部進行了展現,如大衛·芬奇的《七宗罪》(Se7en,1995),盡管該片更容易被歸于懸疑、犯罪一類中,但其也是一部帶有恐怖意味的驚悚片,電影的恐怖感并不來自靈異現象,而是來自兇手約翰對他認定的“罪人”的殘忍殺戮方式。
三、末世原型
英美恐怖電影中不僅有以人物形象為基礎的原型,還有環境原型。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末世原型。在基督教中,末世論(或稱終極論)是一個重要理念,這一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猶太教的“啟示”理論發展而來的。早期的基督教會認為,人類世界有一個最終結局,屆時耶穌基督將復活重返世間。基督為無罪者建立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將獲得永生。盡管隨著科學的發展以及千禧年的過去,末世論不再被人們奉為金科玉律,然而末世論依然觸動著人們的潛意識。這是因為無論時代與科技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人類依然沒能戰勝生命有限這一障礙。而死亡在基督教中被解讀為人犯下原罪后受到的懲罰。只要人還懷有對包括死亡在內的自身有限性的恐懼、不安之情,只要人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曾經自愧于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下地獄的有罪者,那么人就會在內心保存一份對代表至高無上能力的上帝主宰人間、耶穌救贖自己罪惡的期待。
在英美電影中,末世意象一般以兩種形式出現。一種是在災難片中,人類世界(地球)面臨重大災難,如氣候異常、外星人入侵等,人類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另一種則是在恐怖片中,末世被縮小為一個孤立的小地方,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數個或數十個人困在其中,他們為了擺脫困境往往是通力合作,使盡渾身解數,但依然無濟于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后者給予觀眾的恐懼感更為強烈,因為前者的影響范圍過大,災難過于深重反而使觀眾產生了審美距離,這種距離帶來的是安全感,且在觀眾的審美期待中,災難片往往以人類最終戰勝厄運得以幸存結束,而恐怖電影中只有一個幸存者,甚至是困境中每個人都死亡的結局并不罕見。如在魯伯特·溫萊特執導的《鬼霧》(TheFog,2005)中,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一個小城市突然陷入一團迷霧之中,并且迷霧中還有可怖的幽靈,他們在一百年前都是商人,因為陰謀而死于船難,現在他們要以拖其他人下地獄的方式來討回公道。而且幽靈們并不是毫無差別地進行攻擊的,他們要懲罰的是那些違背了七宗罪的罪人,而無辜的人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幽靈們將自己這一番殺戮視作給小鎮帶來“新生”。這種理念是典型的基督教末世理論思維。
又如在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執導的《恐怖游輪》(Triangle,2009)中,女主人公杰西被公認為來自西西弗斯原型,她與西西弗斯的相同之處在于,由于自己的某樣罪惡而不得不反復地做一件令自己感到痛苦的事,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只會無功而返,而由于各種原因,她又無法停下自己的行為。而西西弗斯則來自古希臘神話,似乎這部電影與宗教原型無關。但首先,杰西身處的游輪成為一個小型的“末世”環境;其次,杰西兒子的遭遇是可以用基督教中的“恩寵論”來進行解讀的。在基督教中,博愛的耶穌為了全人類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得救,因此教會解釋耶穌的死是有選擇性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恩寵。“一切從不曾得知拯救福音的人、一切精神不正常的人和白癡、一切不具備接受宗教——倫理之稟賦的人、一切為苦難及危厄和命運所阻而未能達到更高精神境界的人”都被排除在接受恩寵的范圍內,而在《恐怖游輪》中,杰西的兒子恰恰就是一個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盡管在現代文明的理念中,他是無辜的,但是在帶有歧視意味的宗教理念中,他卻是一個無法得到上帝恩寵的人。杰西整個悲劇的開始就在于作為一個單身母親,她終于在生活的巨大壓力之下責罵了自己因為智力缺陷而將家里弄臟的兒子,在游輪上回來的杰西將正在罵兒子的杰西殺死,再帶著兒子去拋尸,結果導致了兒子因車禍而死,杰西只好又開始下一次輪回。最后,西西弗斯故事也記載于《圣經》中,因此整部《恐怖游輪》實際上也是與宗教有千絲萬縷聯系的。
電影研究的目標從來就不應該僅僅是電影藝術本身,還應該包括電影中囊括的時代特征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英美恐怖電影代表了西方人的某種娛樂旨趣以及文化特質,其中部分意象與敘事模式甚至在電影百年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擁有豐富層次的體系。宗教信仰為英美恐怖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吸血鬼原型、亞當/夏娃原型和末世原型等。在流行文化更新換代極快、強調解構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大行其道的今天,上述古老的宗教原型卻能在英美恐怖電影中不斷推陳出新,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見英美電影人深重的宗教情結與基督教文化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