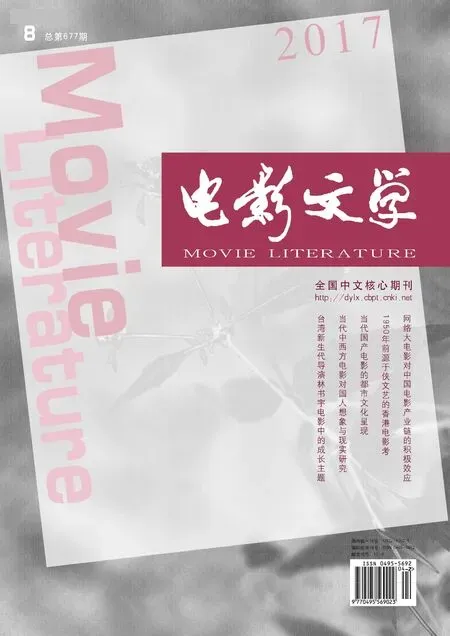論彭浩翔電影敘事中的“平衡”策略
馬翠軒 (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15年來彭浩翔導演共拍攝了13部電影作品,根據創作主題和題材內容,大致可分為“破事兒”系列和“小團圓”系列。前者包括《買兇拍人》《大丈夫》《公主復仇記》《青春夢工場》《出埃及記》《破事兒》《維多利亞一號》《低俗喜劇》等,通過邊緣事件的日常化講述、主流價值的顛覆化表達,展現了一幕幕乖桀叛逆的人物百態和一幅幅荒謬尷尬的現實圖景;后者包括《伊莎貝拉》《志明與春嬌》《春嬌與志明》《人間小團圓》《撒嬌女人最好命》等,通過不著痕跡的人物白描、暗藏草灰蛇線的生活碎片,細微體察都市男女的人心幽明和俗世妥協。兩個系列異曲卻同工,始終圍繞個體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故事,通過黑色幽默和“彭氏營救”等手法在電影敘事上實現了一種“平衡”策略,最終達到藝術個性與商業品質兩者之間的介質融合。
一、黑色幽默帶來電影受眾的心理平衡
“黑色”是指客觀現實的恐怖或滑稽,“幽默”則是指自由意志的個體對現實的戲謔和嘲諷,從而使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拉開距離,以維護飽受摧殘的人的尊嚴。黑色幽默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它的興起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潮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經濟實力大增,科技迅速發展,政局卻持續動蕩:麥卡錫政治迫害延續、學生反對越南戰爭、肯尼迪總統被刺身亡、黑人民權運動和解放運動、民眾苦悶彷徨……黑色幽默成為知識界對抗這個荒誕、瘋狂世界的最佳利器。
反觀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物欲橫流,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冷漠和信任危機日益加重,97回歸后新的主體身份想象和認同帶來某種陣痛,香港導演北上發展遭遇水土不服……現實和藝術雙重領域都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物質與精神的矛盾。彭浩翔及時覺察,把黑色幽默當作一種觀察世界、表達觀點的獨特方式,一種調息導演個性和市場需求的敘事策略,通過多種元素解構重組、類型敘事嫁接挪用、角色關系錯位突變等手段,遮蔽尷尬現實鋒芒,緩解都市生存焦慮,使作品個性和大眾的觀影體驗之間達到平衡。
(一)邊緣敘事與主流文化的解構重組
在后現代語境中,形式主義的狂歡首先表現在敘事的反叛性和游戲性、結構的實驗性和新銳性。在彭浩翔的電影作品中,主流事件顛覆化,邊緣事件主流化,多種元素彼此悖逆、分解、顛覆,導致終極價值模糊,道德指向曖昧。如電影《破事兒》片頭所示:“世界上有很多事,看似驚天動地,實際就那么回事。”
當主流事件被顛覆化解構、重組,呈現出敘事和畫面上的雙重“陌生化”,便成為大眾狂歡的載體和舞臺。電影《青春夢工廠》暗喻著青年導演的電影夢和香港電影發展的坎坷歷程,“解構”后呈現出一場散發青春荷爾蒙的AV夢:“夢想”和“女優”兩個道德色彩彼此悖逆的詞匯,卻共同激發了學生們的感動和共鳴,單純美好的青春理想等同于拍AV和與“女優”上床的直觀訴求……主流事件被擱置為邊緣化敘事,主流文化“淪落”為“硬植入”,便制造出了具有反差感的滑稽色彩。與此同時,邊緣事件卻高登大雅之堂,被進行主流化、公共化、日常化的呈現。影片《買兇拍人》中殺手阿本和被殺對象有閑情討論樓市升值,家人聚會吃火鍋時丈母娘讓阿本順便幫忙殺個人,荒誕意味頓生。
雖然彭浩翔的電影游走于邊緣和主流之間,題材多青睞婚外情、亂倫等禁忌話題,《買兇拍人》中殺人就像吃飯一樣日常自然,但殺手依舊會膽小、害怕警察。電影敘事始終控制在道德規范之內,時常自覺映現主流價值觀念,從而平衡邊緣題材的道德色彩,維護公共秩序的權威性。
(二)非主流故事和類型化敘事的嫁接轉譯
近年來商業電影蓬勃發展,電影受眾經過類型化敘事的長期培育,對“類型化”鏡頭語言、故事結構等均可熟能生巧地進行直覺解碼和自動詮釋。這成為彭浩翔電影利用類型化手法對非主流故事進行嫁接和轉譯,依然能獲取觀眾認知和接受的心理基礎。
電影《大丈夫》挪用、嫁接了香港黑幫電影類型的橋段和元素,于是黑幫電影自帶的宏大儀式感、道義責任感消解了偷情事件的隱私性和猥瑣感,梁家輝等明星的夸張表演方式和社會正面形象弱化了人物角色的下流色彩和社會批判性。英雄本色的敘事模型與偷情聯盟的市井主題悖逆抽離又相映成趣,形式的高渺和內容的世俗之間構成強烈的戲劇反差。荒謬感和滑稽感時刻召喚觀眾的理性參與和上帝視角,但在香港黑幫電影敘事的邏輯慣性和儀式感召下,觀眾們置身事外的第三視角被掣肘,不自覺地被偷換為偷情聯盟的感性立場。隨著立場與視角的不斷變化調整,觀眾的觀影體驗和價值判斷不斷被“喂食”和挑釁,于波動和復位之間實現了某種平衡。
(三)角色定位和人物關系的錯位突變
角色定位和人物關系的結構錯位,以及不確定性的發生突變,讓影片充滿懸念和戲劇沖突,產生明快或延宕的節奏,使得電影主題在主流和邊緣、失衡和平衡之間來回反復。
《出埃及記》中,人物雙重身份的揭示和人際結構關系的變化,成為推動電影懸疑發展的動力。角色的身份語境和矛盾選擇,使人物碰撞和情節發展時激發出更多的敘事空間,鏡頭與畫面則著力刻畫平衡被打破后人物的痛苦、矛盾和困惑。譬如,大量靜止或微晃的長鏡頭暗示著人物內心的掙扎猶疑和角色之間不動聲色的對峙較量,高空旋轉鏡頭則象征著夫妻、同事等日常社會關系的失衡與破裂,場景中角色多處于封閉黑暗的寫實空間,人物站位關系的對角線交點幾乎從不位于畫面中心處:個體失落了其話語中心地位,人物關系縱橫制約,“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生態中平衡與危機并存。
而《破事兒》中,角色定位和人物關系的錯位突變被作為一種后現代式無厘頭手法所應用。“尊尼亞”一節,殺手約見被殺對象,從焦慮等待任務啟動→聊天投機相逢恨晚→預備射殺氣氛緊張→女友來電變身暖男,人物關系忽緊忽緩,情節急轉跌宕,殺人任務不了了之,打破了觀影期待。《買兇拍人》中,殺手、導演、夫妻等角色的固有形象被顛覆,人際關系的突變節奏更加緊湊明快。岳母讓阿本殺掉她的牌友,岳父則暗地讓他殺掉岳母,表面和諧、暗藏矛盾的人物關系制造出螺旋形上升、充滿張力的戲劇沖突,緊接著岳母又勸說阿本“子彈值不了幾個錢,多殺個人也無所謂”,吊詭情節隨之適可而止,平緩了道德被解構所引發的觀影焦慮。
二、“彭氏營救”實現電影主題的價值平衡
以追逐市場為主要目的商業電影,其敘事面貌最終將受到“大多數”觀眾的制約和影響。“彭氏營救”策略修補了后現代敘事的圓形缺口和道德誤差,尤其在商業市場定位清晰的“小團圓”系列中表現更甚。所謂的彭氏營救,是彭浩翔電影向主流敘事和價值觀念的潛意識靠攏,他塑造了具有彭氏色彩、反英雄的“英雄式”小人物,對世象百態和復雜人性給以理解同情,同時打破電影時空的封閉結構,降解電影的“欺騙”性和現實殘酷性,實現對傳統價值的溫情依歸和對現實的人文反思。
(一)“英雄式”小人物
荒唐莽撞的年輕人和尷尬困惑的中年人,是彭浩翔電影里的常見主角。他們是社會建設的中流砥柱,也是經濟快速發展下的承重墻,面臨著生活中的焦慮浮躁、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難覓出路的迷失……這些被彭浩翔以戲謔方式或零度態度所描述:《買兇拍人》里雇主要求阿本拍攝殺人過程以滿足復仇的快感,《出埃及記》中警察老公和隱藏殺手身份的妻子在日常溫存背后隔膜深重……人物呈現出后現代式的悲劇感:否認自己,也否認集體,難以掌控人際(現在),也難以掌控未來。如彭浩翔所言:“對人的關系比較沒有信心,沒有人會跟你是天長地久的,沒有人會跟你講全部的秘密,秘密是不分男女的,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是自私的。”
即便如此,電影并沒有停留在解構話語層面,而是在反思中給予人文關懷,重新回望和建構主流價值的意義和人性的希望。《伊莎貝拉》中的父親形象和寵物伊莎貝拉都象征著現實中難以獲取和堅守的美好情感,張碧欣的尋找和捍衛愈發顯得卑微和珍貴,充滿人情之美。導演也以夸張或平實的手法打造了堅持追求夢想,并不斷成長的一群反英雄的“英雄式”小人物,“AV夢”“偷情夢”也被亦莊亦諧地賦予了脫離束縛、追求自我的理想色彩。《青春夢工廠》里舅父罵學生們是“垮掉的一代”,映射出導演對當代香港年輕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不滿和警示,但片尾導演依然引入“1971年7月7日保護釣魚臺學生運動”向年輕人表示致敬。他借助美智子之口勉勵年輕人:“當我們相信自己對這個世界已經相當重要的時候,其實這個世界才剛準備原諒我們的幼稚。”
(二)共情與懲罰
在彭浩翔的電影人物群像里,大部分人能夠獲取同情、得到解救,實現“人間小團圓”,而小部分人則難以獲得同情、面臨懲戒,陷入尷尬境遇。《大丈夫》中片尾閃回了某個妻子給偷情聯盟發短信提醒捉奸大隊即將抵達,“最后一分鐘營救”解除了人物困境,且頗有歐·亨利式結局的幽默特點。《維多利亞一號》中,開放式結局的想象空間和道德底線的追求維護構成了本片的兩極張力。鄭麗嫦連環殺掉11人,但影片通過希區柯克式“罪孽轉移法”,始終挖掘她的尷尬處境與潛在動機,引發觀眾共情。當故事結尾故意設計為2007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房價暴跌,鄭麗嫦的買房夢想最終破滅,則實現了女主角“原罪”的因果敘事,這是對觀眾共情的懲處,同時也是對道德界限的潛意識維護。
(三)適度“穿幫”
選擇性地適度打破電影敘事的封閉結構,是導演慣用的娛樂伎倆和敘事策略。“本故事由真實案例改編”,彭浩翔用電影《維多利亞一號》開多重語義的“虛構”玩笑。《破事兒》的“做節”段落中,阿富數次對準鏡頭講述故事進展,但又揭穿觀眾看到的影像只是把演戲的情節提前“畫面化呈現”,具體拍攝還要“等導演來了再定奪”,因此“做節”故事和女朋友之死實際上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這種故意穿幫、自我否定的手法,打破了電影圓滿自足的時空結構,進一步強調故事的“虛構性”,揭示電影的“欺騙性”,降解了故事主題的黑色元素和消極成分,是平衡電影價值取向、迎合觀眾市場的敘事策略。
(四)溫情述說
從“破事兒”系列到“小團圓”系列,溫情一直是彭浩翔電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從《伊莎貝拉》開始,黑色市井幽默轉為暖色人間喜劇,更加純熟的溫情敘說成為其商業電影創作的主打牌,擴大了其觀影受眾范圍,提升了電影的市場容納度和傳播度。《買兇拍人》里小導演為喜歡的女優特意撰寫日文劇本;《破事兒》里大頭阿慧懷念陳百強;《人間小團圓》里所有人拋開了心理陰影,開始諒解寬容他人,實現了內心的圓滿自在;而性格喜劇《撒嬌女人最好命》里“溫情”更是升溫為俏皮的“熱情”。電影藝術自覺擁抱商業,以觀眾和市場為導向,復雜的多元敘事調整為方便辨識的線性結構,人物關系暗潮涌動卻最終歸屬得宜——注重現實、珍惜當下的“小團圓”結局既是后現代迷茫綜合征的中庸之選,也是新時期人文精神探索中的一種出路。
彭浩翔常說:“對那些高呼現代藝術不需以取悅人為目的的人,只能告訴他一句:快點長大吧。”作為一名專業的商業電影導演,他盡情揮灑著藝術個性,反對程式化情節和模式化人物,同時尊重電影的商業性,以主流價值和市場認同為圭臬,回歸現實當下語境,在“破事兒”實現“小團圓”,通過電影敘事“平衡”策略,保證了其電影作品的藝術尺度和商業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