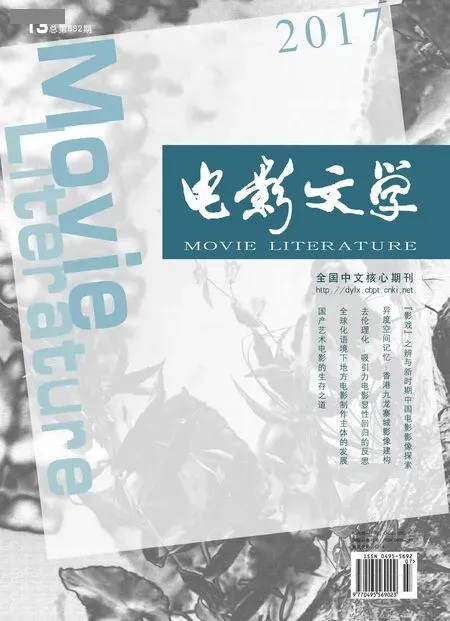杜琪峰《黑社會》系列電影探究
逯俊寧
(無錫市新吳區公共文化中心,江蘇 無錫 214135)
一、香港電影黑幫題材的回顧
香港黑社會題材的電影大多數將黑社會中的人物塑造成英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美化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對人性的美化,是對道義的崇拜。這樣的美化與崇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導演們寄希望于在黑社會這樣的邊緣圈中找到人性與道義的回歸。黑社會題材影片的經久不衰是與其獨特的風格魅力分不開的,片中對暴力元素的展現,視覺沖擊的強烈效果使影片具有很強的觀賞性,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也使觀眾在影片的欣賞過程中獲得觀賞的快感。
香港黑幫題材的影片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成為香港影壇中很重要的表現題材之一,這與黑幫題材影片暴力畫面所具有的視覺沖擊力有一定的聯系。在最初的黑幫片題材中影片表現的主題往往是對黑惡勢力的打擊,崇尚的則是打擊黑社會勢力的英雄。
龍剛的《英雄本色》就是這種主題的代表作,他的主題還是對主流社會的歌頌,對社會秩序的贊揚,最終通過認罪服法、真心悔過的方式來體現影片主題。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黑社會題材的影片再一次繁盛,但影片所表現的主題發生了變化。在吳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中,周潤發飾演的小馬哥作為英雄人物的代表,表達的是在道義之上的黑社會中,只身一人、舍生忘死的大無畏英雄主義精神。影片通過人物性格塑造、槍戰畫面渲染、故事情節曲折等多種手段,塑造了一個講義氣、重感情的小馬哥。黑社會題材影片中相繼出現了《古惑仔》系列,《古惑仔》系列重點表達的仍然是對道義至上的崇拜,不同的是通過黑社會中的小人物來表現這一主題色彩,同時這一系列拍攝多部,時代特色更為鮮明。《無間道》系列中黑社會的主題則是通過主流社會與黑社會的交鋒來展現的,通過雙方臥底的角度來表達人內心深處的善惡,雙方的臥底都是在壓抑的環境下完成任務,都渴望能夠光明正大地生存。
杜琪峰《黑社會》系列中的人物形象是以一種正視的態度去塑造的,但比起之前的黑社會題材影片,杜琪峰的影片更多的是關注黑社會與當下社會人物之間的微妙關系,并且通過對黑社會中秩序形成的探究來闡釋當下社會的發展狀況。通過黑社會這一小圈子范圍內的秩序來展現黑社會之外的社會秩序。
杜琪峰的《黑社會》系列中所表達的雖然也可以看作是對道義和人性的一種表現,但并不只是從道義和人性本身來看問題。香港的黑社會題材影片常常是借黑社會這一題材對現實社會有所寓意,通過黑社會中假想的英雄強化對人性的表達。但生命是無常的,人類總是在一個又一個輪回中消耗著生命,人性的光輝在輪回的過程中變得暗淡。就輪回本身來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重要的我們要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輪回,而不是將人性的關懷表現給觀眾就可以闡釋這種輪回的意義。杜琪峰的《黑社會》中所體現的輪回告訴我們命運是一種絕望的輪回,這正是《黑社會》系列所要表現的主題。
二、絕望的輪回
杜琪峰的《黑社會》談的不是命運的不可知性,單看《黑社會1》這部影片,人物的命運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不可知性,黑社會的環境中人物的命運常常是危險的,大D在最后與阿樂妥協但卻不知最終還是會被阿樂殺死。如果我們的闡述范圍是《黑社會》 這個系列的話,人物命運的無常就會讓位于生命的輪回。第一部中固守社團大義的阿樂在第二部中成了破壞社團秩序的人,那么新的社團領袖吉米在下次的社團選舉中是不是也會成為背叛道義的人呢?事實上影片已經告訴我們道義已經不復存在,一切都只是為了生意、財富和權力,這也就是輪回之所以絕望的原因。
杜琪峰的影片可貴之處就在于不僅僅告訴我們這是一種輪回,而是指出了對社會秩序輪回的絕望。在以往的黑社會題材影片中對個人命運的不確定性也會加以表現,但這種表現常常讓位于道義英雄的塑造,對道義的過多闡述使得這些影片理想性的色彩濃厚,缺乏對黑社會現象真正的關注。《黑社會》系列中對秩序輪回是一種深層次的發掘。當道義不是黑社會中立足根基的時候,什么才成為社團運作的關鍵呢?片中說得很明白:“時代不同了,談的都是生意。”在這樣一個又一個的輪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金錢、權力在當今社會的肆意橫行,從而也成為控制命運的枷鎖。以往的道德、理想在金錢的影響下不斷退縮,那個英雄的時代已經逝去,接踵而來的是對金錢的崇拜。
影片中個人命運的不確定與人生命運輪回的矛盾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如果說之前的黑社會題材影片對人性道義尚且抱有希望,那么在《黑社會》系列中權力、金錢的欲望在當今社會的橫行所產生的對江湖規矩的懷疑則徹底使人性道義的光環讓位于命運輪回的絕望。如果說在《黑社會》中杜琪峰尚對人性道義抱有一絲希望,那就是對飛機這個人物的塑造,在經過了一系列幫派糾紛之后,對金錢、權力依舊很渴望的飛機拒絕了吉米的幫助,雖然飛機沒有找到出路所在,但他在某種程度上拒絕了金錢、權力的誘惑。作者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人物來留下希望的種子,作為撬動輪回的一個點,能夠改變金錢至上的威脅。
邊緣的黑社會中秩序的運作背后是金錢、權力的操縱與控制,那么主流社會中秩序的背后又隱藏著什么呢?影片中對這一點也有所暗示。在吉米成為社團領袖之后主流社會向他提出了要求,社會要求的是安定團結的發展。社團內部每兩年的領導人選舉很大程度上會對秩序的維護造成損害,這樣的方式必然是不允許的。對現有秩序的維護必然會迫使吉米也重視對秩序的建立。其實吉米在最初也是作為中性人物存在的,既不偏向道義,也不偏向社團,他只是想做生意,殊不知時代不同了,談的都是生意,金錢對秩序的重建威力可見一斑。主流社會所擁有的只是對現有制度的維護,就像在黑社會中一樣,主流社會也一樣充滿著正義人性的缺失,影片絕望的主題再一次得到烘托。
三、純黑的色彩
電影對于觀眾來說是一種視聽藝術的綜合享受,畫面聲音的合理利用對于一部電影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部電影以何種形式展現在觀眾面前對于電影主題的表達有著深刻的影響。“一部電影所有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關系所形成的整體系統就是電影的形式。”①在《黑社會》系列中,導演多用低調的照明來烘托影片中緊張的氣氛,影片中充滿著黑色景象的畫面。黑色所代表的壓抑以及在壓抑下面的暗潮涌動都是黑色調被主要運用的原因。
黑社會中成員聚集的茶餐廳里常常是燈光昏暗的,多運用的是從人物背后照射的燈光。雖然可以讓觀眾清晰地看到人物面部的表情動態,但人物的臉上只是用弱光或者側光,給觀眾造成一種潛意識的壓迫感。故事的情節多數發生在夜里,往往畫面中的光線只是街燈或者房屋里射出來的一道道冷光。
由于照明的低調我們所忽視的往往是影片色彩的運用,黑色也是影片的一種色彩,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導演的紅白藍三部曲中色彩的運用,黑色是《黑社會》中的主要色彩。低調的照明昏暗近乎黑色的色彩運用,恰恰暗示了黑社會的邊緣性。視覺是人類獲取信息的首要感知能力,而在黑暗中視覺的缺失正是《黑社會》系列中色彩運用的立意所在。人類處于黑暗中時,視覺的缺失會導致視覺功能的不充分運用,從而造成對外界信息獲取的困難,無知的恐懼是人類無法擺脫的惡魔。無知也就成為我們在黑暗中常常感到恐懼的重要原因。《黑社會》系列中正是需要這樣一種氣氛的營造。
命運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不可知的,影片中的黑色色彩是對無知命運的回應與烘托。影片中絕望的輪回在低調的照明與黑色的畫面中也賦予了更加神秘的意味。我們可以說無知的人生是金錢、權力橫行的原因,這也許是人們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四、冷暴力的展現
暴力這個詞常被看作社會性的問題,特別是作為哲學性的命題受到人們的關注,在電影中暴力的色彩也常常是影片的特色。黑社會題材的影片對暴力的展現是這一題材影片的標志性特點,暴力在對觀眾造成視覺沖擊的同時也是影片主題表達的手段。在以往的暴力影像中,槍支是作為現代社會暴力的代表展現給觀眾的,而在杜琪峰的《黑社會》系列中基本看不到槍支的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刀鋒或者直接的肉搏。全片基本不見槍支,即使出現也往往不是槍支傷人。
在《黑社會1》中,飛機為保護社團信物龍頭棍,只身一人面對六個人的追擊。六個人手執利刃向飛機逼近,飛機將一人按在地上,鏡頭特寫刀慢慢刺入身體。此時是混亂的刀戰場面,昏暗的畫面配以刀刺入身體的聲音給觀眾造成很強的沖擊力。在《黑社會1》的結尾有場阿樂在山里殺死大D的戲,阿樂為了鞏固自己在社團中話事人的地位將大D用石頭砸死。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樂用石頭砸大D砸到第7下的時候大D已經死亡,但阿樂一共砸了14下,直到第15下舉起石頭看到自己的兒子就在面前才收手。接著是阿樂追殺大D的妻子,在用鐵鍬砸了8下之后又用木棍將其勒死。畫面中打砸的聲音配以周圍群猴圍觀的尖叫聲是暴力展現的極致。
《黑社會》系列中暴力回歸到原始的層面,基本不借助現代工業文明的力量,而是完全在原始狀態下冷兵器時代人們肉搏的強制展現。在原始的條件下,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將對手致死是生存的渴求。在現今社會中,人們將金錢和權力作為追求的目標,不擇手段地將對手致死。一個之前講道義、有人性的人在金錢和權力的誘惑下展現出人類原始殘忍的暴力,這時候道義人性已經不復存在。
以往黑社會題材的影片中暴力美學的展現往往會有正義邪惡之分,注重的是對江湖規矩的捍衛、對正義的維護。在《黑社會》系列中顛覆了以往的主題,影片中阿樂在第一部中是規矩的維護者,在第二部中又成為破壞者。阿樂所展現出的對江湖規矩的捍衛、對正義的維護就是一種虛偽的外包裝。同樣,在這里展現的暴力并不是為了激發人們的原始暴力,而是用暴力的視覺沖擊展現影片絕望的輪回的主題。原始沒有傾向性的暴力不會讓人們產生暴力的崇拜,相反,我們可以通過暴力符號的指向性,看到暴力下面的內核,而不是迷戀暴力的視覺沖擊。
暴力是影片展現主題的重要形式,在黑社會題材中對主題的展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克萊夫·貝爾認為:“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的關系,激發我們的審美感情。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視之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藝術的共同本質。”②形式所具有的視覺沖擊在畫面的構成中直接表達主題,但也可以是一種深層次的表達。在《黑社會》系列中暴力的展現不僅僅是視覺沖擊的元素,更是對影片主題的表達。
杜琪峰的《黑社會》系列給我們帶來了一場視覺盛宴的同時要求我們對影片進行深層次的挖掘,這也正是影片的意義所在。正像杜琪峰導演所說的:“拍黑社會,我表達的是歷史發生的事,已不單純是一個江湖那樣簡單,是香港人的事,也可以代表我的看法,有的事情就是這樣,用真正的法律觀點去解決是解決不了的。”③《黑社會》系列為我們展現的不僅僅是黑社會組織的發展歷程,更多的是將邊緣的黑社會與現今社會的現狀進行對比,在對比中讓我們對秩序的理解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在輪回中對生命的意義進行思索。盡管杜琪峰在一定程度上闡釋了他所理解的人生哲學,但對于解決的方法及其出路并沒有指出。優秀的電影可以給人們以警醒,但一部好作品不應該僅僅只是指出問題的所在,重要的是給我們帶來希望,揭示解決問題的路徑。
注釋:
① [美]大衛·波德維爾、克莉絲汀:《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彭吉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頁。
② [英]克萊夫·貝爾:《藝術》,周金環、馬鐘元譯,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
③ 杜琪峰、吳晶:《時代的影像者、影響者——杜琪峰導演訪談錄》,《當代電影》,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