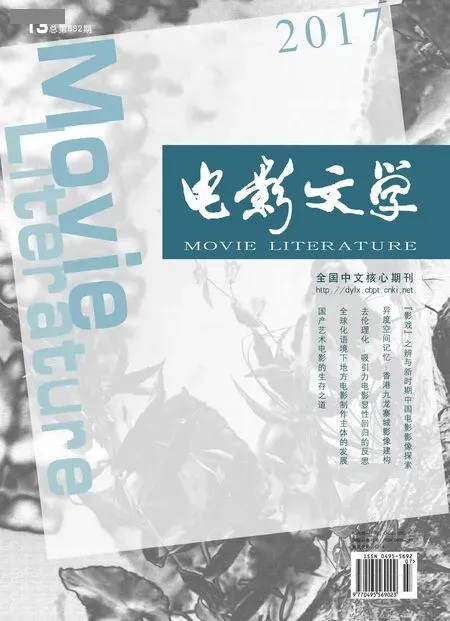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海街日記》的人性詮釋
張亞敏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外國語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日本電影擅長反映人生的情感與傷痛。尤其是在當代題材的電影中,日本電影人不斷展現著他們對人應有的個性自由,以及對日本社會的思考等。是枝裕和是當代日本電影的中堅力量,其自1995年以《幻之光》(Maboroshinohikari,1995)出道之后,其電影就一直關注著人的生與死、愛與恨等永恒的話題,在討論這類普世性的問題時,是枝裕和又注重影像中始終貫注著日本文化意味,就形式而言,其鏡頭語言始終保持著從容不迫的姿態,這一切使其整個影像敘事過程既包含了真摯動人的深情,又有著某種置身事外的節制和冷峻。《海街日記》(UmimachiDiary,2015)是是枝裕和的新作,在第40屆多倫多電影節中與賈樟柯的《山河故人》(Mountainsmaydepart,2015)意外地形成了一種默契的對應與互文。與《山河故人》相同,《海街日記》的亮點也在于導演對人性進行了屬于自己(甚至可以說是屬于自己國家)的詮釋。
一、《海街日記》中的人性定位
在討論《海街日記》的人性定位之前,我們對于是枝裕和電影人性闡釋的背景,有必要給予一定的關注。是枝裕和的成長階段正是日本社會開始奉行一種平均主義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經濟獲得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恢復期。這種社會狀況反映在藝術中,就體現為日本人開始熱衷于探討個人化的生命感悟(而早期的日本電影更多的是討論一種東方的人倫義理),這種對普通人的關注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了頂峰。這一時期日本出現的大量倫理電影或犯罪電影都展現了一種被異化、被扭曲的人性,基于對人的關注來創立情狀,關心當代人內心深處的孤獨。而同樣是表現對個體生命、對人性的關懷或審視,還有一部分導演則選擇了一種更為柔軟、更富溫情的方式。如女導演河瀨直美、西川美和等,這批導演并不執著于“另類題材”,而是堅持著某種“感動物語”的藝術風格。是枝裕和也是其中的一員,其早年的電影《距離》(Distance,2001)和《無人知曉》(NobodyKnows,2004)盡管來自于真實、殘酷的日本新聞,但是枝裕和都有意對題材本身進行了“去批判化”的處理,即相對于通過此類事件來抨擊日本社會的痼疾,是枝裕和更愿意挖掘其中普通人的生存經驗和細膩的人性情感。面對個體生命令人扼腕的凋零時,是枝裕和不是給人們敲響警鐘,而是低聲吟唱一曲柔和的挽歌。
相對于《距離》與《無人知曉》而言,改編自漫畫的《海街日記》中的批判意味和政治色彩更為淡化,這也使得是枝裕和能夠有更大的空間來以他所擅長的方式展現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體驗和感悟,并在娓娓道來中,表達導演本人對于人性的理性思考,并以此影響觀眾的生活方式。
《海街日記》中,最關鍵的理想人性便是善良和寬容。四姐妹相逢的背后實際上有著家族的悲劇:父親在多年前與情人私奔,母親不堪重負將三個女兒留給姥姥,而父親的情人在生下女兒淺野玲后也離開了這對父女,父親后來續弦,前不久病逝。三個姐姐在前去山形參加父親的葬禮后,邀請15歲的小妹妹淺野玲來臨海古都鐮倉和自己一同居住于姥姥的老房子里。在電影中,大姐香田幸被妹妹們公認為最像已經去世的姥姥。對于她們身處的這座老房子,幸也有自己特殊的情愫(不會像三妹千佳一樣開玩笑說要去住公寓)。庭院中有一棵55年前姥姥種下的梅樹,樹下還種著洋水仙等各種植物,這些日常都是靠幸打理照料,這是與幸護士的身份相吻合的。幸曾對妹妹們轉述過姥姥曾經的話:“要除蟲要消毒,活著的東西是很費功夫的。”這種對于生命的關愛,實際上便是幸能夠帶著充分的善意接納淺野玲進入自己生活的前提。盡管前一輩人曾經犯下的錯誤對她們造成了傷害,但是她們依然彼此關愛,對他人原諒多于怨恨,鼓勵多于傷害。
四姐妹的鄰居、本地著名飯店“海貓食堂”的老板娘二宮女士在電影中是一個出場不多,但是有著重要作用的角色。她與四姐妹中的三個人都分別有過接觸:在幸工作的醫院看病,接受佳乃和上級的資產詢問,以及在店里招待淺野玲和她的同學們。甚至在電影中作為節點的三大喪事中,其中一個就是屬于她的。這個配角人物身上同樣體現出了善良與寬容的人性。她的弟弟極為無賴地侵占了她的財產,但是對此她沒有一句怨言。在二宮女士知道自己病危時,也沒有選擇立遺囑來避免自己的財產落在弟弟的手上,欣慰的便是自己的拿手菜還會被好朋友傳承下去,因為弟弟“總不會連菜譜也拿走吧”。對于二宮女士而言,所有的抱怨和恨都只是自我消化,用親情和善意去盡量化解。正是四姐妹以及二宮女士等人性閃爍著光輝的角色的存在,世界得以更為美好。
二、《海街日記》中的人性撫慰
《海街日記》以一種“日記”的方式展現了四姐妹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活,然而也正是在這種平淡的生活中,四姐妹完成了各自的成長。是枝裕和對于電影中的四位女主人公都賦予了善良、包容的正面人性定位,四人結下的純真情誼點亮著彼此的人生旅程。但另一方面,是枝裕和也充分地體現了她們的人生困境,尤其影片的主要視角是置于淺野玲身上的。觀眾與淺野玲一樣都是對這座鐮倉小屋行感新鮮的外來者。與三位已經成年的姐姐不同,淺野玲在影片中的成長除了有一種外來者的窘迫、怯弱外,還伴隨著某種青春疼痛。但是,是枝裕和對于每一個人的困境都不遺余力地給予了人性關懷,并在影片中設置了帶有撫慰意義的意象。
從表面上看,四人善良、樂觀,擁有各自較為穩定的事業和學業,雖然失去了長輩的庇護,但四姐妹在鐮倉的老房子相親相愛,享受著鐮倉緩慢的生活節奏,與鄰里關系也極為融洽。但是四個人其實都各有心結,長姐香田幸的弱點在于,因為父母過早地缺席,她迫使自己提前成為一個“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妹妹們的同時,對她們又總有著過多管教,因此被二妹佳乃稱為“女生宿舍的管理員”。佳乃不愿意看到大姐依然保留著對父母的怨念,用常常和大姐斗嘴的方式表現自己對大姐的心疼,但是在洗澡遇到蟑螂時第一時間求助的還是大姐;三妹千佳在父親離去時仍然沒什么記憶,想向淺野玲詢問父親的細節又恐惹姐妹傷心;而小妹淺野玲則因為自己的身份生活在歉疚感中,曾經代替自己的母親向大姐道歉,說:“畢竟喜歡上有婦之夫就是不對的吧!”這種歉疚感也使得她雖然好奇父親曾經在鐮倉的生活,卻也不敢詢問大姐。
電影以多個意象表達了對四人的人性關懷與撫慰。以空間為例,海邊的鐮倉便是一個充斥著各種記憶的美好意象。這里人不多,但是有海貓食堂保留了20年的美味定食,有漫天的櫻花,有姥姥種植的梅樹,沖刷人們內心隱痛的大海、繡球花和紫薇花等。種種美好或是寄托著姐妹們對前人的懷念,或是隱含了她們對彼此的珍貴回憶。
葬禮儀式則成為一個帶有時間意味的意象。葬禮是日本電影中常見的審美場景,“死亡促使人沉思,為他的一切思考提供了一個原生點,這就有了哲學。死亡促使人超越生命的邊界,臻求趨向無限的精神價值,這就有了倫理學。當人揭開了死亡的奧秘,洞燭了它的幽微,人類波瀾壯闊的歷史和理想便平添了一種崇高的美,這也就有了死亡的審美意義”。在《海街日記》中,四人的相遇和投契、對彼此的維護都表現在葬禮中,是枝裕和有意祛除了葬禮悲慟的一面,而是讓四人(以及觀眾)在葬禮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如姐妹們慶幸父親和二宮女士都是在看完盛開的櫻花后才死去的。
三、《海街日記》中的人性成就
如前所述,相較于部分導演熱衷于在電影中表現人性“破”的一面,即人不滿于陳規或社會制度而做出的種種叛逆、破壞行徑,是枝裕和所考慮的則是如何“立”。只是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敘事往往是溫柔悠長、矛盾性不足的,這使得觀眾有時很難從平淡無華的情節中看到主人公的轉化或蛻變。而事實上,紀錄片導演出身的是枝裕和極為擅長在表現平淡生活的真實性的同時不露聲色地構建出一種戲劇性。在他的電影中,主人公往往可以實現從淺層到深層各類目標的轉變,以及一種積極向上的“自我實現”或對他人的幫助。而在人性上的完善、成就,也是屬于這種自我/他者實現的一部分。
在《海街日記》中,由于電影中最大的戲劇沖突實際上便是四姐妹的人性實現過程,因此電影故意使敘事碎片化了,避免其余沖突在吸引觀眾注意力上壓倒這一主干。在電影中,人物之間沒有發生過激烈的爭吵,一旦人與人出現矛盾,這種矛盾或迅速被轉移、中止,例如,在幸斥責母親“有什么權利讓我們賣房子”的時候,姨姥姥很快就喝止道“都不要吵了”,然后將話題轉移到姥姥的死上來;或是隨著鏡頭讓觀眾感受到它已很快被時間或其他事件沖淡,如當佳乃責備幸喜歡的有婦之夫荒井先生借口妻子有病而拒絕離婚和幸在一起,認為他是一個和她們父親一樣懦弱無能的人,幸為心愛的人辯解道:“你們什么都不懂!”隨后起身離去,但很快在淺野玲的干涉下,佳乃就讓自己喝了酒,走進大姐的房間跟大姐說些暖心的話,并撒嬌得到了大姐最喜歡的“勝利服”,剛才劍拔弩張的氛圍迅速轉為溫馨。
電影中多次出現的青梅意象實際上便是是枝裕和對于人性成就方式的一種闡釋。影片曾借助母親之口來贊嘆姐妹們對于青梅的處理方式,并且反復表現了姐妹們摘果、釀酒的場景。當梅樹結果時,如果人們不加采摘,它們便自行落地腐爛,而如果采摘之后單純用來食用,則很快便會吃完。四姐妹秉承著自姥姥傳承下來的做法,將部分青梅送給鄰居,部分青梅用來釀成不同口味的酒,封存在地板下,每當遇到各種令人憂傷或開心的事,就取出酒來享受前輩饋贈的微醺。這種做法有著豐富的藝術內涵,它一方面本身就極具審美效果;另一方面,它再次地呼應了是枝裕和對理想人性的定義,分享這一行為就意味著善意,以釀酒的方式延續青梅的美味也是一種對生命的珍視。如果說對青梅的護理、采摘和釀酒是一種隱喻式的、總述式的人性實現書寫,那么對于四姐妹各自的人性成長,是枝裕和還做了更為明朗的、分述式的介紹:市民醫院在郊區新建了一個臨終關懷分院,二宮女士便是選擇在這里走完了她的人生。而大姐幸也在最后選擇了來這里工作。這既是對之前與荒井先生那段無果的愛情的一次了解,同時也是幸在人性上的一次自我成就;佳乃和同事在發現二宮女士的悲慘命運之后,開始商量怎樣盡可能地用公立遺囑等法律手段來維護她的利益,他們堅信的是:“神明不能為她考慮的話,那就只能我們來了。”他們做這些職責之外的事情,純粹是出于不求回報的善意,這便是佳乃在人性上的自我實現。千佳在電影中著墨較少,電影中最后展現的是千佳與因登山被凍掉腳趾的店長感情有了進一步發展,而淺野玲也對同樣有著心結的男同學給予了友愛。
綜上,是枝裕和在《海街日記》中,并不旨在表現今日日本現實的一個側面,而是以一個帶有夢幻色彩的故事吸引觀眾去審視這個并不完美的世界,從而創造一種更遠離丑惡、更接近完美的新生活。電影在以明麗清新的畫面滿足了觀眾視覺感官愉悅的同時,又以其對人性問題的詮釋,在精神上不斷觸動、啟發著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