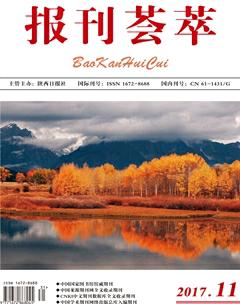西方媒體對上海城市形象的刻畫
彭瑩
摘 要: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方法,對《紐約時報》2000~2014年中涉及到上海的報道進行研究,對所收集的資料分別從定量和定性角度進行高頻主題詞和編碼分析,總結出西方媒體“塑造”的上海形象呈現出怎樣的特點以及上海城市國際形象傳播策略是否成功,從而得出如何將上海打造成一個強符號,這對上海“自我塑造”國際城市形象有政策性的建議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上海;城市國家形象;紐約時報;內容分析法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城市形象是人們對城市的主觀印象,是通過大眾傳媒、個人經歷、人際傳播、記憶以及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從國家的角度來講,城市形象是國家形象的組成部分,是重要的軟實力以及社會資本。[1]過去的研究中,有的將城市形象的研究對象設定為城市宣傳片,有的將研究背景設定為全媒體,有的通過整體傳播策略研究來試圖找出上海城市形象的定位,以觀察和歸納方式為主,缺乏具體數據,較難起到指導作用。[2]在當今媒體化高度集中的世界,西方的強國掌握了全球媒介系統,進而影響了媒介信息的傳播內容與方向。我們知道《紐約時報》是美國歷史最悠久、流程最完備的報紙,其國際新聞居美國報紙之首,被譽為“權力機構的圣經”和“檔案記錄報”。[3]
基于《紐約時報》的廣泛影響和傳播,《紐約時報》所塑造的中國城市形象的實證研究也越來越多。在討論《紐約時報》對深圳報道的文章中,作者采用內容分析法,通過對98篇樣本進行文本分析得出,《紐約時報》著重從“經貿”、“政治”、“對外交流”三方面詮釋深圳形象,這與深圳改革開放以來所呈現的特征基本保持一致。但是,上海同樣是中國城市中最具國際化特征的城市之一,卻很少有研究是討論《紐約時報》對上海城市形象塑造的。[4]
本文主要考察《紐約時報》媒體在報道上海時的傾向性(正面,中性,負面)和報道主題是怎樣的,分析出西方媒體“塑造”的上海形象呈現出怎樣的特點。本文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從而得出如何將上海打造成一個強符號,這對上海“自我塑造”國際城市形象有政策性的建議和現實意義。
二、樣本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紐約時報》2000年——2014年關于上海15年的報道。通過Proquest數據庫中的報紙資源,獲得《紐約時報》15年間關于上海的報道,檢索以新聞標題中含單詞Shanghai為準。據此,獲得研究樣本182篇。分析的單元為單篇新聞報道,對文本做內容上的二次篩選,把文章的著眼點不在上海議題的新聞報道排除于樣本之外,得到有效樣本179個。
研究方法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所收集的資料分別從定量和定性角度進行高頻主題詞和編碼分析。首先對文本材料抽取10篇進行人工編碼,即試編,通過信度檢驗后,再對所有的報道按照編碼表統計類目數據。
三、基本研究數據分析
1.報道傾向分析
從整體報道量看,《紐約時報》對上海議題的關注從2007年開始波動很大。波動原因是,對2008年的股市風波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進行了集中報道。除去這些波動的年份,對上海的每年報道量是在9篇上下波動,并沒有出現只有個別報道的年份,可見其對上海的關注力度并沒有減小。
而從報道傾向統計上看,194份關于上海的報道樣本中正面報道的篇數達到91篇,占47%;中性報道的篇數達到56篇,占29%;負面報道的篇數達到47篇,占24%。
從每個二級議題的報道傾向來看,負面報道主要聚焦于重大事故與重大事件、反復及腐敗的報道和勞工與人口問題這些議題,正面和中性的報道主要集中在旅游、文化建設、國際賽事、城市發展和經貿活動與金融市場上。可見,《紐約時報》對上海的報道總體上看,負面報道較少,大部分是正面報道,特別是在經濟化、城市化和國際化上《紐約時報》是持有支持和承認的立場。
2.議題框架
媒介框架是一種建構的過程,《紐約時報》在建構上海形象時必然會選擇特定主題、材料來設定報道框架,從而建構公眾對上海這座中國城市的認知。統計所屬的報道的一級主題并歸類制圖可以發現,文化報道(旅游、文化建設、餐飲酒店、國際會展、教育)以98篇的報道量占報道總量的最大份額,達到51%;經濟和社會的報道并列第二,占報道總量的12%;政治的報道占報道總量的9%;城市發展的報道占總量的8%。總的來說《紐約時報》對上海采取全方位關注,上海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由此可見。
3.報道熱點內容分析
關于上海報道的主要主題(二級標題)框架可以分為以下15類:反腐及腐敗報道、政治體制改革、金融市場、經貿活動、旅游、文化建設、餐飲酒店、國際會展、教育、重大事故與事件、勞工與人口、治安、城市發展、交通、國際關系。
對國際會展和賽事的報道最多,達到33篇,主要有“上海大師賽”和“上海世博會”等;關于文化建設的報道有22篇,聚焦于“上海為市民舉辦的各類文化活動”和“國外人眼中的上海市民形象”;旅游的報道有22篇,主要報道了“外國人在上海旅游”和“上海迪斯尼”;城市發展的報道關注點在“上海建筑的歷史風格”和“上海政府的城市規劃”;另一個關注熱點是上海的經濟方面,金融市場的報道13篇,經貿活動的報道11篇,內容涵蓋上海逐步向外資開放的證券市場和與國外合作的經貿活動,也談到了上海和香港各方面的關系;《紐約時報》對上海政治的關注也很多,總共達到18篇,主要是官員的腐敗問題(特別是上海前市長陳良宇的腐敗報道)和中央對上海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4.高頻詞匯分析
基于認知圖示的形象理論模型(SIT),從媒體的報道中可以提取與認知圖示類似的詞匯模式,它透露出媒體選擇了哪些屬性來表征一個國家或地區。
在上海形象的高頻特征詞中,可以將上海的內容信息歸納為以下3個主題:關于地名的(“中國”、“北京”、”紐約“、“美國”等)、關于經濟的(“公司”、“市場”、“股市”、“出口”、“投資”、“貿易”、“金融”、“銀行”等)、關于國際化的(“世界”、“開放的”、“西方的”、“外國的”等)。
由此可見,上海形象以國際化、經濟和文化為主,總體形象報道相對均衡。值得一提的是,完全沒有出現“綠色”、“信息化”、“創新”之類的抽象字眼,也沒有任何與之相關的報道,這一點是值得反思的。顯示出了上海目前自身定位和推廣與《紐約時報》的關注點還是具有一定的差異,這對城市形象的經營也會有影響。
四、小結與研究局限
通過分析《紐約時報》2000年—2014年關于上海的新聞報道,可以得出,上海是一個國際化、經濟化、文化的大都市。因此,在上海發展和維護形象的過程中,應抓住本質特征和不可替代性,以持續、多方位、境內外媒體和意見領袖相結合,官方和民間相結合,國際主流媒體和意見領袖相結合的方式,繼續保持西方媒體對上海正面報道的方面發展,加強改善那些對上海持有負面評價方面,完善城市強符號的打造,提高上海乃至中國的國際形象。
本研究存在難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一,在收集數據時,只是在檢索中的標題中搜索“上海”,《紐約時報》關于上海的報道,不一定每篇的標題都顯示“上海”。雖然抽取標題中含有“上海”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總體,但是也不能忽視這可能會帶來樣本偏差。第二,樣本的時間維度可能不夠長,上海的發展過程并不是這十五年就能解釋的,所以《紐約時報》2000年前的報道有必要進行研究,與最近十五年可以做對比,可能會發現一些“變化”。第三,內容分析法本身存在的弱點,許多指標是相對主觀,如報道內容的傾向性是正面或負面,而且編碼員的主觀偏差很難避免。
參考文獻:
[1]范勇.《〈紐約時報〉涉華報道對中國特色詞匯翻譯策略之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82-87+128.
[2]葛巖,趙海,秦裕林,陳長閣,何俊濤,徐劍,盧嘉杰,李曉靜.《國家,地區媒體形象的數據挖掘——基于認知心理學與計算機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視角》,《學術月刊》,47(2015),163-70.
[3]劉佩.《〈紐約時報〉涉及深圳報道中的意識形態與“深圳形象”的建構——以〈紐約時報〉30年涉深報道(1980~2010年)為例》,《中國出版》,(2013),62-65.
[4]宋國強.《中國城市的國際媒體形象》,(碩士,上海交通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