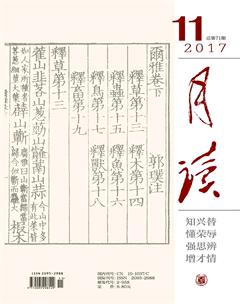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
唐虞尚仁b,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quán)c,驅(qū)赤子于利刃之下,爭寸土于百戰(zhàn)之內(nèi)。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zhàn)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由是編之為術(shù)d。術(shù)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
蚩蚩之類e,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于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f,后啖以利哉g?
孟子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大罪也。”h使后之君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為猶士焉。
(《全唐文》)
注釋:
a 《司馬法》:我國古代一部講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軍事著作。據(jù)《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hào)曰《司馬穰苴兵法》。”后來將《司馬穰苴兵法》簡稱為《司馬法》。司馬穰苴是春秋時(shí)齊國大夫,姓田,名穰苴,官為司馬。他精通兵法,善于打仗。
b 唐虞:指唐堯、虞舜,是上古時(shí)期兩位圣明賢德的君主。
c 尚權(quán):崇尚權(quán)力,注重權(quán)術(shù)。
d 術(shù):這里指軍事著作,不專指《司馬法》。原文中注為:“謂《太公六韜》也。”
e 蚩蚩之類:指被迫打仗的百姓。
f 紿(dài):同“詒”,欺騙。
g 啖:這里是引誘的意思。
h “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大罪也:語出《孟子·盡心下》。孟子主張仁政,反對戰(zhàn)爭。這里他引用一個(gè)好戰(zhàn)君主的話,并認(rèn)為好戰(zhàn)善戰(zhàn)是一種罪過,應(yīng)該受到懲罰。陳,通“陣”。
大意:
古代取得天下依靠的是百姓的民心,如今取得天下用的是百姓的性命。
唐堯、虞舜崇尚仁愛,天下百姓順從他們而擁戴他們?yōu)橥酰@不就是說依靠百姓的忠心而取得天下嗎?漢、魏崇尚權(quán)勢,驅(qū)使百姓到刀光劍影的戰(zhàn)場,為爭奪一寸土地而不惜打上百次的戰(zhàn)爭。他們從士成為諸侯,從諸侯成為天子,不使用武力不能顯示他們的威勢,不進(jìn)行戰(zhàn)爭不能使百姓屈服,這不就是說用百姓的性命來取得天下嗎?
由此將這些戰(zhàn)爭經(jīng)驗(yàn)編寫成軍事著作,戰(zhàn)術(shù)愈精通則殺人越多,戰(zhàn)法越實(shí)用則危害萬物越厲害。唉!這真是沒有仁愛之心啊!
被迫打仗的士兵打起仗來不惜自己的性命,首先是懼怕刑法,其次是貪圖賞賜。百姓對于君王來說,就像是兒子。君王這樣做,與父親想要?dú)⒑ψ约旱膬鹤樱扔猛萜垓_,后用利益引誘,有什么區(qū)別嗎?
孟子說:“‘我善于布陣,我善于打仗,這種說法是最大的罪惡。”假使后代的君王對待自己的子民有孟子這樣的態(tài)度,即使沒有得到士人之心,我認(rèn)為也等于得到了士人之心。
【點(diǎn)評】
皮日休是晚唐著名的詩人和文學(xué)家,與陸龜蒙齊名,世稱“皮陸”。這篇文章雖為讀兵書有感,但作者并非討論這部兵法的具體得失,也不是從軍事科學(xué)的角度對其予以評價(jià),而是從更高的層次上談民心與國家統(tǒng)治的關(guān)系問題,這對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有著強(qiáng)烈的針砭意義。皮日休生活的晚唐時(shí)期,藩鎮(zhèn)割據(jù)日益嚴(yán)重,干戈頻繁,民不聊生。連年的戰(zhàn)亂已經(jīng)成為唐末百姓生存的最大威脅。早日結(jié)束這些因爭權(quán)奪利而引起的戰(zhàn)爭,是當(dāng)時(shí)百姓的共同愿望。皮日休繼承了孟子“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孟子·盡心下》)的思想,主張君主應(yīng)該實(shí)行仁政,贏得民心,如此便可以獲得天下。縱觀全文,作者的側(cè)重點(diǎn)其實(shí)不在于反戰(zhàn)或否定《司馬法》一書的價(jià)值,而是譴責(zé)統(tǒng)治者驅(qū)使百姓征戰(zhàn)而不顧其死活,為的卻只是自己的私欲和利益,也就是說此文的主旨是在宣揚(yáng)仁政和以德治國,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