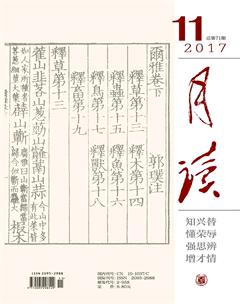村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
萬壑有聲含晚籟,數(shù)峰無語立斜陽。
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xiāng)。
(《小畜集》)
【品讀】
題為“村行”,相當于村游,大約也算不得游,也就是閑來無事到處走走。王禹偁村行不徒步,是騎馬走。“馬穿山徑”,可見是山村。“菊初黃”,可見是初秋時令。“信馬悠悠”,則完美呼題。“野興長”,一來證實先前走來所見山徑菊黃的好景致,二則引出下文更為唯美的山村秋意圖:千溝萬壑,回蕩晚籟聲聲;數(shù)峰無語(錢鍾書《宋詩選注》里講,“數(shù)峰無語”才不是一句不消說得廢話,其是以“反”為“正”,用“無語”來講山峰并非無語而“無語”,仿佛原先是能語、有語、欲語而此刻忽然“無語”的。倘若改成“數(shù)峰畢靜”,意味就削減了),有夕陽斜上山崗;棠梨(即杜梨,一種落葉喬木,春夏葉綠,秋來則泛紅,所結(jié)果子亦是紅的)葉落,緋若胭脂;蕎麥花開,則似雪飛香。山徑、萬壑、數(shù)峰;黃菊、紅葉、白花,此番種種組成的明麗盛景,不單使作者“信馬悠悠野興長”,亦令讀者閱之陶然,且生出無限的向往。
作者走筆至此,讀者著眼至此,皆興味高漲,美不勝收。
不意,作者猛地筆鋒急轉(zhuǎn),突兀來一句莫名自問:“何事吟余忽惆悵?”在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之時,緊接又來一句篤定自答:“村橋原樹似吾鄉(xiāng)。”通篇至此,戛然而止,唯留下讀者執(zhí)卷低回,悵嘆不已——卻原來,卻原來,王禹偁信馬村行,觸景生情,想家了。
有些詩,乃至有些文章,起頭看來,覺其平平,看過一半,仍覺平平,再往下看,還覺平平,就在人興味漸淡時分,煞尾之處,兜頭給你來一瓢,或一棍,叫人一下驚然、豁然、爽然,再復(fù)啜之前所謂“平平”的鋪陳,原來是那樣的意味深長。這樣的筆法,才叫功夫。王禹偁此一《村行》,讀來大有此等功力。
說起王禹偁,怕又要叫人悵嘆了。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在今山東)人。出生在一個世代為農(nóng)的家庭,且家境甚貧,以磨麥制面為生。少即聰慧,三十歲中進士。然仕途走得并不順遂,雖曾歷任右拾遺、左司諫、知制誥、翰林學士,其間卻三貶三入。此一《村行》,即作于初次被貶商州(在今陜西)的次年。如此看來,他那“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xiāng)”的心情,就很好理解,也不難體會了。
說起三貶三入,王禹偁的命運與其后輩蘇軾倒有幾分相似。蘇軾曾被一貶黃州,再貶惠州,復(fù)貶儋州;王禹偁則被初貶商州,復(fù)貶滁州,又貶黃州。蘇軾最后死在了赦免回鄉(xiāng)的途中,王禹偁則病故于貶地蘄州(今湖北),年僅四十八歲。蘇軾《王元之畫像贊并敘》云:“……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徵、狄仁杰)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于眾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余烈,愿為執(zhí)鞭而不可得……”蘇軾這番話講來,是情切切意切切,真乃英雄惜英雄之語!(楊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