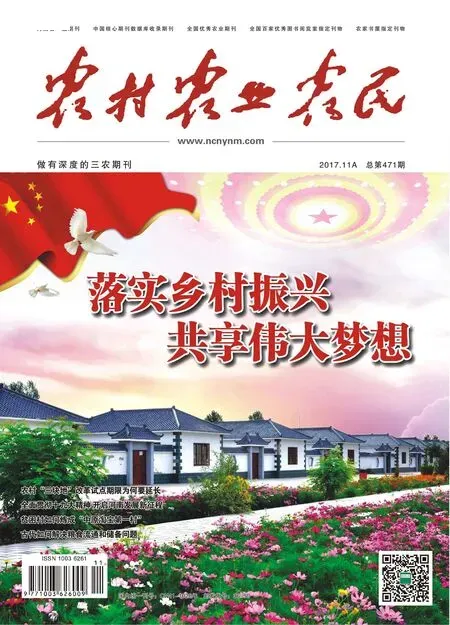城市與鄉村應融合互補加速建設“人的新農村”
劉彥隨
城市與鄉村應融合互補加速建設“人的新農村”
劉彥隨
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而我國“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立體的鄉村地域系統可持續發展問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為新時代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
都說城市化伴有“城市病”,殊不知鄉村也有“鄉村病”,但二者有本質不同。前者是在快速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后者是在逐漸衰落過程中產生的。兩種病都得治,但“鄉村病”更為緊迫。早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家園。
城市與鄉村血脈相融、地域相連,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然而,長期受“城市優先”戰略的影響,城市不斷擴張,經濟快速增長,農民就業重在推進離鄉進城和非農化轉移,鄉村功能重在強化社會維穩和農民生計安全保障,導致傳統農業結構長期得不到改造、現代農業功能普遍得不到健全。

資料圖
這樣的情況就導致鄉村僅僅是為了服務于城市,農業僅僅是服務于工業。我國傳統體制的“三分”(城鄉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離)弊端日益暴露,“三差”(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階層差異)問題不斷加大,這些都成為困擾當代中國“三轉”(發展方式轉變、城鄉發展轉型、體制機制轉換)的重要難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而不是往常講的城鄉統籌,恰恰體現了觀念上的重大轉變。
我國當首先致力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落實鄉村興人、興地、興權和興產業,有效激發鄉村活力、能力、動力和競爭力,系統推進城鄉融合、協調、一體和等值化。當前,我國正處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時期,政府需要同步倡導城市化和村鎮化,形成村鎮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
事實上,近10年來,國家對鄉村建設的支持力度從未消減。我國針對農業農村發展問題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有些鄉村問題始終未得到系統考量和有效解決。其深層問題歸結為“五化”,即農業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農民社會主體過快老弱化、村莊建設用地日益空廢化、農村水土環境嚴重污損化,以及鄉村貧困片區深度貧困化。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鄉村衰落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失。僅在2016年,我國約有1.7億農村人口離開家鄉來到城市。有關團隊經過多年實證研究發現,尋找工作和增加收入是他們進城的主要原因。在1990年至2014年間,我國農村的工作崗位減少了20%以上。
相比于鄉村,城市工作的薪酬更高。
十八大以來,我國在農民工融入城市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就。尤其在大力鼓勵和支持農民工返鄉下鄉創業方面,據農業部最新統計顯示,我國各類返鄉下鄉創業人員已達700萬人,其中返鄉農民工比例為68.5%。
但不容忽視的是,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科技、衛生、文化等公共資源投入少,導致農村人口素質偏低、人才缺乏。鄉村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健康發展,只有農民自身素質和能力的不斷提升,才能有效推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鄉村振興既要注重物質投入的硬件建設,更要重視提高鄉村人口素質的軟件建設,包括鄉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就業培訓、培智扶志等。
新時期亟須建立全覆蓋的鄉村教育培訓體系,健全國家管治、城鄉同治、村民自治的多層次鄉村治理體系。要加快建設“人的新農村”,提升民眾自覺學習意識、創業意愿,培養造就適應現代農業發展、新興產業振興、美麗鄉村建設要求的新型職業農民。
對此,十九大報告中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論述提出了“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引發了業界的強烈關注。
土地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然而,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帶來了大量優質耕地的流失。同時,因耕地分散、細碎、小規模,農田基礎設施不配套,導致耕地利用率低,一些地方有地無人耕、良田被撂荒已成為一種常態。針對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間散亂的問題,圍繞土地資源利用高效化和土地空間利用有序化目標,亟須科學開展推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有序推進鄉村地區組織、產業、空間“三整合”,加大對農村投資傾斜力度、內需拉動強度,塑造中國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新動能、新機制。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