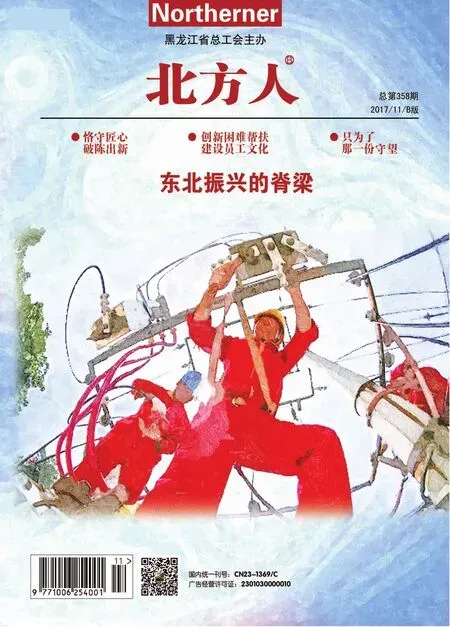藝術火炕
文/聶孝明
藝術火炕
文/聶孝明

我打小生活在東北林區,可以這么說,處在那個年代生活著的人們,都住平房(泥草房),睡火炕。直到35歲之后,才搬到城里住床。
如今搬到城里二十多年了,再沒有睡過火炕。
我有這么一個感覺,仿佛睡火炕的時候,沒有腰痛過。也許是那個時候年輕火力旺?還是火炕暖腰?對人體有保健作用?我在城里也試著睡“地熱”,它可沒法和火炕比,睡“地熱”簡直是活受罪,熱的你直打滾受不了,根本找不到睡“火炕”的那種感覺……
要說睡火炕,我從小到大,包括輾轉搬家睡過好多好多火炕,在朝陽川、在白林、在神樹、在青年農場,甚至“找宿”。
以前睡過的火炕,雖然也很舒服溫暖,但大多數都是“直筒著”樣式的火炕,即灶坑點著火,直通大炕,千篇一律,典型的浪費。稍微精明一點兒的人,往往火燃盡了,把灶坑用木板堵死,或者有的人家,用“插板”插上,這就不錯了……
過日子,一般情況下,一家都是兩口鍋,一口大的,一口小的,大的燜飯,小的炒菜。兩口鍋灶直通大炕。
我在彈丸之地山鄉石長居住的那幾年,睡過的那盤火炕,可以用“藝術”兩個字來形容。
現在想想,那個年代為什么睡火炕?一是因為冷,二是因為買不起也蓋不起樓房,沒有樓房,沒有“集體供暖”。
那時候,家家都沒有使用暖氣,除了兩口鍋做飯以外,還要在外屋(廚房)盤一個大磚爐子。此磚頭砌的爐子,要有“火墻”,“火墻”是兩面光、兩面熱,既暖了外屋又暖了里屋。
火墻的煙,單走,從屋里“火墻”上端,接好幾節爐筒子,在屋里空間穿過,再通炕煙囪。
靠火墻處的爐筒子低,逐漸升高到煙囪,爐筒子低矮處,不注意就會撞腦袋,“忽悠”一下,撞下來不少灰塵。這種取暖模式,幾乎家家如此。這一冬天下來,得燒掉好多好多能源。
還得說我在石長居住時候,燒的那個磚砌的火爐子,“火墻”、大炕、“一條龍”,不用一節爐筒子!屋里照樣暖和,室內還顯得美觀,“一條龍”節省能源不說,居住環境看著舒服,因為沒有那么多節“爐筒子”在屋子中央穿過,比較之下顯出了環境布置的“藝術性”。
睡火炕舒服是舒服,每年都要“扒炕”,即清掃炕洞里的煙灰。
后來,我想了個好辦法,不用年年“扒大炕”。我在“炕梢”,通往煙囪脖子處,把炕面掫開,把煙灰掏干凈,把磚塊照原樣子擺上,上邊揭掉的干硬“板泥”按著原樣子鋪上,在撒上沙子,不用抹濕泥,這就不用特意燒炕了,省心省力省柴火。上面鋪上纖維板,就那么干睡,不冒煙。
我在石長居住時那盤小火炕,一直熱到天亮,無論刮風下雨,不管外面什么環境,它都好燒!那小炕睡著是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