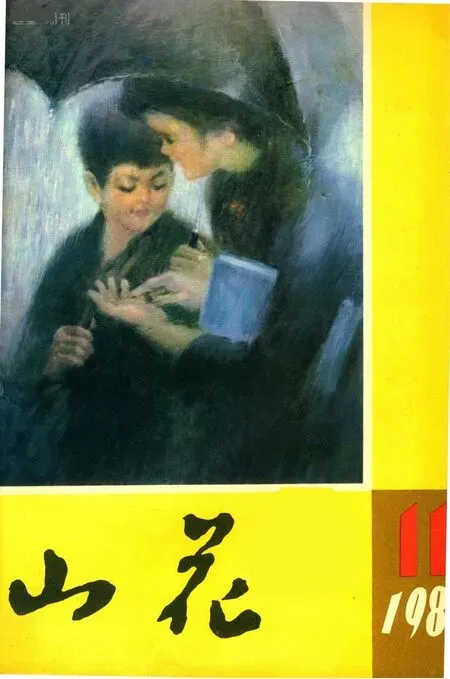以退卻的方式,他們獲得新的依傍
田一坡
《五人詩選》(雷平陽、陳先發、李少君、潘維、古馬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命名理所當然地包含著一種野心,一種為詩歌廓清前景與理清道路的雄心。它與三十多年前的那本《五人詩選》形成一種對峙與應和。198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人詩選》,選編了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五位詩人的代表作品,儼然成為一個時代的詩歌豐碑與詩藝標準。然而,86版的《五人詩選》更像是詩歌河流上的一道閘門,它使詩歌河流在八十年代顯得壯觀與喧囂,但它卻不可能像疏浚河流的河堤一樣規范詩歌河流的流向。詩歌河流終將泛濫,奔涌過這道閘門,漫向九十年代與二十一世紀。
詩歌終將改變,不僅僅基于自然時間的更迭、時代風氣的嬗變,更基于一種發生在詩歌自身中的詩寫經驗、態度以及寫作范式的轉變。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歐陽江河就在《89年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中敏銳地點出這種寫作中的代際斷裂,那是一次在已經寫出和正在寫出的作品之間所產生的一種深刻的中斷。一個寫作階段(八十年代后期詩歌)結束了,一個新的寫作階段不可避免地開始它那“不知所終的旅行”(程光煒語)。三十多年來,詩歌在學院、在民間、在網絡的眾聲喧嘩中經歷了曲折、繁蕪與野蠻的生長之后,一本新的《五人詩選(雷平陽、陳先發、李少君、潘維、古馬)》適時出現。這一次,它不再是河閘,而是矮下身來,在喧囂的詩歌河流之上,匍匐成一條河堤,隱約指向詩歌未來的遠景。
《五人詩選》的潛在目標是為新詩寫作重新厘清前行的道路,但這種厘清并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指指點點,而是以一種和風細雨的方式,甚至是一種退卻的方式。退卻,在《五人詩選》里,不僅僅是一種策略,更是一種詩學立場,以一種退卻的方式,他們在詩歌中退卻到經驗的地基之處,重新建立詩歌與現實、傳統、自然、地域和情感的關聯,使得詩歌在未來的前行有了新的依傍。
雷平陽的詩歌是向現實的退卻,在向生活細節的逼近中,他重新處理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也讓讀者重新思考詩歌與現實的關聯。詩歌面臨著一個極其嚴重的指控:當代詩歌脫離現實,脫離社會。這里的要害不在于這個陳述是否說出了當代詩歌的真實狀況,而在于許多閱讀者認為這個陳述是真實的,它形成一種詩歌閱讀的心理氛圍。許多不讀詩的人不讀詩的理由就是詩與現實脫節,但他們不讀詩又怎么知道詩與現實脫節呢?事實就是,他們雖然不讀詩,但是他們處在這樣一種認為詩與現實脫節的心理氛圍中。它就像一個流言,傳播開來,卻比事實真相更讓人“相信”。一旦閱讀者處在這樣的氛圍中,他會形成自己的閱讀判斷,而且,就算有很好的反映現實的詩擺在他面前,也不會糾正他的判斷。他仍然堅信:當代詩歌是與現實脫節的。面對當代讀者對詩歌的指責,詩人將如何應對?對于多數詩人而言,不理會現實,只是埋頭寫詩恰好是不現實的,他們必須在自己的詩歌里觸及現實,但詩人們真正具有詩學意義的轉變不是在自己的寫作中開始處理現實題材,而是體現在他們選材時方式的變化,他們變得更注重細節,并在細節的描敘中獲得詩對現實的理解與敞開。對細節的注重,似乎重新開啟了一條詩歌關注現實的道路。這種對細節的注重也反映在雷平陽的詩中,比如葉延濱對他的詩歌的評價:“雷平陽是一位逼近生活細節的詩人,比貼近更逼近自己生存的空間。因此,細節放大了詩人對生存狀況的感悟,同時也讓我們在閱讀中逼近了雷平陽的詩意世界,喚起我們對世界的詩意關注。雖然,這個世界從沒有失去過詩意。”在詩歌的細節中呈現出來的世界帶著大量的現實世界的信息,它試圖把閱讀者重新感召到詩歌的旗幟之下。比如他的《戰栗》,以細節的方式呈現了一個“鄉下的窮親戚”在工地的艱辛生活,當她在歷經辛苦后拿到工錢時,詩歌把她戰栗的手和戰栗的心都呈現在讀者面前,并讓讀者和詩歌中的“她”一起戰栗。又比如他的《殺狗的過程》,對一只狗被殺的過程進行了詳細而冷峻的描寫,一次未殺死,狗跑開,又跑回來,如是五次,在詩的末尾,詩歌提到了圍觀的人:“許多圍觀的人/還在談論著它一次比一次減少/的抖,和它那痙攣的脊背/說它像一個回家奔喪的游子”,在這樣的描述里,誰還可以說詩歌沒有生活,沒有現實?
事實上,幾乎每個人都有對于現實的認識,每個人心中都會生成“現實感”。閱讀者有現實感,詩人也同樣有現實感。所不同的是,一般的閱讀者以他們未經反省的現成的“現實感”為標準來要求詩歌,以前,當閱讀者的自我理解還有詩歌的參與時,他們的要求還是從詩歌內部發出的;現在,閱讀者的自我認同不再與詩歌相關,他們就只不過是從詩歌外部強加給詩歌以他們的要求與指責。而作為詩人來說,他們的現實感不是現成的,他們必須通過詩歌的寫作,在詩歌內部生成現實和詩歌的動態關系。他們首先能做的,就是純化自己從市俗生活中獲得的粗糙的“現實感”。在詩歌中他們表現為一種“退卻的方式”,也就是從日常的“現實”中退身而出,在習慣的“現實感”層層剝落,從而回到一種在詩人看來更為真實的現實中。比如雷平陽的《親人》,就表現了這樣一種退卻的詩歌技藝。“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它省/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因為其它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因為其它鄉我都不愛……//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繼續下去/我會只愛我的親人——/這逐漸縮小的過程/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這樣的現實,不再是誰從外部強加給詩的“現實”,而是從詩歌內部重新調適了詩歌與現實的關系并重新獲得詩對現實生活的發言權。這樣一種退卻的技藝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我們自身的現實經驗的純化與深化,伴隨這種現實的純化與深化的詩歌技藝自身的純化與深化,同時也是詩人在這一過程中對自身靈魂的自我看護與教養。通過這種退卻的技藝,雷平陽在“詩歌與現實”這一古老問題的新的處境中給出了一種更為有力的回應。
陳先發的詩歌是向傳統的退卻,這種退卻不是躲在傳統中緬懷古典余韻,而是古典的精魄在新詩中的轉化與重臨。正如趙飛所說,陳先發渴望恢復“道統”的“寫碑之心”如此迫切,托物、言志、載道的詩學理念都明確灌注在其寫作實踐中,每每用心良苦。但陳先發向傳統的退卻,不是那種皮與肉的臨摹,他在向傳統退卻的同時,卻輕易地脫掉了傳統的皮與骨,只保留下傳統的靈魂與那種一句成詩的沖擊力。陳先發的詩中便不乏那種一句成詩的力量。比如這樣的句子:“要阻止刀子從廢鐵中沖出來”,一下便把我哽住了,來不及深究它所想表達的和能表達的,這個句子已經扎到了心底。還必須小心護著,不然刀子便真的從廢鐵中沖出來傷人。又比如他《冬日的雀群》中的一句:寂靜把它們的心磨得發亮。這句其實平實得很,但如果你恰好在秋收冬藏的農村及他們的精神狀態里浸淫過,這句詩會向你展現它所有的魔力。它會聚集起你的全部鄉村經驗以及你對某種靈魂狀態的領悟,并且是如此的恰如其分。兩個句子展現了一句成詩的兩極:一極是詩句的不及物狀態,它打動人只是因為它本身。一極是詩句的及物狀態,它打動你是因為它所承載的人生經驗。恰好是在這兩極之間的張力中,陳先發自如轉換的詩句帶來一種語言的爆發力。比如《捕蛇者說》中:“蛇因懷疑不長四肢,它不分晝夜的/蛻皮僅僅出于對懷疑的迷戀。”蛇不長四肢,這是我們的經驗,“蛇因懷疑不長四肢”卻只能是詩的發明了。在語言的兩極間的自如穿梭為詩人帶來一種奇特的觀物方式以及對它的奇詭表達,這讓陳詩中充滿了極其繁復的一系列意象,它們既古典又現代,既現實又虛幻,既逼近事物真相又脫離事物真相。像他自己的詩句所寫的一樣,他的詩歌是如此輕易地脫掉了自己的骨頭。我把這看作是陳先發的詩藝所在。讓語言斬獲自己的頭顱,詩意也正是在這一斬首行為的過程與細節中逐漸得以呈現。這一艱難的過程,詩人卻干得如此“輕易”,真是叫人心生驚悚啊。當然,一句成詩的沖擊力畢竟是有限的,它必須在詩的整體結構中才能獲得持久的力量。陳先發在他的諸多短詩中展現的結構能力應該是能夠讓人服氣的。他不但有一句成詩的爆發力,也有在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營構開闊的空間的整合力。如他的《村居課》中,“他剝罷羊皮,天更藍了。老祖母在斜坡上/種葵花。哦,她乳房干癟,種葵花,又流鼻血。”種葵花,又流鼻血,可真讓人牽腸掛肚啊。
李少君的詩歌是向自然的退卻,這種退卻不是隱士歸隱于山林的獨善其身,而是在詩歌中重新激活自然對于現代人的心靈凈化;這種退卻不是在現代生活中臆造一方獨處的山水,而是把現代生活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然生活在其中;這種退卻不是一個人在語言的山水自然中消泯自身,而是要在山水、月光的殖民地之中做一個現代靈魂的自治者。李少君的詩歌,生動地展示了一個現代人將冷冰、狂躁的現代物象馴服為親切、溫順的自然物象的心靈修煉過程。現在,李少君作為自然詩人的面貌越來越清晰,他詩歌中的自然,親切、隨和、簡約而又透明。李少君詩歌中的自然、山水,仿佛觸手可及,但事實上,作為詩歌的一體之兩面,他詩歌中的自然有著幽暗與迷宮般的屬性,也恰好因為這幽暗與迷宮的屬性,他的自然才足以成為承托現代生活的根基。而這一點,恰好被許多評論者所忽略。詩人寫得較早的《麋鹿》一詩,很好地顯現了李少君詩歌中的自然的迷宮品質。
《麋鹿》想通過這些縱橫交錯的道路說出什么?或者說,在這些不斷找到又迷失的小路中,什么經驗被帶到我們切身的體驗中?“森林中有一條要迷路才能找到的小路。”這是一個已故的瑞典詩人說的。而這個詩人所說把我們帶向了森林的縱深。必須走到迷路之處,一些小路才向我們閃現。人迷失,又尋找。森林確實有著一種人世的象征,像但丁在人生中途的迷失。但這不是“霧失樓臺,月迷津渡”般人世的蒼涼,卻有著“山重水復,柳暗花明”般人世的幽深。“森林中有一條只有麋鹿才能找到的小路。”這是一個美少女說的。而美少女用想象把我們帶向了森林的更深處。更深之地,惟有麋鹿才能到達。人所不到之處,人唯有想象才能抵達。而少女以其美妙的想象引領我們進入森林更深處時,它抵消了森林所隱含的危險,因為想象的引領者乃是溫順而美麗的麋鹿。于是,麋鹿的道路既是對人的道路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糾纏:它既是對人的小路的更深的推進,但同時又以其幽深與溫婉消解了人的道路的危險、焦慮與彷徨。如果說詩人尋找的人的小路乃是人世的象征,那么,麋鹿的道路則只能是本然又純粹的詩(藝術)的象征。事實上也是,少女從本然上就接近詩藝本身。這樣說來的話,《麋鹿》想通過這些小路說的就不僅僅是對自然與人世的體驗,更是對詩歌本身的體驗。然而,在詩的第二節,找到的道路再次通向迷失。“林子里總有一條讓人迷失的小路。”作為寫詩的“我”說。“林子里總有一條讓麋鹿也迷失的小路。”美少女嘆息說。詩的第二節和第一節的對峙乃是解讀本詩的關鍵,它因此區別于詩中提到的詩人,也因此區別于美少女。因為《麋鹿》真正經驗的東西乃是在這道路的縱橫交錯中展現出來的:找到與迷失是道路的一種交錯:找到與迷失的交互關系乃是一種無盡的循環。不能因迷失而否認找到,也不能因找到而否認新的迷失。小路正是在這樣的找到與迷失的循環中越走越深。人的道路與麋鹿的道路形成另一種循環,就像人生和藝術所形成的無盡的話題。“我”與已故詩人也是道路的一種交錯,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少女對自身所形成的一種交錯感,它提示了一種接近藝術的敏感天賦是如何在對自身的否定中才得以真正走近麋鹿的道路。就這樣,《麋鹿》以其貌似清晰的精悍把我們帶入一種人世、自然與藝術的混沌的領悟中。
潘維的詩歌是向地域經驗的退卻,在這種退卻中,江南地理作為一種地域經驗逐漸內化為詩人的精神視域。在潘維的筆下,江南變得如此肉感與性感。精致、溫婉,又混合著一絲現代的緊張與顫栗。我至今還記得初讀潘維的《同里時光》時的那種被江南氣息包裹的感覺,時光在青苔上、鏤空的窗欞上、繡花鞋和清風雅月的青石板上靜靜流淌,李少君說這是一首寫出即成經典的詩,并特別提到那句經典的結尾:“小家碧玉比進步的辛亥革命,/更能革掉歲月的命。”潘維將他詩歌的根扎入江南的地理中,在深化這種地域經驗時,許多人又擔心這會窄化他的詩歌之路。如果說,地域經驗如果僅僅提供詩歌的題材和風格,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事實上,作為一種精神視野的“地域經驗”才是詩人不得不必然面對的詩歌命題。在作為精神視野的“地域經驗”中,我們才能夠真正去評判一個詩人在處理他的“地域性”時所展現出來的詩歌技藝的高下。顯然,在潘維那里,向地域經驗的退卻,是一種精神視野的轉化,而不僅僅是題材的尋求與風格的復制。
古馬的詩歌是向情感經驗的退卻,在強調智性、經驗和戲劇化的詩歌潮流之外,默守著詩歌的抒情本質,借助謠歌的純粹情感力量,將西涼涂抹得如同月光般迷離與澄澈,同時又如同白骨般冷冽與迷魅。必須承認,九十年代之后的詩歌創作,越來越日常化、戲劇化與智性化,里爾克的句子“情感已經夠了,詩是經驗”如同清規戒律影響著詩人的創作。如果說詩是經驗,情感難道不是生命的基本經驗方式?是的,詩歌必須拒絕那種自我陶醉、自我感傷的眼淚與濫情,而對那種在微妙與細致的情感境況中興發而出的純粹與充盈的情感力量,新詩怎么能夠拒絕呢?古馬的詩,正是在天地間行走著的人孤寂很久之后的贊歌,是情感被月光釀成了清冽的酒,需要尋一干凈新鮮的通道涌流。正如梅紹靜所說,古馬詩歌的的美仿佛真的在“沉寂”之中,它的“沉寂”是金;它的美似乎是在“了然”里頭,它的“了然”卻是幻異。也許真善美本身就已“自給自足”,不需推銷,不必論證,它在那里望著我們,靜靜地等待我們的腳步踏響鳴沙……
五個人,不同的退卻方向,不同的退卻方式,他們分別回到了詩歌的隱秘源頭,回到經驗的地基深層:繁瑣現實、古典幽微、繁茂自然、廣袤地域、深層情感……如果說《五人詩選》的野心是為詩歌的未來發展廓清前景與厘清道路的話,那么,五位詩人就以退卻的方式作出了最好的詩歌范例——詩歌,只有不斷地回到詩歌的源頭,才能重新遠行。甚至,遠行的方向,就是一次次回到詩歌經驗的隱秘源頭,回到詩之為詩的永恒質問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觸及到了《五人詩選》隱秘的立場與雄心:新詩需要樹立標準。這里的標準并不是對其他詩人創作的指手劃腳,而是作為一種示例,在動態與包容中建立起來未來詩歌前進的路標。李少君在曾在《新詩需要樹立標準》這篇訪談里把我們目前的詩歌狀況與宇文所安所描述的初唐詩向盛唐詩轉變的過渡時期相提并論。如果是這樣的話,新標準的樹立則無疑于需要擔當起陳子昂《修竹篇序》對詩歌發展的導引作用。但是,陳子昂有興寄、風雅的傳統可以援引以為助力,我們今天詩歌的發展則需要重要去挖掘那些再次導引詩歌發展的原動力。有趣的是,宇文所安在《初唐詩》中著力分析的就是宮廷詩作為詩歌標準與慣例而發揮出的對唐代詩歌走向的影響。但今天面臨的情況卻恰好是沒有一個標準與慣例可供我們超越。于是,詩人們只有退卻,以反身而誠的方式,重新尋找新詩的依傍。
再重申一次,《五人詩選》提供的退卻方向只是案例,是參考,而絕不是“只能如此”的標準。事實上,新詩可以返回的方向還有很多很多:語言的地基、身體的隱秘顫栗、愛欲的萌發、存在的澄明、萬物的應和……只要詩人足夠敏感、足夠耐心,轉身與回返的路,就能走得足夠遠,遠到未來……
而現在,五位詩人在退卻的道路上留下回返的路標。詩人退卻到詩歌的根性處,和它們和諧共鳴,因此,他們找到了新的依傍。這些依傍,才是詩歌再一次噴涌的原動力。有了依傍,詩歌才有行向未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