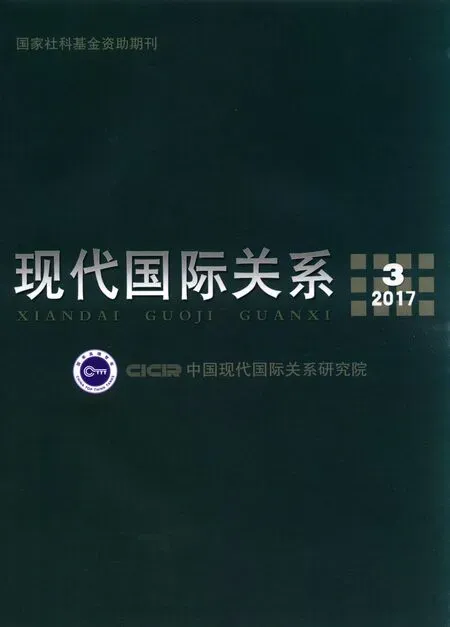亞太“雙領導”與中美自貿區戰略博弈*
孫西輝 呂 虹
亞太“雙領導”與中美自貿區戰略博弈*
孫西輝 呂 虹
當前,亞太地區已形成中美相對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雙領導”的客觀條件,但是由于中美發揮領導作用的主觀條件差距較大,亞太地區并未真正形成中美“雙領導”體制。中美實力對比和亞太權力分布的這種客觀事實,對于分析兩國亞太自貿區戰略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各自推進的自貿區建設有特定的目標,但兩國的亞太自貿區戰略是互補性競爭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調整了奧巴馬政府的亞太自貿區政策,使美國的亞太自貿區政策出現一些新變化。特朗普政府的亞太自貿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種發展可能,中國需要密切關注并繼續推進自己的亞太自貿區戰略。
國家利益 自貿區戰略 亞太地區“雙領導” 中美關系
[作者介紹] 孫西輝,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博士后、副教授,主要從事外交戰略、中美關系、亞太國際關系等研究;呂虹,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副教授,主要從事美國外交政策、亞太國際關系等研究。
近年來,隨著中國持續快速發展和美國相對衰落,國際權力轉移和中美實力消長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有學者甚至提出亞太地區已形成中美“雙領導體制”和“兩極格局”的觀點。這些研究均聚焦于亞太地區的實力分布,尤其是中美力量對比。中美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是亞太地區最強大、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兩國實力的變化對于地區格局和地區秩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中美力量對比發生變動的情況下,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博弈日漸激烈,而自貿區戰略是備受關注的領域之一。一方面,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P),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并欲轉向雙邊自貿區談判。另一方面,中國簽署的雙邊自貿區協定大多數涉及亞太國家,目前正積極參與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伙伴關系”(RCEP)談判。這表明,中美都把自貿區談判視為對外經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把亞太地區作為自貿區戰略的“主攻方向”,亞太地區成為兩國自貿區戰略博弈的“競技場”。本文將在對比中美實力的基礎上,分析亞太地區的權力格局,探討兩國亞太自貿區戰略的發展邏輯與博弈特點,討論特朗普政府未來亞太自貿政策的可能發展方向及中國的對策。
一、亞太地區中美“雙領導”:既成事實?
根據筆者掌握的材料,美國美利堅大學的趙全勝教授最早提出“中美雙領導體制”的概念,“這一概念關注的是亞太地區出現的新格局,強調美國與中國在不同領域所發揮的不同的領導作用,具體指的是美國與中國分別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全領域和經濟貿易領域發揮著領導作用。”*趙全勝:“中美關系和亞太地區的‘雙領導體制’”,《美國研究》,2012年第1期,第8頁。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則認為,“目前亞太這個局部地區,形成了中美兩極格局,……即使亞太地區已形成兩極格局,中國的實力仍弱于美國。”*閻學通:“亞太已形成中美兩極格局”,《國際先驅導報》,2015年2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02/05/c_133972187.htm.(上網時間:2016年6月30日)應該說,兩位學者都看到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實力地位的新變化,但前者強調中美分領域的“雙領導”,即兩國在不同領域擁有領導權;后者強調中美在亞太地區形成兩個“極”,但實力地位有差距。本文認為,這兩種表述各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準確。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在亞太地區并非“不平衡的‘兩極’”,亞太地區也未形成中美“雙領導體制”。
(一)中美在亞太的實力相對均衡。中美經濟實力對比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美國經濟總量領先,但中美經濟地位可能發生逆轉;二是中國工業產值領先于美國,且差距越來越大;三是中國對外貿易超越美國,差距在穩定擴大;四是美元國際地位保持絕對優勢,人民幣短期內不可能明顯縮小差距。綜合來看,美國在經濟總量和貨幣地位方面占有明顯優勢,但經濟總量的優勢存在不確定性;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工業產值方面領先,且這種領先趨勢在不斷擴大。此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更為明顯。中國不僅是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且與許多亞太國家存在明顯的經濟互補性,因而在亞太地區的經貿領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以及亞太國家傳統的貿易對象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與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相比,中美兩國的經濟規模具有絕對優勢,其他國家的實力將與中美的差距越來越大。
根據“全球火力”(GFP)的相關數據*“Countries Ranked by Military Strength,” April 2016.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p.(上網時間:2016年7月2日),中美軍事實力對比的總體特點,一是美國陸軍在多數項目上不占優勢,中國陸軍十分強大;二是美國空軍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有優勢;三是美國海軍在質量上具有絕對優勢,中國海軍在數量上有優勢。總體上,美國軍事實力目前仍遙遙領先,但中國正在許多方面快速追趕。在亞太地區,盡管美國在西太平洋有一些軍事盟友和海外基地,但畢竟遠離美國本土,維持軍事存在或進行軍事行動的成本高昂。對于中國而言,西太平洋是中國的“家門口”,近海防御和作戰成本較低,而且可以借助陸軍優勢彌補空軍和海軍的不足,形成陸、海、空、天立體防御和威懾體系。因此,盡管美國軍事實力總體上遠遠超過中國,但地緣優勢使中國可以在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實力和威懾力不輸于美國。此外,中美兩國的軍費開支、軍事裝備和軍隊人數,也是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
在政治實力方面,中美實行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擁有的政治實力和影響力也不盡相同。一方面,政治實力和影響力以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為基礎,政治實力和影響力的大小取決于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強弱。另一方面,政治制度類型對于政治實力沒有太大影響,但對于政治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中美政治實力對比的主要特點,一是美國極力推銷其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中國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二是美國頻繁支持他國反對派,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三是美國對外實行強制外交,中國積極應對強制外交。簡言之,由于綜合實力、價值理念和外交原則不同,中美政治實力和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美國的政治影響力遍及全球,中國則僅限于周邊區域。即便在亞太地區,美國的政治影響力也遠遠大于中國,但中國在把經濟實力轉換為政治影響力方面具有一定優勢。由于經濟和軍事實力懸殊,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政治實力和影響力也難以望中美之項背。
通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第一,與美國相比,中國在綜合實力和在全球領域的影響力上仍有較大差距,但中美在經濟、軍事和政治領域的實力和影響力對比各有優勢;第二,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大體相當,美國略強;第三,中美兩國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亞太地區其他國家難以比擬。鑒于當前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和戰略競爭關系,可以說亞太地區形成了一個實力大體相當的中美兩強并立的力量格局。
(二)中美在亞太發揮領導作用的主觀條件懸殊。通常而言,“領導”既可以表示一種帶領或引領向某一方向前進的動作或狀態,也可以指具有這種能力的行為體,還可以表示為具有發揮引領作用的特權或地位。國際政治領域的“領導”通常指“領導權”(leadership)或“領導地位”(leading position)。與“領導權”相近的一個術語是“霸權”(hegemony)。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經常不加區別地混用“領導權”和“霸權”,但也有少數學者區分其差異。如戴維·雷克(Daivd A. Lake)認為,“霸權穩定論”可分解為“領導理論”和“霸權理論”。*David A. Lake, “A.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7, No.4, 1993, pp.459-489.實際上,漢語中的“霸權”常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指利用實力優勢刻意操縱或控制其他國家的行為。英語中的“霸權”則是一個中性詞,常指超群的優勢地位或能力。由此可見,“霸權”與“領導權”是近義詞,但前者強調相對于別國的優勢地位或政治支配地位,后者強調擁有發揮引領作用的特權。
學術界對“領導權”進行過相關論述,包括“領導權”的含義*Charles P.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2, 1981, pp.242-243; Young,Oran R. Young,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3, 1991, pp.281-308; Joseph S.Nye, The Powers to Lead: Soft, Hard, and Sm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和發揮領導作用的條件*趙全勝:“中美關系和亞太地區的‘雙領導體制’”,第10頁;陳琪、管傳靖:“國際制度設計的領導權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14~15頁。。本文認為,“領導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要點:第一,領導權是發揮領導作用的特權,領導地位指因擁有領導權或發揮領導作用而得到的聲譽,擁有領導權和領導地位的國家是領導國。第二,實力是領導權的決定性因素與客觀條件,國家間的實力對比是領導權歸屬的主要指標。第三,發揮領導作用不僅需要具備相應的實力,還需要一些主觀條件,如擁有發揮引領作用的意愿、能力和技巧。第四,擁有領導地位需要得到國際社會或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認同。
根據前兩點認識并結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基本觀點,即中美不僅在亞太地區的實力和影響力大體相當,且與域內其他國家實力相比具有絕對優勢,因而具備了在亞太地區擁有領導權或發揮領導作用的實力基礎或客觀條件。然而,根據后兩點認識,發揮領導作用不僅要看實力和客觀條件,還要考察相應的主觀條件和國際認同。在這方面,中美兩國具有較大差異。
首先,中美在發揮領導作用的意愿方面態度迥異。美國毫不諱言追求領導權,其領導人和高官頻繁表達在亞太發揮領導作用的意圖和決心。與之相反,中國領導人從未表達過發揮地區或全球領導作用的意圖。中美兩國不同的態度與宣示是由各自的實力和外交傳統決定的。其次,中美在發揮領導作用的技能方面差異懸殊。一方面,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是具備國際領導能力,即吸引他國追隨的素質和主觀條件。另一方面,發揮國際領導作用需要一定的經驗和技巧,即將領導能力變為現實的方法和本領。從理論的角度看,獲得并發揮領導能力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運用政治和經濟權力進行激勵;二是發揮觀念的作用影響他國的認知;三是借助談判技巧推動談判。*Michael Gnibband Joyeeta Gupta, “Leadership: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Joyeeta Gupta and Michael Grubb, ed.,Climate Change and European Leadership: A Sustainable Role for Europe? Frederick: Kluwa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p.15-24.從現實的角度看,美國作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全球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與影響力,且自二戰以來不斷主導創建各種國際制度,并通過各種國際場合加以推廣,在地區層面和全球層面積累了不少發揮領導作用的經驗與技能。新中國是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脫胎而來的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的發展任務和壓力,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時間不長,國際談判的經驗不足。再次,中美發揮領導作用面臨不同的國際認同。通常情況下,某一(些)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權威性、代表性和公正性形象決定其領導地位的國際認同程度,而這一形象可通過三種途徑獲得:一是通過展示強大的實力建立權威并獲得國際認同;二是通過尋求共同的信念或價值觀念獲得國際認同;三是通過提供某種利益獲得國際認同。二戰以來,美國憑借強大的實力在全球和亞太地區展示了自身實力,歷次大小戰爭使其處于絕對權威的地位,在海外推廣美式民主制度使不少國家認同這一價值觀,并通過制度手段提供各種公共產品,美國發揮國際領導作用自然會得到一些國家的認同。與此不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只是在近十幾年才快速增長到國際矚目的程度,并開始在國際領域提供公共產品,但中國并未刻意炫耀實力,也沒有推銷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因此,中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也具有一定的認可度,但與美國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綜上所述,盡管中美在各領域都具有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實力,亞太地區形成了相對均衡的中美兩強并立格局,存在中美“雙領導化”的客觀條件,但由于中美發揮領導作用的主觀條件差距較大,亞太地區并未真正形成中美“雙領導”體制。換言之,亞太地區只是出現了中美“雙領導化”的趨勢。然而,中美實力對比和亞太權力分布的這種客觀事實,對于分析兩國亞太自貿區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博弈:零和抑或互補?
中美有各自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在博弈中呈現既競爭又互補的狀態。
(一)中美自貿區戰略的發展邏輯。對外戰略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作為一種對外戰略,自貿區戰略同樣遵循這一原理。也就是說,國家利益決定自貿區戰略,自貿區戰略服務于國家利益。這里有三點需要說明:第一,國家利益涵蓋不同的領域并具有相應的層次。通常而言,國際政治領域的國家利益指有利于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與精神收益,通常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第二,一國的自貿區戰略并非服務于所有領域和層次的國家利益。作為一種對外經濟戰略,自貿區戰略通常會給相關國家帶來經濟收益。然而,并非所有國家都能從中獲得經濟收益,也不是所有國家都只看重經濟收益,有些國家可能通過自貿區戰略維護其政治或安全等方面的國家利益。第三,并非所有國家的自貿區戰略都追求同樣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自貿區戰略維護的國家利益根據普遍程度的大小排序是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處于國際體系不同階梯的國家具有不同的優先目標,因而對自貿區戰略各項收益的重視程度存在差異。
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啟動對外自貿區建設。從1985年生效的美以自貿區,到1992年北美自貿區(NAFTA),再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美國的自貿區戰略經歷了一個正式啟動、低效推進、快速發展和深化構建的演變過程。2009年至今是美國自貿區戰略的深化構建階段,也是美國在“重返亞洲”的背景下實施亞太自貿區戰略的重要時期,突出特點是大力推進TPP。鑒于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實力對比大體相當,奧巴政府實施亞太自貿區戰略的更主要目標是鞏固地區領導地位和限制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并獲得經濟收益,途徑是牢牢掌握國際規則制定權和地區話語權。然而,特朗普政府對亞太自貿政策進行了大幅調整,主要表現為退出TPP、重視雙邊自貿區建設、更注重經濟收益。*“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 January 23,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1/23/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withdrawal-united-states-trans-pacific.(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從目前的情況看,特朗普政府正在積極落實“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競選理念,在對外貿易方面主要體現為:在意絕對經濟收益、突出美國藍領階層的利益、更強調所謂的公平貿易。因此,特朗普政府的突出特點是強調經濟利益并兼顧政治利益。
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后逐步擴大對外貿易。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開始與一些國家啟動雙邊自貿區談判。2013年以來,中國不僅在國內進行自貿區試點建設,而且加快推進對外自貿區談判。2002年至今,中國的自貿區戰略經歷了初步探索、正式啟動和快速推進三個發展階段。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國自貿區戰略的快速推進階段,也是在亞太地區全面展開自貿區戰略的階段。中國在這一階段新啟動了五個雙邊自貿談判,簽署了五個自貿協定;啟動了兩個多邊自貿區談判;另有五個雙邊自貿談判在研究中,并提出構建亞太自貿區的“北京路線圖”。中國大力推動亞太自貿區戰略的根本目標是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內外環境。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并重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
(二)中美自貿區戰略的競爭性。討論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的競爭性,不能僅局限于中美兩國,還要考慮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周邊鄰國。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的競爭性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利益競爭。自貿區戰略本質上是一種對外經濟戰略,經濟收益是基本目標。對中美而言:一是雙邊自貿區中的中美競爭情況。奧巴馬時期美國主導的TPP不包含中國,12個成員國中有多個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特朗普政府已經退出TPP,但主張以雙邊自貿區代替TPP,且雙邊談判很有可能率先從TPP的參與國開始。如果特朗普政府推崇的雙邊自貿區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樣會影響鄰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系。二是RCEP中的中美競爭情況。東盟發起的RCEP邀請中國等六個國家參加,但不包括美國。在西方看來,中國實力強大,實際上是RCEP的主導國。有學者認為,如果RCEP建成而TPP沒有建立,中國將獲益880億美元。*Ronglin Li and Yang Hu,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China’s Free Trade Strategies,” in Harsha Vardhana Singh, ed., TPP and India: Implications of Mega-Regionals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Wisdom Tree, 2016, pp.209-210.三是中日韓自貿區中的中美競爭情況。中日韓自貿區顯然只包含東亞三大經濟強國,不包括美國。鑒于中日韓的經濟規模總和對美貿易規模,中日韓自貿區建立后將對美國產生影響。
第二,建設路徑競爭。關于亞太自貿區的建設路徑,中美兩國思路各不相同。一是美國路徑中的中美競爭情況。對于奧巴馬政府而言,建設亞太自貿區(FTAAP)的思路是以TPP為基礎不斷在亞太地區擴展,最終形成一個涵蓋整個亞太的自貿區。然而,特朗普政府退出TPP,要以雙邊自貿談判代替多邊自貿機制。這表明,特朗普政府目前關注的是本國經濟收益,并不急于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當然,這不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相關政策不會發生變化。二是中國路徑中的中美競爭情況。中國建設FTAAP的路徑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與某一國家(集團)或地區建立的雙邊自貿區;第二步是次區域多邊自貿協議;第三步是以APEC為基礎,將各種雙邊和多邊自貿區整合為區域性多邊自貿協議。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將在最后一個步驟中融入。三是東盟路徑中的中美競爭情況。東盟建設FTAAP的路徑也可分為若干個步驟:第一步是以東盟為基礎建立東盟自貿區(AFTA);第二步是以東盟為中心建立“10+1”結構;第三步是以東盟為核心建立“10+3”結構;第四步是以“10+6”機制為基礎建立RCEP;第五步是以APEC為基礎構建FTAAP。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從第二階段便已參與其中并發揮重要作用,而美國直到最后階段才能加入。
第三,戰略利益競爭。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美圍繞亞太自貿區在深層次上競爭的是戰略利益。一是美國的戰略目標與中美競爭情況。根據奧巴馬政府的FTAAP路徑,中國被排除在TPP之外,而其他成員國大多是美國的條約盟友、軍事伙伴或與中國有爭端的國家,孤立與防范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特朗普政府雖然退出了TPP,但不代表美國將放棄地區領導權。二是中國的戰略目標與中美競爭情況。中國當前的自貿區戰略主要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目標,中國無意爭奪地區領導權。當然,中國積極推動FTAAP也有自身的戰略利益追求,即確保周邊地區穩定與繁榮,為中國經濟建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東盟的戰略目標與中美競爭情況。東盟雖然希望主導地區多邊機制,但由于整體實力有限,需要不斷借助大國的力量對沖其他大國的影響,以維護自身戰略利益。東盟在APEC中借助中國的力量抵制日本主導東亞多邊機制的意圖,邀請美國加入東盟地區論壇(ARF)來平衡中國影響,但“10+3”機制的建立也顯示了東盟對美國的疑慮。在推進RCEP的過程中,東盟邀請中國參加以對沖美國和TPP的壓力,卻形成了中美之間的競爭。
(三)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的互補性。實力地位決定國家利益,進而影響自貿區戰略的戰略定位、實施方式和利益層次。在亞太地區,盡管中美具備了成為“雙領導”的實力和影響力,但中國主觀上不謀求地區領導權。此外,中美不同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各自在對外戰略中追求不同的戰略目標,這使兩國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在諸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甚至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第一,戰略定位的差異與互補。中美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這對兩國對外戰略的定位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亞太地區的絕大多數自貿區談判對象和已建立的自貿區伙伴都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其亞太自貿區戰略的定位是采取符合相關國家實際的中低端標準。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奧巴馬政府力推的TPP致力于建立高端自貿區。只不過,為了加速談判進程,各國在諸多領域相互妥協,導致成員國在部分標準方面存在差異。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認為這有損于美國利益,執意退出TPP并試圖轉向雙邊自貿區談判,希望以此實現完全平等一致的高標準。可見,中美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在定位方面存在極大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不僅有助于避免了兩國的零和競爭,也為域內國家提供了更多選擇,因而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第二,實施方式的差異與互補。中美實力地位不同,經驗和能力也存在差異,因而實施自貿區戰略的方式不盡相同。中國實施亞太自貿區戰略堅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以雙邊自貿區為基礎,經由次區域自貿區而實現區域性自貿區。就美國而言,奧巴馬政府以多邊自貿談判為起點,希望通過擴充TPP成員的方式向整個地區擴散;特朗普政府目前傾向于雙邊自貿區談判,但不排除今后重回多邊機制的可能性。無論特朗普政府最終是否回歸多邊自貿區思路,都可能會堅持所謂的“美國優先”原則,并可能從TPP談判國入手,因而其亞太自貿區戰略的實施方式必然不同于中國。總之,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的實施原則和方式極為不同,這使得亞太各國在區域一體化方面面臨更多機遇。
第三,利益層次的差異與互補。由于實力地位以及歷史與文化不同,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的目標大相徑庭。中國是發展中大國,面臨巨大的發展任務和壓力,因而在亞太自貿區建設中側重經濟利益。同時,中國也是一個新興大國和世界經濟大國,追求適度的政治收益符合本國利益,主要體現為維持有利的發展環境、參與制定區域規則和推動“兩個引導”*習近平:“牢固樹立認真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開創新形勢下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報》,2017年2月18日。。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維護地區領導權是根本目標。奧巴馬政府的亞太自貿區戰略重視經濟利益,但更側重政治利益。奧巴馬在2015年的國情咨文中表示:“中國想要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這一地區制定規則。我們為什么要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們應該制定那些規則。”*“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annotations:8511434.(上網時間:2016年6月4日)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亞太自貿區政策似乎更突出經濟利益,尤其是美國工人的利益*“Trade Deals That Work for All Americans”, https://www.whitehouse.gov/trade-deals-working-all-americans.(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但不可能放棄地區領導權等政治利益。因此,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在政治利益方面的根本目標不同,這是兩國亞太自貿區戰略非零和性的最重要原因,同時也使域內其他國家可以更好地進行比較和選擇。就此而言,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也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三、美國亞太自貿區政策的前景及影響
特朗普政府對奧巴馬政府的亞太自貿政策進行了調整,但這并非根本改變美國的亞太自貿區戰略。當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亞太自貿區政策表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更強調所謂的公平貿易,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更明顯;二是更注重經濟利益,但不排斥政治利益;三是更看重雙邊貿易協定,不傾向多邊自貿機制。目前,特朗普政府執政時間還不長,其亞太自貿政策尚未定型,今后還有多種發展可能,也會對地區形勢和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一種可能是美國以雙邊形式取代多邊自貿區談判。也就是說,美國繼續推進亞太雙邊自貿區談判,但不涉及地區多邊自貿機制建設,即徹底放棄TPP。相對而言,這種可能性最大。就地區形勢而言,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拋棄多邊自貿區談判意味著放棄美國一直推動的區域性自貿區建設,也可能不支持甚至破壞其他國家推動的區域性自貿區建設,這將嚴重遲滯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堅持雙邊自貿區談判,旨在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非但不會在任何方面對他國做出讓步,反而可能以單邊方式或強硬手段對談判對象國施壓,這或將導致亞太地區國際關系出現一定程度的緊張。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如果美國徹底放棄TPP,中國以多邊方式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沒有了美國的直接競爭,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也會對中國支持的RCEP更加“專心”,從而使中國可以更從容地實施自己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并贏得更多國際支持和聲望。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了TPP的直接競爭,中國在內部改革和產業升級方面或許會因外部壓力不足而放緩步伐,從而影響中國提升經濟競爭力的速度。
此外,在美國退出TPP的情況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等TPP談判國試圖繼續推動TPP生效,澳大利亞甚至主張中國“接盤”TPP,這使中國面臨一個重要抉擇。作為具有亞太地區領導實力的國家之一,中國是否加入TPP需要慎重考慮。一方面,中國現在加入TPP的條件仍不成熟。一是部分TPP協議和規則不適合中國。TPP是美國主導達成的所謂高端自貿協議,雖然對越南等發展中國家有所照顧,但中國如果按照現有協議加入顯然不適合本國國情。二是日本未必希望中國加入TPP。美國退出后,日本是TPP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不僅希望美國重新加入,而且試圖靠自身力量支撐TPP,因而不太可能希望中國加入。但另一方面,中國加入TPP也有一些益處。一是有利于穩定和強化地區多邊貿易機制。美國退出TPP之后,其他成員國的反應不一,部分同時參與TPP和RCEP談判的國家將目光轉向RCEP,甚至一些未參加RCEP談判的國家也希望加入,還有些已經參與了RCEP談判的國家仍寄希望于TPP。如果中國加入TPP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有利于穩定亞太國家的貿易關系并推動多層次的多邊自貿機制建設。二是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地區影響力。與美國退出TPP顯示的“逆全球化”傾向不同,中國明確向世界表達了支持經濟全球化的意愿和決心,展現了“順勢而為、擁有擔當”的大國風范。如果中國加入TPP,以此表明中國的這一立場,將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使中國在與美國的亞太兩強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牢固。因此,對于加入TPP的邀請,中國需要認真權衡并繼續觀察。
第二種可能是美國重回亞太多邊自貿區機制。也就是說,美國重拾多邊自貿區的方式,如重新加入TPP。這種可能性暫時不大,但美國國內外仍存支持TPP的力量。不少美國國會議員反對退出TPP,其中不乏共和黨重量級議員。如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麥凱恩曾表示:“特朗普打算退出TPP,盡管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但對于我們這些相信自由貿易和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重要性的人而言,仍感到十分失望。”*“McCain: Trump Withdrawal from TPP A ‘Disappointment’”, The Daily Caller, November 22, 2016, http://dailycaller.com/2016/11/22/mccain-trump-withdrawal-from-tpp-a-disappointment/.(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美國共和黨通常比較支持自由貿易。考慮到共和黨掌管國會兩院的現實,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重啟亞太多邊自貿區談判的可能性。同時美國學術界和戰略界不少人反對退出TPP。一些美國經濟學家和戰略家認為,美國退出TPP在經濟和戰略方面有利于中國但有損于美國利益,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加里·哈弗鮑爾、布魯金斯學會的比爾·加爾斯頓等都持此種觀點。*“專家:美國退出TPP有利于中國而傷及自身”,《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3日。四是部分美國盟友期待美國重新在TPP“挑大梁”。自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TPP起,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十分焦急,一直期待特朗普“回心轉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甚至當面規勸。實際上,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并轉向雙邊自貿談判并非排斥多邊機制,而是認為諸如TPP和NAFTA等多邊自貿機制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過于關照,沒有充分照顧到美國的利益,因而認為這種制度安排不公平。因此,如果美國能夠順利達成它希望的那種雙邊自貿協議,或其他國家愿意與美國達成美國認可的多邊自貿協議,特朗普政府有可能轉向多邊自貿談判。
如果特朗普政府未來恢復多邊自貿區談判,也會對地區形勢和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若特朗普政府在多邊自貿區談判中堅持“美國優先”,必然要對已達成的TPP協議進行重新談判。假如特朗普政府在談判過程中適當妥協,則有可能達成新的多邊自貿區協議,但它對地區形勢和中國的影響與奧巴馬時期達成TPP所產生的影響不會有太大區別。
第三種可能性是特朗普無法推進其政策,導致美國亞太自貿政策發生變化。這屬于小概率事件,但也并非絕無可能。特朗普執政以來,其政府內部出現各種問題,與美國主流媒體更勢同水火。特朗普就職兩周后,支持率僅為44%,成為少有的剛上任反對率就超過支持率的美國總統。有43%的民眾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這一比例幾乎與其支持率相當。*Jennifer Agiesta, “First Trump Approval Rating Lags behind Past Presidents”, Daily Mail Online, Feburary 3,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2/03/politics/donald-trump-approval-rating/index.html.(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低支持率無疑會影響其行政效力和政策推行。有評論員認為:“特朗普在執政第一個月已經向情報機構和媒體開戰,司法部門或將成為下一個敵人。在特朗普與美國體制之間,不是反對力量將他拉下臺就是他摧毀這個體制,沒有中間地帶。我將賭注押在前者上面。”*Edward Luce, “Donald Trump and the siege of Washingto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9,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bc99e5d8-f526-11e6-95ee-f14e55513608.(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任性”執政招致仇恨。英國《每日郵報》曾報道,有12000多人在推特上呼吁刺殺特朗普。*“More than 12,000 Tweets Have Called for Trump’s Assassination since the Inauguration”,Daily Mail Online,Feburary 3, 2017,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189124/More-12-000-tweets-call-Trump-s-assassination.html.(上網時間:2017年2月4日)反對和仇視特朗普的原因多種多樣,甚至未必與貿易政策有關,也不一定都是認真的,但在社交媒體公開呼吁刺殺美國總統仍能表明某種傾向。“高齡”總統健康問題也是隱憂。特朗普已經年過七旬,雖然目前健康狀況還不錯,但畢竟“歲月不饒人”,不能排除出現健康問題影響執政的可能。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對亞太地區形勢和中國亞太自貿區戰略的影響將取決于特朗普之后的美國新政府的相關政策。
如前所述,特朗普政府的亞太自貿政策尚未定型,未來仍存在較多不確定性。然而,無論形勢如何發展,中國不僅要密切關注美國的亞太自貿區政策走向乃至特朗普政府的“前途命運”,更要按部就班地實施自己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實際上,由于中美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兩國的亞太自貿區戰略存在定位差異,中美都需要正確認識該戰略的這種互補性競爭關系,加強溝通與交流,合理處理相關問題,共同為維護和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承擔應有的大國責任和義務。○
(責任編輯:王文峰)
* 本文是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國地緣政治的影響及其應對研究”(項目編號:16BGJ03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