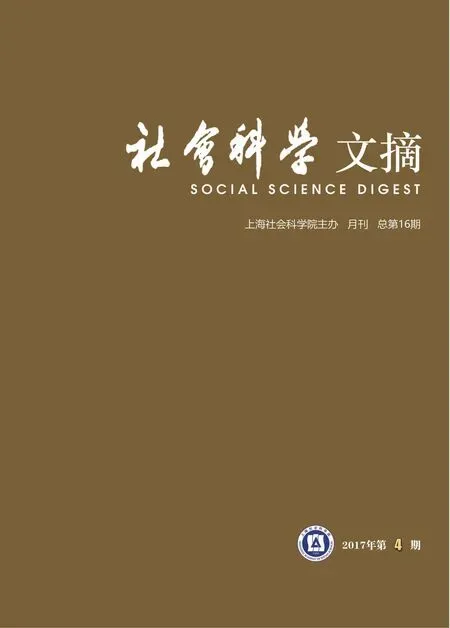何謂世界文學?
文/方維規
何謂世界文學?
文/方維規
“世界文學”難題,或眾說紛紜的“世界文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圍繞“世界文學”觀念展開了一場深入的理論探討;并且,“世界文學”概念成為新近關于“全球文學”(Global Literature)國際論爭的焦點。打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烙印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曾被持久而廣泛地接受。最遲自20世紀60年代起,這個概念逐漸遭到批評,原因是其思考文學時的(常被誤認為源自歌德的)精英意識,以及世界文學設想雖然超越了民族框架,卻只能基于這個框架才可想象。“一般來說,所謂普世性,只要不僅是抽象,只能存在于地方性之中。”如今,不少人喜于“世界的文學”(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之說;這個概念雖然還勾連著世界文學的“經典性”,卻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想象或綱領。
新近的世界文學論爭呈現出色彩斑斕的景象。歐美關于這個概念的論爭,似乎還未終結。本文試圖反復追尋歌德論說,旨在厘清相關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考察當今。
“世界文學”概念的“版權”及其歷史背景
論說“世界文學”概念,總要追溯至文豪歌德。歌德曾長期被看作“世界文學”一詞的創造者。另外,不少學者論述歌德“世界文學”概念時,不愿或不忍心看到其時代局限,他們主要強調這一“歌德概念”的全球視野。
無疑,“世界文學”概念不能只從歌德說起,還得往前追溯。約在30年前,魏茨(Hans-J. Weitz)發現維蘭德(Christoph M. Wieland)早在歌德之前就已用過這個詞,見之于他的賀拉斯(Horace)書簡翻譯修訂手稿(1790)。維蘭德用這個詞指稱賀拉斯時代的修身養成,也就是“世界見識和世界文學之著色”(“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 u. Weltlitteratur”)。此處“文學”乃見多識廣的“世界人士”(homme du monde)之雅興;此處“世界”也與歌德的用法完全不同,指的是“大千世界”的教養文化。無論如何,已經沒有理由仍然把“世界文學”一詞看作歌德之創,也不能略加限定地把它看作歌德所造新詞。
其實,“世界文學”這個有口皆碑的所謂“歌德概念”,在歌德起用之前54年就已出現!施勒策爾(August L. Schl?zer)早在1773年就提出這個概念,將之引入歐洲思想。他于論著《冰島文學與歷史》中寫道:“對于整個世界文學(Weltlitteratur)來說,中世紀的冰島文學同樣重要,可是其大部分內容除了北方以外還鮮為人知,不像那個昏暗時代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學、愛爾蘭文學、俄國文學、拜贊庭文學、希伯來文學、阿拉伯文學和中國文學那樣。”事實是,“世界文學”概念及與之相關的普世主義,已在1773年出現,早于歌德半個世紀。
毋庸置疑,歌德對“世界文學”概念的確立和流傳作出了重大貢獻,而說這個概念最初并不源自歌德,還有更深層的思想根源。這里不只涉及這一詞語本身,而是孕育和生發世界文學思想的思潮。一個重要貢獻來自赫爾德(Johann G. Herder)。1773年,赫爾德與歌德、弗里西(Paolo Frisi)、莫澤爾(Justus M?ser)一起主編出版《論德意志藝術》(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其中不僅載有狂飆突進運動的宣言,亦鼓吹民族文學或人民文學。
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其《文學的世界共和國》中指出,民族文學思想主要由赫爾德倡導并產生重大影響,從德語區傳遍歐洲并走向世界,此乃所謂“赫爾德效應”(“Herder-effect”)。“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這兩個概念相輔相成:前者是后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沒有后者,前者只能是地方的;沒有比照對象,民族文學也就失去了與世界上重要作品的媲美可能性。赫爾德也是世界文學的精神先驅之一,他的著述明顯體現出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歌德《詩與真》(1811~1812)中的一段話,講述他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與赫爾德的相遇。
他(赫爾德)在其先行者洛斯(Robert Lowth)之后對希伯來詩藝之極有見地的探討,他激勵我們在阿爾薩斯收集世代相傳的民歌,這些詩歌形式的最古老的文獻能夠證明,詩藝全然是世界天資和人民天分,絕非個別高雅之士的私人稟賦。
這段語錄中的“世界”,常被歌德研究者看作其世界文學思想的序曲,這當然不無道理。可是,若無赫爾德,這個概念在歌德那里或許不會獲得如此重要的意義。
“世界文學”概念不只拘囿于自己的實際意義,它還連接著更寬闊的歷史和體系語境,同其他一些近代以來與“世界”二字組合而成的重要概念密切相關。“世界-”概念旨在涵蓋某種存在之整體。1770年至1830年有一股強勁的“世界”熱,一些同屬普遍主義的概念脫穎而出,其中有許多今天依然很重要的觀念,以及一些今天還被看重的價值觀與全球思維方式。也是自18世紀70年代起,歌德時常說及世界,“世界詩歌”(Weltpoesie)、“世界文化”(Weltkultur)以及“世界歷史”“世界靈魂”“世界公民”“世界事件”等詞語組合,常見于他的言說。就“世界文學”而言,歌德很早就認識到文學場的某些特有規律,使得交流過程成為特殊的文學景觀,可是這要到很久以后亦即19世紀20年代末期才被他明確描述。而在19世紀早期的法國,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奧爾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éans, 1801)的法文本譯者德謝(Jean J. Derché),最先提出了歐洲文化網絡意義上的“文學世界主義”。
最后,我們還須提及施特里希(Fritz Strich)在歌德研究的標志性著作《歌德與世界文學》(1946)中所強調的視角,即個人經歷對歌德世界文學思想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歌德感到特別驚奇,自己那些隱居狀態中創作的作品,完全是為了釋放自己,為了自己更好的養成而寫的,最后居然能在世界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接連不斷地傳到他這個年邁文學家的耳里。這一世界反響有益于他的身心,讓他感到幸福,從而成為他呼喚和促進世界文學的最重要的動機,要讓所在都有他這種福祉。
莫衷一是,或歌德對“世界文學”的不同理解
自1827年初起,歌德開始并多次在書評、文章、信件和交談中明確談論“世界文學”。他在1827年1月15日的簡短日記中,第一次寫下“世界文學”字樣:“讓舒哈特(Johann Ch. Schuchardt)記下法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他又在1月26日給哥達(Johann F. Cotta)的信中說:“我們現在必須特別關注外國文學,人家已經開始關注我們。”次日,他在給作家和翻譯家施特賴克福斯(Adolph F. Streckfu?)的信中表達了他的信念:“我相信,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對此感興趣,因而都邁出了可喜的步子。”
也是在1827年初,歌德在《藝術與古代》雜志第6卷第1冊轉載了《塔索》譯者迪瓦勒(Alexandre Duval)的兩篇書評,一篇簡介出自《商報》(Journal du Commerce),另一篇出自《全球報》,迪瓦勒盛贊歌德為楷模。歌德最后在評論這兩篇書評時寫下如下結語,第一次公開說及“世界文學”:“人們到處都可聽到和讀到,人類在闊步前進,還有世界關系以及人際關系更為廣闊的前景。不管這在總體上會有何特性,[……]我仍想從我這方面提醒我的朋友們注意,我堅信一種普遍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我們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榮的角色。”
最后,歌德于1827年1月31日在與愛克曼(Johann Eckermann)的談話中表達了后來聞名遐邇的觀點:“我喜歡縱覽域外民族,也勸每個人都這么做。民族文學現在已經算不了什么,輪到世界文學時代了;現在每個人都應出力,促成其盡快來臨。”
法國《全球報》于當年11月1日援引歌德之說,但將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替換成“西方文學或歐洲文學”(“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ou européenne”),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歌德“世界文學”的原意。換言之,他當初想象的世界文學是歐洲文學,如他主編的雜志《藝術與古代》第6卷第3冊(1829)的題旨明確顯示的那樣:“歐洲文學,即世界文學”(“Europ?ische,d. h. Welt-Litteratur”)。
毫無疑問,歌德是一個極為開放的人,但他有著明確的等級觀念。“中國、印度、埃及之古代,終究只是稀奇古怪之物”,他如此寫道,“自己了解并讓世界了解它們,總是一件好事;但它們不會給我們的品德和審美教育帶來多少助益”。顯然,歌德無法超越他所生活的時代。
德意志文學家對古希臘的鐘愛是眾所周知的。這種認同感頗為強烈,甚至可被看作“民族”而非“跨民族”之感受。歌德在同愛克曼的談話中如此解釋自己的思想:
[……]但在賞識外國事物時,我們不能固守有些奇特之物并視之為典范。我們不必認為來自中國或塞爾維亞的東西就是這樣的,也不必這樣看卡爾德隆或尼伯龍根;而在需求典范之時,我們始終必須返回古希臘,那里的作品總是表現完美之人。其他一切事物,我們僅須歷史地看待;如可能的話,從中汲取好東西。
偏偏是歌德這位“世界文學”旗手,固執于歐洲古典精神,似乎讓人難以理解,但我們無須驚詫,那是時代的局限。我們不應忘記,歌德是在七十八歲高齡,也就是去世前五年,倡導“世界文學”思想;他更多地只是順帶提及,且不乏矛盾之處,并非后來的比較文學所要讓人知道的系統設想,且把“世界文學”看作這個專業的基本概念。歌德所用的這個概念,絕非指稱整個世界的文學。并且,他的世界文學理念,所指既非數量亦非品質,既不包括當時所知的所有文學,也不涉及各種民族文學的經典作品,基本上只顧及德意志、法蘭西、大不列顛和意大利文學,間或稍帶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民間文學,偶爾也會談論幾句歐洲以外事物。
“世界文學”vs.“全球文學”:何為經典?
當今對歌德之世界文學論說的討論頗為活躍。可是,“沒有一種世界文學定義獲得普遍認同”。一方面,歌德的世界文學思考被當作理論,從而被過分拔高。另一方面,人們開始詰問,這個“歌德概念”究竟指什么?人們能用它做什么?歌德曾把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學看作歷史快速發展的結果,而他所說的“這個高速時代和不斷簡便的交流”和由此而來的“自由的精神貿易”,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達到了他無法想象和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今的世界文學觀念,這也是“全球文學”觀念的時代基礎。
在不少人指出歌德式世界文學概念的歐洲中心主義蘊含之后或同時,人們又試圖重新起用這個概念,為了在今天的意義上賡續世界主義傳統,抵御全球化的連帶弊端。當今世界許多地方所推崇的“世界文化”概念,不僅為了描述一個因全球化而改變的世界,亦體現出批判性介入。而介入的一個依據亦即中心觀點,來自歌德所強調的世界文學成于差異而非同一。柯馬丁(Martin Kern)在《世界文學的終結與開端》一文中,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對立”語境中,提出如下問題:“在不斷交流、相互影響和文化、語言四處彌漫的同質化壓力之下,地方的獨特性如何幸存?”非常明確,他的理論依據已見于該文題詞,即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所言“世界文學思想在實現之時即被毀滅”。奧爾巴赫哀嘆世界上文學多樣性的喪失,從而詰問歌德的世界文學理念究竟還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我們這個時代。交流的根源在于差別,已經占有則無需交流。不同文學之間的調適,使交流失去了豐腴的土壤。因此,人們必須更多挖掘不同文學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柯馬丁詬病與歌德理念背道而馳的最新發展:“對歌德而言,世界文學作為文化實踐保證了各種當代文學文化相互啟發和影響,然而它在今天卻面臨變為全球文學的威脅。全球文學并不關心文學文化來自何處,而是屈從于全球化市場的壓力。”因此,他認為“世界文學和全球文學的二分,已變得十分緊迫;如果世界文學成于他異性、不可通約性和非同一性,那么全球文學確實是其對立面:它在單一的、市場導向的霸權下強求一律,抹除差異,出于某種同一性而非他者性將他者據為己有”。
目前(西方)學界有一個共識,即世界文學概念不能理解為所有文學的整體,亦非世界上最佳作品之經典。世界文學是普遍的、超時代的、跨地域的文學;若要躋身于世界文學,必須是超越國族界線而在其他許多國族那里被人閱讀的作品。施特里希在70年前提出的觀點,“只有超越國族邊界的文學作品”才能成為世界文學,今天依然有效;或如達姆羅什廣為人知的說法,將世界文學描寫為“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學作品”。可見,世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個視角問題:文學不再歸于國族這一亞屬體系,而首先要從國際文學場出發,以此劃分不同文本和寫作方法的屬性和歸屬。跨語言、超國界現象亦見諸緣于政治關系的集團利益而生發的區域文學。
當代“世界文學”概念,首先不再強調國族歸屬。這對文學研究來說,也就意味著重點轉移,告別按照語言劃分的國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研究重心在于揭示諸多文學及其場域之間的關聯和界線。弗萊澤(Matthias Freise)對“何謂世界文學?”的理解是:
其核心問題是普適性與地方性的關系。這一論題提示我們,可以用關系取代本質主義視角來觀察作為現象的世界文學。我認為,世界文學必須作為一種網狀關系,而非一組客觀對象,比如一組文學文本來理解。這些關系的中心問題之一,就是普世性與地方性之間的張力。我們把客觀對象和諸關系按照不同系統鑒別分類,世界文學的不同理解首先就從這種差異中產生。理解作為關系的世界文學,提醒我們關注其過程性。世界文學并不存在,而是在發生。
我們再回到全球文學,其訴求是從全球視角出發,打破文學生產中的中心與邊緣的界線,也就是一開始就應在跨國族的架構中思考文化生產的發生和形成。語言多樣性和更換國家(居住地)對寫作產生深刻影響;并且,由此產生的文學分布于世界上的不同語言、文化和地域。就文學生產而言,國族文學的界線尤其在西方國家不斷被消解,新的文學形式不時出現,很難再用慣常的范疇來歸納。在歐美國家,我們幾乎到處可以看到雜合文學,也就是不只屬于一個國家的文學。
政治和社會的變化常會給人帶來時空上的重新定位,這在當代常與全球化和跨國發展緊密相連,即所謂走向世界。當代斯拉夫文學的轉向,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而發生,許多文學文本不再拘囿于國族的單一文化和單一語言的文學傳統。這些現象既會在文本內部也會在其所在的文學和文化場域造成“混亂”,但也釋放出創新之潛能。當今世界的許多作家,不會感到自己只屬于某個單一文化,他們有著全球認同。這是一個非常典型、到處可見的現象,它與旅行和國際性相關。這些作家作品的明顯特色是語言轉換和多語言,以及對于世界各種文化的多元視角,從而帶來社會及學術聚焦的移位,突破了以往語言、文學、歷史(文化)的三維組合。將作家團聚在一起的,不是他們的來源地、語言和膚色;團聚或分離作家的,是他們對世界的態度。
論述世界文學,不可能不談“經典”或曰“正典”。那些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在世界人民眼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有聲望的作品,可被看作世界文學,這基本上依然是一個共識。歌德使用的“世界文學”,是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精神所創作的文學。對歌德來說,不是每一部在世界傳播的作品就必然屬于世界文學。能夠獲此殊榮的關鍵是文本的藝術價值及其對世界上眾多文學的影響。(在歌德那里,“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精神”中的“世界主義”,如前所述不完全是今人理解的世界主義,他的“世界”偏重“歐洲”。)
德國文學理論家從來就有神化歌德及其“世界文學”意義的傾向,這有其深層根由。人們時常談論如何克服國族文學思維,旨在拋棄“往后看的‘老式德意志愛國主義’藝術”。格森斯(Peter Go?ens)在其論著《世界文學:19世紀跨國族文學感受的各種模式》(2011)中,聯系歌德與愛克曼的談話,他寫道:
一件藝術作品的當代成就[……]不僅取決于創作者的技藝以及他對國族藝術的意義。靠技巧和文學作品的愉悅價值所贏得的聲望是短暫的,這對世界文學思想沒有多少意義。這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作家及其作品是否成功地破除了國族文化的界線并斥諸文學藝術實踐。
這里或許可以見出本雅明關于作品通過翻譯而“長存”(Fortleben)的說法。
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什么作品可被列入世界文學行列,要在這方面獲得普遍認可的范疇和看法是相當困難的,不同國族或人民因為文化差異而對文學的意義所見不同。在西方世界,“經典”一詞從來就給人一種不言而喻的固定想象:它首先是指古代作家和藝術家的歷史作品,這些作品及其作者被視為審美楷模,在“經典”(classicus)意義上被歸入“上乘”。后來文學時代遵循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審美準則、效仿他們并創作出重要作品的作家,亦被稱為經典作家。當然,世界文學還須經得住不同時代的考驗并被看作重要作品。
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勒夫勒(Sigrid L?ffler)的《新世界文學及其偉大敘事者》(2013)一書,呈現的完全是傳統“經典”的對立模式,賦予世界文學新的含義。在她看來,今天的世界文學不是西方、歐美的文學,而是源自那些太長時間受到忽略、創造力和創造性都在爆發的地方。世界文學是全球文學,是當代真實可信、敘述真實故事、發出鮮活之聲的文學,是游走于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人、往昔殖民地后裔和沖突地區的難民所寫的后國族文學、移民文學。“游牧”作家是不同世界之間的譯者。新的世界文學取自文化混合、沖突和生存題材,如跨國遷徙、自我喪失、異地生活和缺乏認可。其實,她的“新世界文學”就是不少人新近倡導的“世界的文學”。
一般而言,“世界文學”和“世界的文學”這兩個概念多半是在明確的不同語境中被運用:若說“世界文學”依然意味著作品之無可非議的重要性,那么,“世界的文學”則更多地指向世界上那些不怎么有名、卻能展示新方向的文學;它們不同凡響、頗有魅力,卻還未在讀者意識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說,“世界的文學”未必就是審美和經典意義的上乘之作,或得到廣泛接受的作品。談論世界的文學,人們面對的是浩繁的書卷、無數作品和文化傳統、難以把握的界線以及挑選時的開放態度。
余論
歌德沒有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這個概念的神秘效應,在很大程度上緣于一個事實:它拒絕所有固定界說,就連歌德自己也回避言簡意賅的界定。他的世界文學設想的中心意義,首先意味著文學的國際交流和相互接受。他曾強調說:“不能說各民族應當想法一致,他們只需相互知道,相互理解,還要——設若他們不愿相互熱愛——至少學會相互容忍。”在諸多關于“世界文學”觀念的著述中,我們一般能見到的是歌德的樂觀態度及其相關言論,不了解或被遮蔽的是他最遲自1831年起的否定視角,至少是懷疑態度。歌德自己也告誡過,人們不能只看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學的積極意義:“若隨著交通越來越快而不可避免的世界文學逐漸形成,那我們對這樣一種世界文學不能期待過多,只能看它能做到什么和做到什么。”
寫作此文的目的,不僅旨在勾稽“世界文學”概念的——借用比較文學曾經喜用的說法——“事實聯系”(rapports de fait),也在于呈現它在當代的最新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跨語言、超國界的文學走向,全球化過程中的世界認同、文學運行和經典化的生成條件,以及還未完成的概念化過程。在這一世界背景下,當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口號和實踐,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我不愿用不少人眼中的“民族主義焦慮”形容之,但要指出它違背文學之國際傳播的一般規律。文學接受基本上是“拿來”,“接受”往往是主動行為,全世界都是如此。“輸出”之一廂情愿,欲速則不達,本在意料之中。與此相伴的是一些學者切盼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我要問的是:何在?一些學者一味強調“中國性”的說法,與世界潮流格格不入,與新的“世界文學”理念格格不入,也與“全球文學”或“世界的文學”理念格格不入。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研究中心;摘自《文藝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