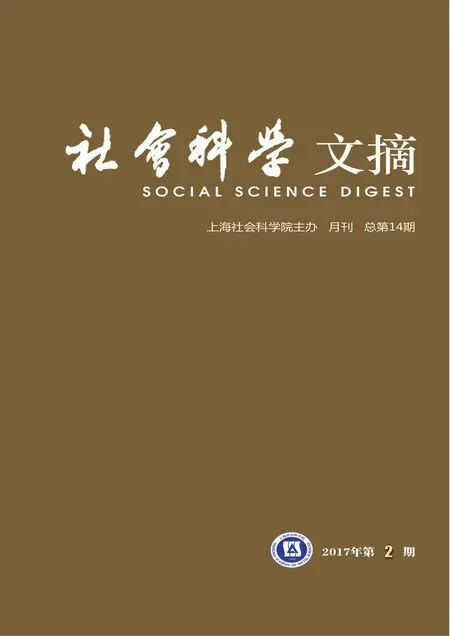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文學冷戰”:大陸赴港“流亡者”與1950年代美國反共宣傳
文/翟韜
“文學冷戰”:大陸赴港“流亡者”與1950年代美國反共宣傳
文/翟韜
近年來美國文化冷戰研究、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美國對外宣傳與文化外交史(又稱“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熱門,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美國政府動員和利用各種文化藝術形式(諸如報刊、電影、音樂舞蹈、運動)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和國際公關活動。其中利用文學形式開展對外宣傳的活動也漸漸為學界所注意,相關研究集中在:中央情報局在喬治·奧威爾小說《動物農場》、《一九八四》的翻譯、傳播、影視改編過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真相運動”中美國情報部門策劃動員蘇聯東歐流亡者撰寫文學傳記小說的活動,美國情報機構和在其歐洲的隱蔽廣播“自由歐洲電臺”和“解放電臺”動員、利用、傳播蘇東的“地下文學”的活動等。較為綜合性的研究也已經出現,它們觀照美國政府在“二戰”和冷戰時期動員和操縱國內外(文學)圖書出版界、以服務于美國外交和政治目的政策與活動。本文則嘗試把美國利用漢語小說進行反共宣傳這一做法的過程完整呈現出來:梳理政策形成情況、描述文本生產過程、分析文本內容,把歷史研究缺乏的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缺乏的歷史情境研究結合起來。
大陸赴港“流亡者”與美國的反共宣傳政策
美國炮制的反共中文文學項目,源于對其針對蘇聯東歐的“文學冷戰”的相關活動。從冷戰爆發到1950年代中期,美國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實行的是“解放戰略”,即通過宣傳和心理戰發動蘇聯和東歐人民群眾來顛覆、瓦解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體制。杜魯門時期美國對外宣傳最高決策機構心理戰略委員會之下有兩大項目來具體實施解放戰略,一是策反蘇聯東歐民眾的“叛逃者項目”,一是促進蘇東人民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的意識形態戰,具體說來是“學說項目”。而“叛逃者項目”和意識形態戰是有交叉的,且越來越靠書籍這一媒介結合在了一起:利用叛逃者個人傳記文學的形式來進行意識形態心理戰,這種媒介形式被學者稱為“冷戰自傳文學”。
冷戰前期,為了消除“紅色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并配合美國的亞洲冷戰戰略,美國在大中華區(尤以東南亞華人為主要目標)展開了浩大的心理戰和宣傳運動。這場反中共的心理戰和宣傳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以香港為中心展開的。香港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文化傳媒資源成為了美國依仗的心理戰和文化宣傳活動中心。在其中大陸赴港“流亡者”群體都扮演了絕對重要的角色。“流亡者”不僅把關于新中國的豐富信息和情報帶到香港,而且與美國在港支持的反共組織和傳媒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最為重要的是,香港之所以擁有豐富和雄厚的傳媒、文化資源與人才,主要就是由于大陸赴港流亡者群體的緣故,1950年代香港的傳媒業和文化界主要是由大陸赴港移民群體構成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冷戰前期美國的反中共宣傳運動就是依托香港這座城市的諸多資源、尤其是大陸赴港“流亡者”群體開展的,因而關注香港“流亡者”群體,便是抓住了美國反中共宣傳運動最重要的一條線索。
從事傳媒行業和其他文化行業、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大陸來港“流亡者”,成為了美國駐香港宣傳機構——香港美國新聞處漢語宣傳材料最主要的稿件和素材來源。美新處在香港遍尋中文作家、編輯、翻譯、新聞記者等合適的人選,來進行符合美國宣傳目標的創作、編輯和翻譯等工作。這對于生活普遍比較窘迫、沒有特別穩定的收入來源的“流亡”知識分子來說,是個難得的改善生活條件的機會。于是雙方一拍即合,在美新處主辦和資助的各種反共宣傳媒介的外圍形成一支龐大的“流亡者”媒體人隊伍,他們是美國在1950年代的反中共宣傳活動的“主力部隊”。
反共小說的生產和發行機制
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的十年之間內,美國駐港宣傳站點逐漸形成了以書刊紙媒為重點的兩大宣傳項目:一是以《今日世界》為代表的多份中文刊物,一是包括翻譯書籍、原創書籍等在內的“書籍項目”。
書籍項目中以反共小說最有特點。香港美新處自1953年開始策劃“反共小說”。美新處評估到,當時很多華僑青年非常反感簡單粗暴的反中共宣傳作品,對那些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進行理論反駁的著作也沒多大興趣。針對這種情況,美新處打算采取一種更加隱蔽和輕松的方式進行反共宣傳。美新處官員打算重點開發反共小說,這類作品“通過把個體人物在不同階段的經歷編成小說(fictionalized)、但同時又是寫實性的敘述和描寫,來達到反共的目的。”當時還沒有中國作家專門從事反共小說創作,美新處積極尋找這方面的作家把其作品推銷到東南亞市場上去。
于是在美國新聞處的精心挑選和組織之下,一批鮮明的反中共題材小說作品被“創作”了出來。其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正是蜚聲世界文壇的華裔女作家張愛玲和她的兩部反共小說《秧歌》及《赤地之戀》。除了反共小說之外,香港美新處還策劃、創作、編譯了一批具有紀實文學和報告文學色彩的反共作品,大部分是以在大陸親歷“苦難”和逃亡為題材,其中以劉紹唐的《紅色中國的叛徒》為代表,該作品被美新處譯為16種文字銷售散發到世界各地。以反共小說和反共紀實文學為代表的反共文學作品漸漸成為美新處極為倚重的一種宣傳媒介,逐漸成為原創類書籍的主要形式。
原創中文書籍的發行環節也是比較巧妙的。美新處主要通過商業出版社簽訂合約的方式出版發行:美新處每一次想要出版圖書,不僅免費給某商業出版社該書的版權,而且還不用該出版社花費人力物力進行策劃和采、編、譯,且發行銷售環節還有保障,因為美新處會以成本價收購所有書籍;而且出版社還有進一步獲利的可能,美新處策劃出版的書籍如果由出版社操作真正進入商業流通領域,所獲得的額外銷售所得會全部歸出版社所有。因而一個常見的現象是,美新處不再回購某書籍之后,該書籍還能繼續發行、銷售、賺錢。如美新處曾在1955年開發過《故事畫報》,制作發行即采取上述機制。1961年準備放棄該媒介。美新處認為出版社就不會再繼續出版了。但過了一段時間卻驚喜地發現《故事畫報》沒有消失,仍以較小的版面在香港和臺灣市面上繼續出版、銷售和流通。對于出版社來說,這樣運作的好處非常多,很愿意合作。這幾乎是只賺不賠的買賣,最低限度也就是免費獲得一本書的版權,沒什么可損失的。對于美國宣傳部門來說,其實好處更大,這有些類似變相的“資助出版”。盡管政治力量在商業傳媒背后扮演了推動力作用,但不是單純的資助,而是“授之以漁”,盡最大可能性使每一本書籍成為“純粹”的書籍商品。這是一種非常高超的隱蔽宣傳手段,是在把宣傳品“洗白”、包裝成為文學商品。
對小說主題和情節的文化分析
在大陸赴港“流亡者”反共小說中,有兩類主題最為普遍,一是“青年對革命的幻滅”的“醒悟體”,二是“逃離鐵幕、奔向自由”的“流亡體”。
(一)“醒悟體”小說
在眾多“醒悟體”反共小說中,最普遍的一類情節是革命青年由于自身受到政治運動沖擊和目睹了新中國政權的種種“黑暗內幕”之后放棄革命信仰。
“醒悟體”小說情節很多樣、傳達著多種“反革命”道理,但這些小說的共同點可能更加耐人尋味。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毫無例外地都是青少年,而小說情節幾乎都是在重復這些青年對革命的產生幻滅感,最后“告別革命”的程式。這與美國在大中華區的宣傳對象和目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東南亞華僑青年群體(甚至整個大中華區的青年學生群體),一直都是美國在亞洲宣傳的重點之一。反共小說這個宣傳手段的出臺更是直接和對華僑青年的反共宣傳目標有關。在美國對華人青年進行冷戰宣傳這個大背景下解讀以上反共小說,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文學作品具有強烈的心理戰和宣傳題圖,可以說是精準地為美國宣傳政策量身定做的材料。
這種小說情節的設置,除了反映出政策意圖之外,更饒有意味地反映了美國精英看待革命的深層次文化心理。大體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國政學兩界——對外宣傳官員乃至外交精英和社會科學主流的“現代化”理論家群體——有一套高度一致的對革命和革命者的觀念、且多以社會科學話語形式表達:革命者多是沒有社會關愛和家庭關愛的邊緣人群,參加革命是為了克服嚴重的焦慮和空虛等精神病癥。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他們失去了傳統文化這一精神寄托,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陷入了對自身政治身份迷茫不安的“認同危機”之中,于是加入共產黨想要尋求秩序感和歸屬感。總之,這種觀念把革命者視為地位邊緣、缺少社會關愛的精神病人。
我們看到“醒悟體”小說主人公大都是孤兒,這種人物身份的設置正是典型地反映了上述美國宣傳官員對待革命和革命者“社會病理”診斷。《赤地之戀》中的葉占奎、康悌、《出籠鳥》中的陸素綾、《仇恨》中的云峰等等都是孤兒,即這些曾經篤信革命、堅定的共產黨員都是缺乏家庭和社會關愛的人群。我們還可以看到,這類小說的結局也恰是上述“理論”為“精神病患者”開出的“藥方”。上述主人公的一個主要的結局就是最終回歸家庭和社會,革命者“回家”的結局頗為符合社會科學家的“社會病理”診斷思路:家庭倫理和社會關愛可以提供秩序和歸屬感,是替代革命和黨組織“醫治”革命者孤獨不安的精神病癥的歸宿。
(二)“流亡體”小說
由于香港的傳媒業和文化教育界主要由流亡知識分子組成,所以由香港美新處請其捉刀的作品,多是以他們在大陸生活的經歷、逃亡過程和到港后的流亡生活為題材。因而“逃離鐵幕、投奔自由”的“流亡體”小說,是美國在大中華區炮制的反共文學作品群體中最“主流”題目。香港美新處采取各種手段挖掘和宣傳流亡者“逃離鐵幕、奔向自由”的題目。美新處認為這種“我在場”、“發生在我身上”個人親歷式的逃亡經歷,在大中華區尤其在東南亞華人中是非常有效的宣傳素材。美新處把這些素材制作成廣播節目,在香港和東南亞地區播放。站點還邀請“流亡者”去海外演講,甚至還組織大陸“流亡者”去東南亞華人學校從事教學活動。相關信息也被整理成英文提供給東亞以外的美國宣傳站點,在世界范圍內宣傳大陸“流亡者”的話題。
香港美新處最經常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流亡者素材編輯成平面媒體材料,多以新聞報道、紀實文學、個人自傳、小說等形式面世,美新處采取各種手段把這些媒體材料在報紙、雜志上刊載,或是單獨以書籍、畫報和小冊子的形式出版發行。由于“逃亡”的主題帶有極為明顯的個人親歷特點,又多有復雜曲折的情節和較強的故事性,所以最經常被改編和創作為紀實文學與小說的形式,這構成了美國在港炮制的反共文學的主體部分。紀實類流亡文學作品多以第一人稱自述的形式敘述,情節比較程式化,主要是三段式:在大陸的悲慘遭遇、逃亡經歷、“點題”的結尾,往往是“我終于到達了自由世界”、“我終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之類的結語。題目也多是“我從××來”、“我××(如何)投向自由”。
當然,不僅是鋪陳逃亡的情節,更重要的是把“流亡”這一行為賦予在冷戰雙方中做出選擇的象征意義。在反共文學(也是所有的宣傳材料)中,美國宣傳部門把香港建構為“東方西柏林”、“自由燈塔”的象征,將流亡行為賦予濃厚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在這里,流亡者由于各種政治、經濟、心理恐慌等原因逃亡香港的行為,被賦予高度政治化的解讀:是在冷戰中“用腳投票的義舉”,是一種“逃離鐵幕、奔向自由”的行為,是人民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之間做出正式選擇的象征性舉動。
美國宣傳部門還在把難民赴港建構為一種類似宗教朝圣般的舉動。反共小說中描寫了很多“生死逃亡”的細節,著墨最多的就是對流亡者“奔向自由”“虔誠”心情的描寫。以上這些描寫帶有一定的宗教意味,甚至美國宣傳部門也不避諱把“逃亡潮”說成是“一件有歷史意義和世界意義的大事,”這是“《圣經》上出埃及記的重演,”也是“一首悲壯的史詩。”美國宣傳官員之所以把大陸人流亡香港賦予高度意識形態化色彩,甚至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恐怕是因為美國人把對自身起源的神話和對自我身份的想象投射到了“流亡香港”這個冷戰事件中。美國人把祖先從歐洲移民新大陸的歷史建構為一種“宗教流亡”的歷程,他們“將新英格蘭視為上帝為人類準備的一個特殊避難所”。在冷戰的高潮時代,當美國人執著地用自由與奴役之間的斗爭想象著冷戰的時候,也把西柏林和香港想象成是為愛好自由的人們準備的一個“特殊避難所”,是反抗專制與共產主義的“堡壘”,而涌入西柏林的德國人和涌入香港的大陸人,和心向新耶路撒冷“應許之地”的美國祖先朝圣者一樣,也是一群心向自由、虔誠堅貞的“義士”。
結語
美國宣傳機構對華“文學冷戰”擁有一定的宣傳效果。一方面,反共文學作品發行量大,散播范圍廣,可以大體判斷閱讀人群數量較多、受眾面較寬。另一方面,從中國大陸所見一些史料來看,美國在香港制作的反共文學作品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滲透進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這種效果很大程度上和小說獨特的優勢有關。比起文化冷戰常采取的其他形式如音樂、舞蹈、體育、博覽會、教育交流等,文學和小說、尤其是個人傳記這一小說形式,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化宣傳媒介。其突出特點是可以給讀者提供一種“個人親歷性”,通過文學語言和生活情境,小說可以迅速把讀者帶入作品的內部世界中去,使讀者“親歷”作者的經歷。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密切相關的進程:一是把政治話題“人性化”,即把反共和親西方的立場與信息通過個人經歷、人類情感和曲折情節傳達和呈現出來;二是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即把冷戰意識形態斗爭的話題簡單地和集中體現在個人經歷變故之后的思想斗爭和人生選擇上。這樣就把文學傳記和政治意識形態滲透這兩個本不太相關的事物很好地結合起來,實現了所謂的“反共意識形態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Anti-communist Ideology)。搞清這個本質也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美國對華宣傳的技巧。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摘自《世界歷史》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