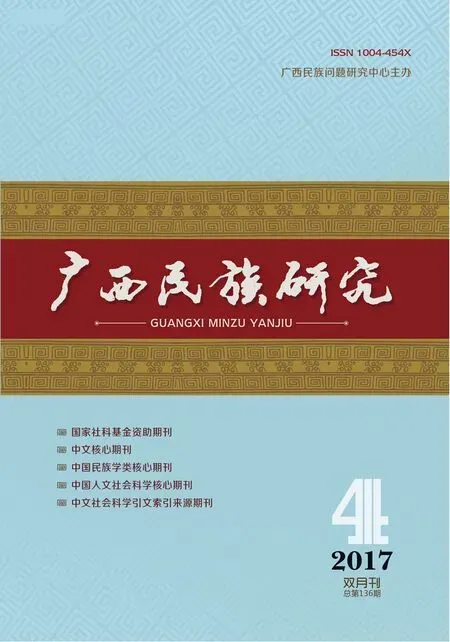駱越古語和漢語同源詞研究*
蒙元耀
駱越古語和漢語同源詞研究*
蒙元耀
壯侗諸族順承西甌駱越而來,西甌駱越是百越的重要一支,百越與東夷有密切的聯系,這可以從壯傣、布依、黎等民族的自稱得到旁證。族稱、動植物名稱中的古老詞匯蘊涵著豐富的語言學內容,通過古籍的鉤稽與比較研究,可以解釋現今壯侗語族與周邊相關語言的親疏關系。
駱越語;古漢語;同源詞;關系研究
百越與東夷有歷史淵源,語言方面也有密切聯系。西甌駱越是百越之中的重要支系,而現今壯侗語民族與之有明顯承接的關系,所以,探討駱越古語和漢語的同源詞問題,其實就是探討壯侗語族和漢語的語言歷史問題。西甌駱越是壯侗語族的直接先民,從今天的海南、兩廣一直到云貴高原東部,這一帶都是西甌駱越人分布的故地。要研究駱越語和漢語的淵源,可以從族稱、常見動植物名稱、地名以及天文地理、日常事物、常用動詞形容詞入手。這幾個方面的基本詞匯不僅讀音穩固,而且詞義也很穩固。借助語音和詞義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駱越語和漢語之間的確存在緊密的淵源關系。
一、族 稱
族稱是一個群團的外在標志,其含義一般來說是比較固定的。透過族稱,我們可以觀察到壯族先民跟漢族的關系。壯侗語諸民族順承百越而來,而百越與東夷又有密切聯系,這可以從壯、傣、布依、黎等族稱得到旁證。
1.tai2
傣族自稱tai2,廣西龍州金龍和大新寶圩的部分壯族也自稱tai2,云南富寧、文山、廣南也有不少壯族同樣自稱tai2。
這個族稱非常古老,直接能跟“夷”對應。根據古漢語研究成果,在上古,“夷”讀如“弟”,這就是說,上古時期“夷”和“弟”同音。所以,鵜鶘的“鵜”在《說文解字》中也寫做“鴺”。[1]153鼻涕的“涕”,也寫成“洟”。《說文解字》水部:“洟,鼻液也。”[1]565而“涕,泣也”。涕的本義是哭泣。壯語至今還是把“哭”說是tai3。“涕”引申為眼淚。如:“感激涕零。”由于洟涕同音,同時也因鼻涕眼淚常同時并舉,如“涕泗滂沱”,所以后人就用“涕”來替代“洟”。
許慎的《說文解字》對“夷”字的解釋是:“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1]493可見,“夷”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動詞,做“平”來解釋,如“夷為平地”。一個是“東方之人”,是名詞。所以古代的東夷,就是居住在東邊沿海的人。《說文解字》解說“大”字:“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1]492“大”“弟”在粵語里音近,夷從大得聲。有方家把“夷”的上古音構擬為*djai2[2]25,如今壯、傣、泰的自稱tai2與之相去不遠。由此推知,用這一族稱的人,當是古代“夷”人的后裔。傣語、泰語都有把“人”說成tai2的說法,如“龍州人”即tai2lu?2tsou1。①此為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范宏貴先生告知。范教授系龍州壯族人士,曾在云南學習、工作,對傣語泰語有豐富的知識。從這一點來看,自稱為tai2的壯傣語支其實就是保持了古代“夷”這一古老族稱的群團。
2.lai2
海南的黎族自稱lai2,黎族是壯侗語族的民族之一,自然也是駱越后裔。lai2當源自于古代的俚人。過去壯侗語民族也曾有“俚僚”之稱。俚人的分布不止在海南一島,兩廣地帶也很多見。周去非《嶺外代答》載:“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為聲音,殊不可曉,謂之蔞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于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僚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言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蜑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3]144-145可見宋代時期,廣西欽州一帶還有俚人居住。
追尋起來,lai2雖是記錄“俚、黎”之音,但其根基仍在“夷”。前邊說了,“夷”在上古讀如“弟”,為*djai2,而壯漢語之間或者駱越語和漢語之間,有t-,th-=l-的聲母對應關系。如“銅”是人類最早普遍使用的金屬,上古漢語叫*d??,中古叫*du?,壯語里“銅”的說法有to?2、lu??2兩個音。通常的意見認為to?2是漢語借詞,lu??2才是壯語固有詞。但這兩個讀音均可能來自“東夷—百越”語言。因為商朝時中國銅器才猛然興盛,而商朝是東夷人的一支進入中原后才建立的,故也可以說,“銅”的這兩個讀音很可能是同一來源的詞所分化。鄭張尚芳就認為“銅”可能是漢語向臺語②臺語即壯傣語支在國際上的通行說法。借用的。[4]232
作為旁證,“落”在壯語是tok7,粵語是lok8,上古漢語是*l?k[5]56;“梯”在壯語是lai1,粵語是th?i1,上古漢語是*thiei[5]127;“多”在壯語是lai1,粵語是to1,上古漢語是*ta[5]52。此外,壯語里“削”有ta:t7、la:t7兩種說法,“小片、小塊”也有tip7、lip7,“奪”也有tu:t7、lu:t7兩說。
最明顯的是“脫”,壯語有tu:t7、lu:t7兩個說法。前者用于“脫”衣服、擺脫等,后者用于脫離、脫落、滑脫、脫手而出等。
可見t-,th-與l-的聲母交替現象是常見的表現。所以,“夷”演變為“俚”是一種語音歷史變化形式。
3.jai4/3
貴州布依族自稱pu4jai4,廣西壯族也有不少人自稱pou4jai3、pou4jui3或pou4jiai3等。pu4或pou4是“人”的大類別詞。jai4/3或jui3是族稱,探究起來,這個詞同樣是“夷”的音變形式。
先從韻母說起。如今“夷”的韻母是-i,漢語的-i韻有對應為壯語布依語-ai韻的變化規律。如“西”,壯語是θai1;“細”,壯語是θai5;“雞”,壯語是kai5;“題”,壯語是tai2;“迷”,壯語是mai2;“底”,壯語是tai3;“泥”,壯語是nai2。可見,“夷”變成布依語、壯語的jai4/3、jiai3是很嚴整的對應變化。至于jui3,則是主元音由-a變成了-u而已,它們大體還是在近似對應的范圍之內。
從聲母上看,“夷”聲母的*d-演變為j-,這種對應變化在古漢語研究中稱為“喻四入定”。在漢語,“稻”以“舀”為聲符,“舀”是喻母字。“途”以“余”為聲符,“余”同樣也是喻母字。“偷”以“俞”為聲符,“俞”同樣屬喻母字。另外,“膽、擔、檐、簷”皆從“詹”得聲,然而“膽、擔”今讀t-聲母,而“檐、簷”卻讀j-聲母。在壯漢語之間,這種舌尖音d-、t-演變為j-的現象也不罕見。如“舀”,壯語說法是tak7;“移、搬移”,壯語是tai6。
結合上邊提及的“多”是la:i1,可以說,無論“夷”變化為lai2或是jai4/3、jui3,這些演變都符合壯漢語或者駱越語和古漢語之間的語言發展規律。歸納起來,“夷”的演變途徑大致可以這么描述:
夷是*djai2,當*dj失去腭化音時,就變為dai2,現今岱、傣仍有部分支系用此稱謂;當它清化時,就變為tai2,這是傣族和部分壯族的自稱。當濁聲母*d清化為送氣聲母時,它就演變為thai2,即現今泰、老、撣等支系的族稱。當*dj塞音擦化后,它會變成*ai或*lai,這就是俚或黎的自稱。當*dj的塞音消失時,它會變化為舌面擦音jai4/3,這就是布依族和部分壯族的自稱。
從自稱可以看到,現代的傣、壯(自稱tai2的部分)、布依和黎的族稱均能跟“夷”的古音構成直接對應。
二、動物名稱
人類長期與動物為伍,即使從森林走到平地建立起人類社會,人們依舊與各種動物有著密切聯系。從動物名稱可以看到百越語和漢語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不少動物名稱蘊含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從生活環境考慮,這些動物很常見,其名稱是語言之中的基本詞匯,借助這些動物名稱,我們可以觀察到:越是古代的常見動物,其名稱的共同性就越大。如“豹”,壯語是peu5,“貓”壯語是meu2,“鹿”壯語是lok8,這些動物的名稱就非常對應。豹在古代是廣泛分布的猛獸,貓是人類早期馴養的動物,鹿是古人的狩獵對象,是重要肉食來源之一。這種語言之間的共性,不好簡單地說是互相借用的結果。下邊幾例就很能說明問題。
1.????6
象是陸地上的大型動物。人類對大象的認識應該是很古老的事情。在古代中國,大象從南到北一直分布到黃河流域。甲骨文里已經出現了“象”字。古老傳說里,舜帝時就有了“象耕鳥田”之說。在云南、泰國、老撾等地,還可以看到人們至今仍役使大象來從事某種勞動。可見大象與人的關系非常密切。
壯語稱“象”為????6,這是一個語族同源詞。壯語、傣語、布依語、侗語、水語、仫佬語、毛南語以及廣東連山一帶的標話都有一致或近似的說法。泰語、老撾語、緬甸語的說法也有嚴整對應。許慎的《說文解字》象部說:“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1]459象是喜溫動物,可見在漢代,中國的大象當是南方比中原更為常見。從《說文》的記載看,“象”大體可以推定是南方越人的詞語,假如不是同源詞,那就是漢語向百越語借用了“象”這個詞。[6]96-97
2.wa?i2
壯語稱水牛為wa?i2,侗語叫kwe2。水牛也是陸地上的大型動物,百越民族對水牛的認識很古老。在河姆渡考古遺址里就發現大量的水牛骨頭和牛肩胛骨做的骨耜。牛是農民的寶貝,自古以來牛就是農耕民族的基本詞匯之一。然而壯語的wa:i2與漢語的“牛”字不對應,與之對應的是“犩”。
犩也寫成犪。《爾雅·釋畜》有“犩牛”。郭璞注:“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7]405《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8]183犩從魏得聲,上古音構擬*?ǐw?i。[5]219“魏”今音wèi,與壯語的wa?i2相近。
水牛力大,喜水,不耐寒,是南方的動物,也是稻作生產的重要畜力。而稻作農耕是百越民族的主要謀生方式,可以推想,水牛應是古越人最早馴服的牲畜之一。wa?i2與犩應是同出一源的字。
3.kop7
田雞叫黑斑蛙,壯語的說法是kop7。kop7對應為漢語的“蛤”。粵語稱田雞為k?p7,平話叫kap7。蛤從合得聲,上古音構擬為*k p。[5]24蛤在上古可指貝類,也可指蛙類。當蛤指蛙類時,常作青蛙和蟾蜍的通稱。唐代劉恂《嶺表錄異》:“有鄉墅小兒,因牧牛,聞田中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9]44清朝李調元《南越筆記》卷十一:“蛤生田間,名田雞。”①轉引自《漢字大字典》 (縮印本)第1189頁,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
蛙類是田野間的常見動物,兩棲,喜溫喜水。氣溫降低后要冬眠。南方水網密布,高溫天氣的時間長。無論如何,蛙類的常見度要比北方高,百越人不可能缺失這一概念。現今壯語、布依語、傣語、泰語、老撾語、拉珈語均說是kop7,仫佬語、毛南語、莫語的說法也與此近似,我們可以推定,kop7不僅是壯侗語族的同源詞,無疑也是百越和漢語之間的一個同源詞。
其實,不但是kop7與蛤對應,壯語的kwe3也能與“蛙”對應,筆者在《壯漢語同源詞研究》一書里有詳細申說,此不展開。[6]140-142
4.ta??6
壯語叫蛇為ta:?6。這一說法與漢語的“它”能構成嚴整對應。《說文》它部:“它,蟲也。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從它。”[1]678
“它”是蛇的本字。在甲骨文里“它”就是一個面目猙獰的三角蛇頭形象。后來“它”被挪作虛詞使用,人們就在“它”之前加上“蟲”而另構成新字。漢語的“拕”從“它”得聲,上古時與“它”同音。《說文》手部:“拕,曳也,從手它聲。”[1]610在甲骨文里,拕就是以手拖蛇的會意字。[10]219拖,壯語說ta2。
拕(拖)的ta2與蛇的ta??6在音韻學上稱為陰陽對轉。這種語音演變在古漢語或漢壯語之間是常見現象。如“蚆”指兩頭尖中間寬的貝類,“蚌”也是貝類。漢語的“肚、鼓、孥”對應到壯語分別是tu?4、kjo??1、nu??4。利用這種傳統的音韻演變規律,我們可以找出許多過去不曾留意的同源詞。因為蛇是中國南方的常見動物,百越人不可能缺少這個常用詞而向另外的語言借用。這種隱蔽的對應很能說明兩種語言之間的原本關系。
與此相關,蚺是蟒,虺也是蛇,它們跟壯語的num1(蟒)、??2(蛇)也能構成嚴整對應。[6]131-136這些對應現象呈現出來的語言關系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這應該不是簡單互借問題。其背后隱含的語音規律表明,這兩個群團在上古很可能存在語言發生學的關系。
三、植物名稱
植物與人們的生活也是息息相關。駱越語和漢語之間,有不少植物名稱能構成嚴整對應。特別是南方百越地區的特產,根本就不好說是百越人向漢語借用這些植物名稱。
1.kwi5
壯語稱肉桂為ko1kwi5。廣西簡稱桂,是因盛產肉桂而得。肉桂是出名的樟科植物。壯語還有ka?u3kwi5、ka?u3no6、ka?u3fei2、?ok8kwi5等稱謂。?ok8是肉的漢借詞讀音,kwi5,是桂。壯語把許多樟科植物稱為ko1ka?u3,即栲樹。no6即肉,故ka?u3no6是肉栲;fei2是火,因壯醫認為肉桂是溫熱屬性的藥物,故而得名,ka?u3fei2即火栲。ka?u3kwi5則是桂栲。
肉桂是上乘的傳統藥材,與人參、鹿茸齊名。醫家素來重視肉桂。《山海經》開首就說:“南山經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8]1《說文》木部:“桂,江南木,百藥之長。”[1]240“梫,桂也。”[1]239《爾雅》釋木:“梫,木桂。”郭璞注:“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為木桂。”[7]329木桂即肉桂。①轉引自《漢字大字典》 (縮印本),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桂見第501頁,梫見第513頁,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從古籍里傳遞出來的信息是,桂乃南人對肉桂的命名。遠在上古時代肉桂就已經是中國南方的名藥。東漢年間成書的中國現存最早的本草書《神農本草經》載有365味藥材,壯族地區盛產的菌桂、牡桂就赫然在列,[11]346可見壯族先民認識并利用這一藥物由來已久。
既然“桂”是南人的說法,其初始源頭當出自百越語。毫無疑問,把“桂”看成兩種語言的同源詞也應該沒有問題。
2.?u??1
樟樹在壯語叫ko1?u??1、ka?u3?u??1,ko1是棵,?u??1是樟,ka?u3即栲。樟樹是多用途的優質樹材,著眼于木材,也叫fai4?u??1,fai4即樹、樹木、木材。樟樹木材的耐久性好,加工容易,建筑上用做梁、柱、窗、樓梯等。用來作衣箱書柜特佳,其芳香氣味使蠹蟲不敢接近。木材、根、枝、葉可以提取樟腦和樟油。根、果、皮、葉均可入藥。
不須繁瑣考據,從?u??1之音就可以看出它跟“樟”的讀音對應。樟樹盛產于中國南方,可以推斷,其初始的命名者,也應該是百越人。除了樟樹外,像?u??1he?n3是黃樟,?u??1jou2是油樟,?u??1pja1是巖樟,這些都是優質材用樹種。
3.to?3
壯語叫橙為to?3。橙是中國南方高產的水果。《說文》木部:“橙,橘屬,從木登聲。”[1]238從登得聲的字,如“燈”,壯語是ta?1;“凳”,壯語是ta?5;“鄧”,壯語是ta?6;“瞪”,壯語是?a?2。這些字的韻母都是a?,與橙的韻母有一定的差異。可見橙讀to?3跟這些字的語音不是同屬一個歷史層次。
根據農史與考古材料,橙起源于中國的東南沿海。從原產地來推究,這應是百越人最先栽培的果類。從事理上判斷,如此好吃且又豐產的植物,百越人不可能缺少表達其概念的詞。基于中原不產橙子的事實,大體可以認定,“橙”是越人最先命名的植物。
與橙相似,柑也是起源于中國東南沿海的水果。橙、柑都是蕓香科植物。壯語稱“柑”為ka:m1。柑從甘得聲,甘在壯語也讀ka:m1。疳也從甘得聲,壯語一樣說是ka:m1。
四、結 論
總結前邊的討論,可以看到,族稱和動植物名稱蘊涵著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透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到西甌駱越的語言跟漢語有不可否認的直接聯系。像這些植物專名根本就不須構擬,一眼就能看出它們在壯漢兩種語言里有嚴整對應。假如我們認可這些詞具有足夠的古老性,而且也承認壯侗諸語傳承自西甌駱越語言,不必舉更多的例子,我們有理由相信,壯侗語或西甌駱越語跟古漢語必定存在淵源關系。這種淵源關系的糾結點就在東夷人身上。
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標志,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和傳承性。通過古籍資料勾稽與語言比較研究,借助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方法,可以探查古代駱越語言的狀況,解釋現今壯侗語族語言與東南亞相關語言的親疏關系。重點是研究壯侗語族與東南亞語言核心詞的異同情況。從歷史角度理清東夷、百越、駱越乃至現今壯傣語支重要族稱的音義由來及演變形式。從《越人歌》 《維甲令》《山海經》等古籍查找相關古越語的材料,利用漢字古音構擬來跟壯侗語族語言語音作對比研究,解釋語音演變規律及變化形式;找出壯傣語支一批核心詞來進行比較研究,看它們在語支、語族甚至周邊語言里的對應情況,總結相關的語音對應規律,進而解釋語言間異同情況的文化原因。運用以上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對百越語、上古漢語及現代壯侗諸語的重要詞目進行比較,可以探索駱越語言的特點與傳承,借助語言分布研究,能夠揭示西甌駱越及其后裔在中國南方相應的分布情況。
[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羅美珍.羅美珍自選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周去非.嶺外代答[M].楊泉武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4]鄭張尚芳.語言同源與接觸的鑒別問題[C]//薛才德.語言接觸與語言比較.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5]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6]蒙元耀.壯漢語同源詞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7]胡奇光,方環海撰.爾雅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方韜譯注.山海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5.
[9]劉恂.嶺表錄異[M].商璧,潘博校補.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
[10]熊國英.圖釋古漢字[M].濟南:齊魯書社,2006.
[11]覃尚文,陳國清.壯族科學技術史[M].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A RESEARCH TO THE HOMOGENOUS VOCABULARY OF ANCIENT LUOYUE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
Meng Yuanyao
The ethnic groups of nowadays Kam-Tai linguistic family come from the Xiou and the Luoyue,an important division of the Beiyue ethnic group.The 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iyue and the eastern Yi ethnic group can be demonstrated from the self-claiming of the Zhuang and Thai,the Buyi and the Li etc..The old vocabularies of the names of ethnic groups,animals and plants contain rich linguistic substances.By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the closed or remo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nguages of ethnic groups of nowadays Kam-Tai linguistic family and that of the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can be revealed.
language of the Luoyue;ancient Chinese language;homogenous vocabulary;relation studies
H0-05【文獻識別碼】A
1004-454X(2017)04-0087-005
﹝責任編輯:陸 露﹞
蒙元耀,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院語言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南寧,53000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駱越文化研究”(16@ZH010)專項課題“駱越語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