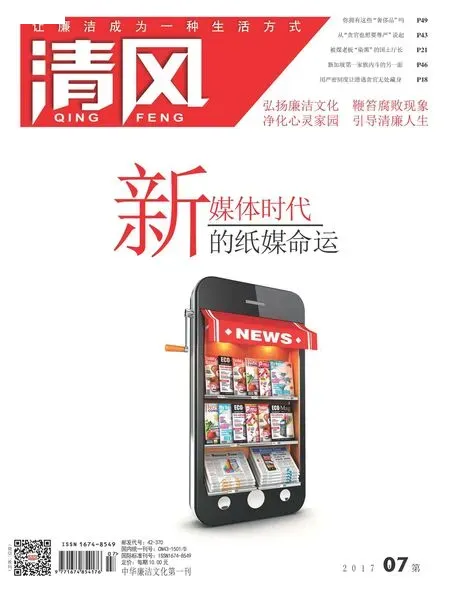從官員到市民的紙媒情結
文_本刊記者(發自北京、武漢)
從官員到市民的紙媒情結
文_本刊記者(發自北京、武漢)
關于紙媒體,人們都不陌生,尤其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各類人群,可以說是與紙媒體接觸最多的群體。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本刊記者也十多年如一日天天瀏覽紙媒體,在與各界人群打交道時自然也經常談起紙媒體的現狀、前途等話題。從本刊記者獲悉的大量信息來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雖然幾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機,但不少人依然對紙媒體有一種割舍不下的“情結”。
跳出大家各抒己見的個人觀點,以及他們對紙媒體深淺不一的情節來看,不能回避的是,在以手機終端等為載體形式的電子媒介的介入下,紙媒體的生存環境無疑受到很大的挑戰,但是,從官員到普通市民,很多人對紙媒體的“戀情”不會消亡。而如何順應電子媒介時代,如何在電子媒介時代贏得生存和發展空間,已然成為紙媒體留住人們眼光的新的任務。
近期采訪的關于紙媒的故事
如果一天不看報,就感覺少了點什么似的。我不習慣在手機上分析新聞內容。
本刊記者在北京、武漢、長沙等地采訪時,注意到當地政府官員和普通群眾對紙媒體的看法及態度。本刊記者數次到北京市采訪,與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會長河山、海淀區中關村法庭的法官陳昶屹等,就讀書的話題進行過深入交談,也談到了紙媒體面臨的現狀。同時,本刊記者還就此話題與在北京、武漢、長沙媒體界工作的多人及其他各界人士進行過探討。現舉數例,從中可以窺見人們對紙媒體的情結與心態。
河山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本刊記者在北京東城區采訪他時,了解了一些鮮為人知的背后細節。河山在舉例分析一些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問題時,反復講到:“我高度關注報紙雜志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案例。”他說,一次他看到某報紙報道了“打假人士”的故事時,高興得一拍大腿:“我一直在留意這種事例,第一次從報紙上看到這種事例時,感到特別興奮,因為報紙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這等于通過報紙這種權威渠道告訴大家:買到假貨是可以維權的。”看書讀報,已經成為河山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令記者略感意外的是,河山對智能手機的使用卻并不嫻熟,他說,一次他無意中觸碰了手機中的某一處功能,結果自動下載了一款付費游戲軟件,在沒得到他允許的情況下扣走了他15元錢。為此,他還專門到北京的當地法院起訴網絡供應商侵權。
陳昶屹過去在海淀區基層法庭十年的工作時間里,攻讀了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網絡法方向博士后,成為北京基層派出法庭的唯一一名博士后法官。在很多人看來,陳昶屹選擇的是一條“清水”之路,“我的一些大學同學畢業后進了中央某些部委工作,也有的選擇了經商致富。”然而,陳昶屹卻耐得住寂寞,一頭扎進了基層工作與書海中。陳昶屹對本刊記者說:“我將讀書看報當做生活的重要內容。”正是堅持讀書看報,極大豐富了他的知識,也讓他成了遠近聞名的一名優秀基層法官。
還有一次,本刊記者在北京采訪,與數位媒體界人士一起就餐時,大家在飯桌上談興正濃,一位北京某雜志社的編輯推門而入:“不好意思,剛才去買報紙了,所以來遲了一會兒。”該編輯進入餐館時,夾著一大包報紙雜志及相關資料。本刊記者特意翻閱了他攜帶的報刊,發現有當天北京市出版發行的三份報紙、兩本雜志,還有網絡設計方面的專業書籍。本刊記者問:“今天的報紙有什么重要新聞,值得你在吃飯之前匆匆去買?在手機上看不是一樣的嗎?”該編輯回答:“多年的習慣了,如果一天不看報,就感覺少了點什么似的。我不習慣在手機上分析新聞內容。”
本刊記者近日到武漢采訪時,被身披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光環”的村官霍計武所震撼。在信息相對閉塞、交通不便的偏遠山村里,霍計武靠什么來打發業余時間,是否感到孤獨寂寞?面對本刊記者這樣的問題,霍計武淡然一笑:“這里肯定是無法與城里的繁華相比的,讀書、看報,這是我打發晚上時間的主要方式,更是我充實自己的一種主要途徑。”霍計武對本刊記者表示,凡是村里、鄉里訂閱的報紙雜志,他幾乎都看了個遍。
“紙媒能給人安全感、信任感”
權威的政策發布、消息來源,通過紙質報紙傳播,能給人一種安全感、信任感、確定感。
紙媒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信息傳播渠道,但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新媒體也同樣不再陌生。既瀏覽手機、電腦,也讀書看報紙雜志,越來越成為更多人獲取信息的雙重渠道。黨政官員大多公務繁忙,他們是否還讀書看報呢?本刊記者在采訪中曾問過多位政府官員:“如果在智能手機與紙質報刊中二選一,您會選哪一種?”被問者一般都會表示,二者都必不可少,但紙質報刊的權威性更高。一位受訪者思考了一下,說:“如果非得二選一,我想我還是會選擇紙質報刊吧,因為權威的政策發布、消息來源,通過紙質報刊傳播,能給人一種安全感、信任感、確定感。”
“今天,干部怎樣讀報?”調查這個問題無疑是個龐大的工程。但來自中國最權威的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調查給出了部分內容的答案。2016年4月13日至20日,《人民日報》“要聞四版”與人民論壇雜志社合作,在廣東省僑聯等多個單位的協助下,對黨政干部讀報習慣和偏好等進行了調查。
調查稱,超過九成受訪干部每天會抽出時間讀報,40.54%的受訪干部每天用于讀報的時間在半小時以上,有13.51%的受訪干部達到1小時以上。為工作而讀報,是所有接受采訪的黨政干部們提及的共同目的。調查中,超九成受訪干部認為讀報對自己工作有幫助,認為幫助較大的占35.47%。
而普通市民對紙質媒體的態度,從本刊記者在街頭巷尾的偶見偶聞也可窺其一斑。近日,本刊記者周末去烈士公園游覽時,就看到幾位讀者正在翻看報刊亭里當天的報紙。據一位正在看報的讀者介紹,他每次路過這里時都會隨手翻一翻,雖然很多新聞在網上已經看到,但從報紙上看到的感覺不一樣。
新媒體不是紙媒的“掘墓人”
傳統紙媒具有權威性、公信力屬性,它所蘊含的文化質感,隨著互聯網的興盛,鋒芒會越發顯現。
為什么新媒體突飛猛進的今天,仍然有這么多人對紙質媒體“戀戀不舍”呢?按照記者采訪的諸多人士的說法,是現在人人一部智能手機,當然絕大多數人是“離不開”手機的,但是,他們也都有類似的觀點:“手機再怎么便捷,也不可能有紙媒體的權威性。”一位報業人士進一步給出了專業性的解釋:傳統紙媒具有權威性、公信力屬性,它所蘊含的文化質感,隨著互聯網的興盛,鋒芒會越發顯現。互聯網網民人群愈發大眾化,而紙媒讀者愈發精英化。紙媒深度報道所特有的力度和思想性,構建了紙媒平臺的卓越影響力。
然而,不得不面對的是,新興電子媒體已成燎原之勢,幾乎滲透到了每個人的工作與生活中。一些紙媒體在新媒體的沖擊下,一度轉型甚至放棄了紙質媒介的傳播形式。但新媒體“江湖”也不可能一帆風順,泥沙俱下之下,一些紙媒體又重新選擇紙質媒介為載體,這是一次理性回歸。
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仍然是紙媒體的優勢在起作用。作家吳興人在文章中列舉紙媒體的優勢時分析:第一,是紙媒體的直觀性和方便性。一紙在手,可無須借助其他任何工具、不受場地的限制來獲取新聞。而廣播、電視、手機報以及網絡媒體等都要有個終端。第二,紙媒體新聞報道的權威性。中國內地絕大多數紙媒體的背景是以黨報為核心的報業集團,有著嚴密的新聞采編和發布流程,其新聞的原創性、真實性、權威性、社會分析能力、社會導向能力和強大的傳播能力是其他任何新興媒體無法比擬的。第三,紙媒體的研閱性。紙媒體對新聞的闡釋、對新聞的解讀也是其他媒體無法取代的。
最為媒體界人士所熟知的,莫過于《紐約時報》報道過的一則新聞:美國《新聞周刊》是擁有80年歷史的老牌新聞雜志,在過去幾年經歷了慘痛的變故。“《新聞周刊》在關停紙質版整整一年后,這本艱苦斗爭的周刊即將重返報刊市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周葆華認為,《新聞周刊》重推紙質版,是對新的經營模式和銷售模式的一種探索。
另一則來自印度紙媒體逆勢而上的消息則更加振奮人心。據CNN報道,今天,以報紙和雜志為代表的印刷媒體出版物在全球各地的銷量已經日趨衰落,但在印度國內的情境卻完全相反,沒有顯示出受到互聯網影響的跡象。近日,印度審計部門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從2006年開始到2016年為止的10年時間里,印度國內每天的報紙印刷量已經增加至2300萬份以上,其每年的增長幅度接近5%。盡管印度政府和部分高科技企業如谷歌、Facebook等,希望將這個國家的13億人口更多地帶入互聯網領域,但該國民眾對傳統印刷出版物的需求仍在增長。對出版商而言,更多的讀者意味著自己會擁有更高的收入。據預測,截止到2021年時,印度出版印刷業拉動的廣告收入,將會從2016年的2000億盧比(約合31億美元)上升到未來的3000億盧比(約合45億美元)。根據印度審計部門的預測,未來,印度國內傳統印刷媒體產業的產值將會達到67億美元左右。
在紙媒體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大背景下,紙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的發展新模式,在中國各地都已風起云涌,無論到哪家報社或雜志社,“創新傳統媒體,發展新媒體”幾乎成為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社長程穎剛提出了一種獨樹一幟的見解:新興媒體并不會成為紙媒體的“掘墓人”。相反,紙媒體如果充分利用好支撐在新興媒體背后的新技術,反而會如虎添翼。無疑,在新媒體興起的今天,紙媒體仍然具有天然的優勢,對此,權威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也刊文稱,新媒體不是紙媒體的“掘墓人”。事實正在證明、也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證實,這一結論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