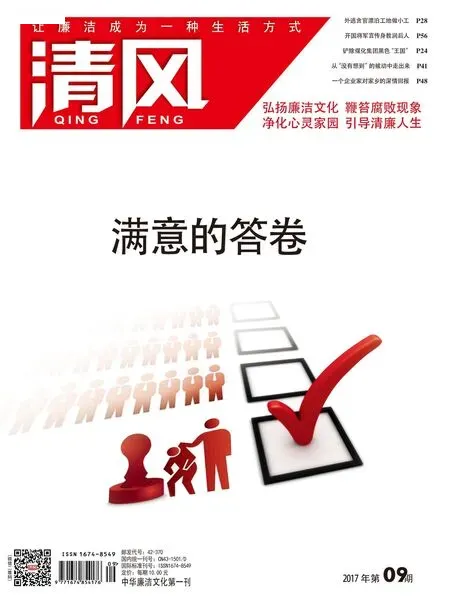張居正的選人用人觀
文_張桂輝(福建廈門)
張居正的選人用人觀
文_張桂輝(福建廈門)
張居正四十三歲入閣,四十八歲為內閣首輔(明中期后相當于宰相)。他當國初期,正值嚴嵩父子亂國之后,政治上混亂、腐敗,經濟上處于崩潰的邊緣。擺在張居正面前最棘手的,無疑是經濟問題,尤其是如何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問題。不過,在張居正看來,財政問題只是表象,而改革面臨著更多的深層次問題。比如,庶官瘝曠、吏治因循等“積弊”。
“庶官瘝曠”“吏治因循”,指的是官員貪腐與庸懶。長期以來,由于吏治不清,官場上充滿了各種形式主義,推諉、扯皮、虛飾等,更是屢見不鮮,成為官場常態。官員隊伍中,普遍存在的貪贓枉法現象,既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更讓政令無法得以貫徹實施。面對這些問題,張居正較之其他一些改革家,不但更老練,而且更成熟。他深刻認識到,沒有一支過硬的干部隊伍,再好的頂層設計、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難以落實到位。
有鑒于此,張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使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枯木逢春,重煥生機,被譽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與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等幾次重大改革相比,發生在萬歷年間的張居正變法,是范圍最廣、收效最好的一次改革。張居正變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在于他重整吏治,選賢任能。
古人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張居正選人用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不拘一格,任人唯賢;最核心的一點,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所謂“循吏”,用今天的語言表述,就是那種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困難拋開,把事情做好,讓事實證明、用結果說話的官員。至于“清流”,則是那些擅長夸夸其談,唱功好做功差,說得多干得少,滿腦子道德教化的人。在“循吏”與“清流”之間,張居正態度鮮明,毫不猶豫地啟用前者,毫不客氣地拒絕后者。
張居正任首輔之后,要求三品以上大臣都要向朝廷推薦人才。其中,不少人推薦了海瑞。時任吏部尚書楊博還曾就這個問題專門游說張居正。然而,張居正不為所動,就是不予起用。在張居正眼里,海瑞是一個有道德、善自律的好人,但好人未必就是好官。好官的標準應當是——上讓朝廷放心,下為蒼生增福。而海瑞做官,只有原則,沒有器量;只有操守,缺少靈活,因此有政德,無政績,是一個典型的“清流”,不好使用,不能使用。權衡利弊,張居正果斷決定——擱置海瑞,且一擱十年,且在他執政期間,始終不予起用。
相反,張居正啟用戚繼光時,后者只是個總兵。那時,總兵相當于今天的“省軍區司令”,可上面還有一個總督呢。總督,既是地方的行政長官,又是總兵的頂頭上司。以往,但凡總督和總兵產生矛盾,朝廷撤換的必定是總兵。這幾乎成了“慣例”。張居正恰恰相反——不管他人如何攻擊、怎樣貶損戚繼光,抑或他和總督產生矛盾后,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撤換的都是總督。不僅如此,每個總督上任時,張居正都會親做“任前談話”,明確要求支持戚繼光。正因此,戚繼光擔任薊遼總兵十三年,薊遼沒有發生一次戰爭,蒙古人也沒有一次進犯。辯證地看,這既是戚繼光恪盡職守的功勞,也是張居正知人善任的結果。
政因人興,事在人舉。從萬歷元年到十年,張居正政績斐然。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等,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只得安分守己而與明朝進行和平貿易。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平定。國家富強,國庫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余,超過全國一年的支出。交通驛站,辦得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平。經過張居正的苦心經營,明朝成為彼時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如今在選拔任用干部,尤其是任用“一把手”時,固然要從資歷、能力、口碑等因素加以綜合考慮,但更重要的是,應當考察其責任意識、是否具備敢于擔當的“循吏”精神。因為,只有“循吏”,才能真正肩負起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任。換句話說,只有選拔那些思想敏銳,勇于改革創新,善于開拓進取,腳踏實地、抓鐵留痕的人才,才能最終成就現代化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