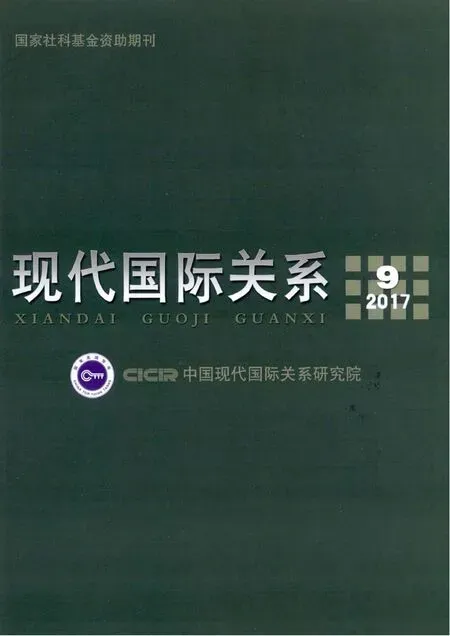歐佩克內部派系之爭的原因、影響及走向
陳騰瀚
歐佩克內部派系之爭的原因、影響及走向
陳騰瀚
歐佩克內部鷹派和鴿派之爭由來已久,引發兩派斗爭內部原因主要有兩派基本國情差異和歐佩克自身組織缺陷;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國際石油市場及外交關系變化等方面。不同時期鷹派與鴿派國家制定相關政策的主導因素不盡相同,但大都呈現出相互對立的狀態。這種派系之爭對國際能源市場、石油輸出國、歐佩克組織自身、中東地區局勢、能源地緣政治等方面的影響不容小覷。從當前鷹鴿兩派國家的關系看, 歐佩克內部派系之爭的未來走勢存在三種可能:走向緩和、保持現狀及走向決裂。
歐佩克 國際能源格局 石油價格 海灣地區
歐佩克組織是當今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國際能源組織之一,于1960年在巴格達成立,創始國包括伊朗、委內瑞拉、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五國,目前共有13個正式成員國。*其他七國分別是:卡塔爾(1961年加入)、利比亞(1962年加入)、阿聯酋(1967年加入)、阿爾及利亞(1969年加入)、尼日利亞(1971年加入)、厄瓜多爾(1973年加入,1992年退出歐佩克,2007年重新加入)、加蓬(1975年加入,1995年退出歐佩克,2016年7月重新加入)、安哥拉(2007年加入)。此外,印度尼西亞(1962年加入,2008年暫停歐佩克成員資格,2015年重新加入)在2016年11月30日召開第171次歐佩克大會之后又再次宣布暫停其成員資格。根據對美關系及政策傾向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派:鷹派、鴿派以及搖擺的中間派。鴿派主要指沙特、阿聯酋、卡塔爾三國,在對美關系上表現為親美親西方;在石油政策上態度溫和,認為油價應該緩慢上漲且保持相對穩定,希望通過調整產量來穩定國際油價,最終目的在于保持石油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鷹派主要指伊朗、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三國,認為在石油定價上應該更加強硬,主張大幅提升油價,在產量政策上一般情況下都希望開足馬力進行生產,在對美和對西方國家態度上與鴿派截然相反。其余七國可被稱作是“搖擺的中間派國家”,但這各有特點:伊拉克和利比亞為偏鷹派國家,科威特為偏鴿派國家,尼日利亞在大部分時間內都保持中立。歐佩克內部的派系之爭自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成為影響歐佩克自身發展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一、歐佩克派系之爭的表現及原因
在歐佩克成立初期,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與矛盾均不明顯。這一階段的歐佩克有三個特點:第一,組織的成立并未受到西方的重視。瑞士政府甚至不肯給其以國際組織應有的外交地位,其總部被迫于1965年遷往維也納。*趙宏圖:《新能源觀——從“戰場”到“市場”的國際能源政治》,中信出版社, 2016年,第145頁。第二,經濟收入是各成員國的主要目標。當時國際石油市場早已飽和,但日益增長的供應使市場過剩不斷擴大,成員無暇顧及合作,只能力求保證自身石油收入。第三,各成員國致力于擴大組織影響力。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取得了部分油價決定權和對石油資源所有權,但仍舊無法掌握國際石油市場的主導權。20世紀70年代可以說是歐佩克的力量達到頂峰的時期,成員國間顯示出了高度一致性。“石油武器”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顯示出巨大威力。但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使國際油價大幅震蕩,歐佩克成員國間嫌隙也逐漸擴大。這一階段西方主要石油消費國的經濟受到了高油價的抑制,開始尋求替代能源并開發新的能源技術,使得國際石油市場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歐佩克市場份額從70%降至43.6%。*張照志、王安建:“歐佩克石油生產配額制度與油價關系研究”,《地球學報》,2010年第31卷第2期,第707頁。石油收入降低使歐佩克放棄了此前的基準油價政策*基準油價政策是指以沙特阿拉伯的34°輕質油價格作為國際油價基準的定價體系政策。,轉而采取生產配額制。但在生產配額制落實過程當中對石油生產的監督管理弱化,成員國的超配額生產等問題不但難以有效應對油價下降,還導致歐佩克組織內部分成員國陷入了國內經濟危機。沙特、卡塔爾、科威特、利比亞等四個國家在這短短5年中國內生產總值降幅均超過了20%。*Gavin Brown, OPEC and the World Energy Market: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2nd ed.), London: Longman, 1991, p.675.經濟上的嚴重受損使各個成員國間出現了矛盾,并在每一次油價階段性下降時進一步加劇。在此期間發生的兩伊戰爭更是使歐佩克內部出現明顯的派系分野。20世紀90年代,歐佩克內部矛盾的烈度有所降低,這主要受外界因素影響:蘇聯解體使整體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歐佩克各國需要在這一時期內做出相應的對外政策調整,尤其是對美和對西方政策,因此各國對內部矛盾的關注度有所下降;海灣戰爭結束后歐佩克各國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來恢復國內社會經濟,派系斗爭并不是國家的主要任務。另外,歐佩克成員國或者不愿意提高產量(沙特、阿聯酋等),或者無法提高產量(伊拉克、科威特等),這使得它們之間的產油配額結構維持在相對穩定水平*劉冬:“歐佩克石油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國際油價的影響”,《西亞非洲》, 2012年第6期,第48頁。,成員國間相對均衡的石油生產比例也因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派系間矛盾。21世紀初,由于價格帶機制政策*價格帶機制政策,指的是如果歐佩克原油價格連續20天高于每桶28美元或者低于每桶22美元,那么組織內成員國便自動增加或減少原油日產量50萬桶來平衡油價,具體數額則由各成員國按配額比例分配。無力控制國際油價,歐佩克在2005年放棄了該政策,并通過實行松動配額制、調整石油產量、調整石油產能這三大政策使國際石油市場在近十年內都處于適度緊張的狀態。除去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的國際石油市場蕭條外,國際油價大體上呈逐步上升趨勢。該戰略使各成員國獲得了大量收益,也使內部派系矛盾進一步緩和。
自2014年起,歐佩克新一輪矛盾開始顯現并不斷激化。新一輪矛盾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產生于鷹派與鴿派之間的矛盾,包括歐佩克在2015年起是否需要減產,以及2016年歐佩克達成減產協議的具體條件;二是源自于鴿派內部,即卡塔爾與其他鴿派國家的關系及其在中東的地位問題。2014年11月27日維也納會議結束后,沙特宣布2015年石油不減產。這使得自2014年6月開始的油價波動下滑一發不可收拾,國際油價在短短兩個月內迅速暴跌,最低價位跌破了每桶45美元。鴿派國家在這一時期主要考慮石油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希望能夠延緩國際石油市場多極化,并且盡可能多地擠占石油市場,而鷹派國家更多地則是考慮自身的經濟因素。在此期間,委內瑞拉通貨膨脹突破400%,經濟和社會陷入雙重危機,伊朗則是受到核制裁和不減產的雙重打擊。盡管2016年底歐佩克決定實施減產,但成員國間的不信任卻隨著時間的推移進一步加劇。2016年11月,歐佩克才正式開始協商并實施減產協議。但沙特和伊朗兩國對市場份額的爭奪使兩國在減產問題上成為兩個極端:沙特希望在保持現有市場份額的前提下達成減產協議;伊朗則希望獲得產量豁免權以奪回原有的市場份額,并彌補此前損失,達成這兩個目標之后再考慮是否減產。在2016年10月底召開的歐佩克專家會議上,兩國矛盾進一步激化,并且表示,如果伊朗仍然堅持不減產,沙特有可能大幅提高石油產量以壓低油價,甚至威脅退出會議。可以說,沙特和伊朗的分歧是此次歐佩克難以達成減產協議的主要原因。同時,這也充分體現出了對市場份額的爭奪極有可能導致歐佩克成員國之間,尤其是不同派系之間產生分歧的現實。2017年6月,中東七國與卡塔爾斷交,而這主要是由卡塔爾與伊朗關系引起的,特朗普訪問中東之后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對伊朗”的聲浪,而卡塔爾卻與伊朗越走越近,加之半島電視臺和卡塔爾政府網站的“假新聞”,使中東局勢變得更加復雜,歐佩克傳統的“鴿派三國”一分為二,而卡塔爾強硬的態度只會使這一輪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歐佩克各成員基本國情的差異和歐佩克自身結構矛盾及制度缺陷是導致歐佩克內部出現派系之爭的重要內因。而兩派斗爭不斷擴大并日漸激烈,主要體現在于伊朗和沙特這兩個代表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導致兩派分化對立狀況日益加劇。
第一,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歐佩克內部派系之爭的根源在于兩派國家在經濟基礎上的差異,而歐佩克國家經濟基礎上的差異主要源自于石油儲量以及經濟收入狀況上的區別。沙特是鴿派國家中石油探明儲量最豐富的國家,在2010年底委內瑞拉在奧里諾科河流域發現石油之前,沙特石油儲量一直居世界第一。因此沙特需要通過相對溫和的政策來維持其石油競爭力,但面臨其他替代能源的擠兌和競爭時,也會采取激進措施。相比沙特,阿聯酋與卡塔爾石油資源要少很多,甚至比一些鷹派國家還要少,但這兩個國家經濟較為發達,人均GDP遙遙領先,不需要利用高油價政策來賺取外匯,反而需要通過穩定的石油政策來維持石油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地位。相反,伊朗和阿爾及利亞這兩國石油資源相對匱乏,經濟相對落后,因此增加經濟收入促進國內發展是其制定石油政策的首要目標,而高油價無疑會帶來巨大的石油收益,在油價持續抬升階段擴大石油出口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收益。
第二,政治體制上的差異。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鷹派與鴿派政策差異并不大,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兩派在石油政策上出現分歧,并在此后不斷擴大。歐佩克內部的政治體制和結構差異主要體現在伊朗和沙特兩國的政治體制區別。伊朗在早期屬于君主制政體,王室在外交政策和石油政策上擁有絕對的主導權。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伊斯蘭體制政體,民族保守主義成了伊朗政策基石。伊朗政體的特殊性在于它擁有兩套系統,“一是反映其傳統價值觀的宗教系統,二是反映現代潮流的共和系統”。*金良祥:《伊朗外交的國內根源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第53頁。但在實際操作上,伊斯蘭系統的地位高于共和系統,這種政體更有利于保守主義掌權。這種保守主義蔑視和對抗強權,維護傳統的宗教意識形態,在外交政策和石油政策上表現為激進作風,希望通過油價的大幅度漲落來打擊強權,這從20世紀歷次定價和限產會議上伊朗支持大幅提價的主張上可見一斑。沙特長期以來維持著君主制體制,國內沒有合法政黨,國王擁有最高的司法權和行政權,但同時受伊斯蘭教義和教法限制,并且在重大事務的決定上需與宗教領袖、其他王室成員等協商,《古蘭經》是沙特國內的最高憲法。這種君主制決定了沙特在實行外交政策和石油政策時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就是不以犧牲君主合法地位和社會穩定性為代價,并且為了保證社會穩定不考慮付出的經濟代價程度。因此,沙特“石油政策比較保守,原因是害怕油價大起大落影響收入,導致政局不穩危及統治”,*張照志:“影響歐佩克石油政策的主要因素及其未來政策走向”,《資源科學》,2011年第3期,第455頁。長久以來都以穩定適中的油價政策為主。
第三,宗教派系上的差異。雖同為伊斯蘭國家,但伊朗和沙特兩國卻有著巨大差別。伊朗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主體為波斯人,什葉派約占91%。*中國駐伊朗使館,參見http://ir.chineseembassy.org/chn/zjyl/gjgk/t1295251.htm. (上網時間:2016年10月31日)沙特則是單一民族國家,其民族主體為遜尼派阿拉伯人,約占本國公民的85%。*中國駐沙特阿拉伯使館,參見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stgk/t708997.html. (上網時間:2016年10月31日)兩國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使其在對外政策上表現出對立狀態。對伊朗來說,維護穆斯林的利益首先是維護什葉派穆斯林的利益。2013年6月,埃及發生傷害什葉派事件,伊朗近200名議員聯合向埃及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調查此事*“Iran Condemns Killing of Shias in Egypt”, Tehran Times, June 26, 2013.,沙特對此則沒有明確表示。
第四,組織制度缺陷。歐佩克本質上是個松散的組織,雖然各國在產量政策上存在“共謀行為”*Gulen S. G., “Is OPEC a Cartel? Evidence from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Tests”, The Energy Journal, 1996, Vol.17, no.1, pp. 43-57.,但在落實過程中卻心口不一,協議通常并沒有強制力約束。產油國無法確保自己在遵守協議的情況下其他國家也能夠同樣遵守協議,而不受協議約束的國家往往能夠獲得更大的收益,最后的結果是各方無法達成協議,或即使達成協議各方也很難嚴格遵守。*董春嶺:“‘歐佩克時代’即將終結?”,《世界知識》,2016年第10期,第42頁。組織的松散性加劇了鷹派和鴿派產生分歧的頻率和烈度。一方面,鷹派國家由于儲量和產量較低而通常“背叛”,而鴿派國家只能選擇接受并做出讓步,鴿派國家因此在經濟和市場份額上遭受損失,當鴿派國家無法繼續承受損失時,雙方就會產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這種“背叛”行為經常發生,鷹派和鴿派的矛盾會不斷積累。2016年11月30日歐佩克達成減產協議之后,成立了減產監督機構,俄羅斯等其他11個非歐佩克產油國也加入到減產行動中,截至2017年2月減產執行率*減產執行率是指實際減產數量占目標減產數量的比重。假如當年減產目標每日減產100萬桶,實際每日減產80萬桶,則減產執行率為80%。已達94%*Alex Lawler, Rania El Gamal, “OPEC Compliance with Oil Curbs Rises to 94 Percent in February”,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ternational-business/opec-compliance-with-oil-curbs-rises-to-94-percent-in-february-reuters-survey/articleshow/57399724.cms.(上網時間:2017年4月5日),國際油價也開始回暖。然而2017年3月初,沙特突然宣布增產,國際油價連續超過一周下跌。5月25日,歐佩克召開第172次會議,決定將減產協議延長至2018年3月,并且不限制利比亞和尼日利亞的原油產量,*OPEC,“OPEC 172nd Meeting Concludes”,http://www.opec.org/opec_web/en/press_room/4305.htm. (上網時間:2017年6月15日)以期恢復國際油價,但國際石油市場卻并不看好這一行為,油價也出現了小幅度震蕩,利比亞和尼日利亞當月的原油產量增加約34萬桶/日。*OPEC,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 May 2017”,May 11, 2017,p.52.
從外因方面看,影響歐佩克派系之爭的因素主要有國際石油市場的變化和外交關系的變化等。其中,國際石油市場的變化包含了市場份額和石油競爭力與石油收入間的抉擇兩方面。
第一,對市場份額的爭奪。市場份額與石油收入上直接相關,對市場份額的爭奪也是歐佩克兩派產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尤其體現在伊朗和沙特兩國之間。對沙特來說,2014年不減產政策目的之一在于擴大亞太市場份額的同時利用伊朗處于核制裁階段石油產業被部分凍結而擠占伊朗先前的市場份額。2014年伊朗只有在油價達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實現財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須保持高油價以維持國內生計。*田文林:“中東亂局下沙特與伊朗的地區‘新冷戰’”,《當代世界》,2015年第6期,第45頁。不減產政策會大幅壓低油價,沙特能借此打擊伊朗的石油產業,迫使伊朗在石油做出讓步,并為本國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對伊朗來說,反對減產協議的原因在于,沙特在伊朗受制裁期間搶占了一部分伊朗的市場,制裁結束后伊朗需要以包括產量措施和油價措施等在內的政策重新奪回原有的市場份額,并且希望通過與中印俄簽署相關協議等方式早于沙特在亞太市場站穩腳跟。
第二,在石油競爭力與石油收入上的抉擇。各成員國在采取集體行動時,在政策優先選擇上的差異也會導致兩派產生分歧和斗爭。歐佩克鴿派成員由于石油儲量和經濟規模較大,會優先考慮維持石油競爭力,打壓油價能夠有效地將其他能源擠出市場,付出的代價便是石油經濟遭受損失;鷹派成員由于石油儲量和經濟規模較小,會優先考慮保證石油收入,抬高油價或增加產量能夠及時增加財政收入,付出的代價便是其他能源進入市場而使石油的競爭力下降。2014年沙特大力主張不減產政策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打壓頁巖革命帶來的非常規石油間接降低了傳統石油的市場競爭力的狀況,而伊朗、伊拉克等國堅決反對則是因為不減產政策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到了2016年,沙特等鴿派國家主張減產,是因為已經達到了擴大市場份額并保證石油競爭力的目的而不愿繼續遭受經濟損失,伊朗等鷹派國家反對減產則是由于石油收入會因為減產而進一步減少并且國內經濟在短期內無法恢復。
第三,外交關系變化。當鷹派國家或鴿派國家內部的外交關系惡化時,會導致集體政策執行力降低或者一國在短期內直接轉投另一派系;當鷹派國家與鴿派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惡化時,會導致整個派系斗爭加劇,集體行動更加難以達成。以兩伊戰爭和2016年伊朗和沙特斷交事件為例。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直到1988年才正式結束,戰爭雙方是同為鷹派國家的伊朗和伊拉克。伊朗在此期間堅持“向海灣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伊拉克則開始尋求沙特幫助,沙特在戰爭初期表示支持伊拉克,中后期甚至直接與伊朗正面對抗。其間歐佩克組織集體執行力下降,國際石油市場庫存嚴重過剩,油價下跌。1986年的減產協議達成之后成員國超配額生產的現象十分普遍,阿聯酋超產高達61.2%,科威特超產達23.2%,沙特超產達到了11.9%。*Ian Skeet, OPEC: Twenty-five Years of Price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76.2016年1月2日,沙特內政部以恐怖主義罪名處決47名囚犯,其中包括什葉派激進教士尼姆爾。這引發了伊朗的強烈不滿,而沙特隨后選擇與伊朗斷交,*謝瑋:“沙特伊朗爆發外交危機,油價受影響有限”,《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2期,第64頁。繼沙特之后,巴林、蘇丹、索馬里、阿聯酋、科威特和卡塔爾等國也先后宣布與伊朗斷交或者降低外交關系級別。*唐志超:“伊朗與沙特關系危機及其地緣政治影響”,《領導科學論壇》,2016年第10期,第88頁。沙特伊朗兩國關系惡化直接加劇了歐佩克內部兩派分野,這不僅反映在減產協議難產上,也同樣反映在兩派在也門危機和敘利亞問題的對立上,這次斷交事件無疑把歐佩克推向了組織撕裂的邊緣。
二、歐佩克派系之爭的影響
歐佩克內部派系斗爭對國際能源市場、石油輸出國、歐佩克組織自身、中東局勢和能源地緣政治等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是對國際石油市場及天然氣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就對國際石油市場的影響而言,體現在油價波動及全球能源供應結構和貿易流向上。國際油價從2014年7月開始下跌,并在此后由于不減產政策而逐漸加劇。本就飽和的石油市場由于產量增加導致原油不斷貶值,布倫特原油價格從2014年6月的115美元/桶一路跌至2015年1月的46美元/桶,*IEA,“Oil Medium-Term Market Report 2015”,http://www.oecd-ilibrary.org/energy/medium-term-oil-market-report-2015_oilmar-2015-en.(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日)盡管2015年年中國際油價穩定在了每桶50~60美元,但此后又出現下滑趨勢,12月更是突破了每桶35美元的大關,從2014年至2015年,國際油價降幅高達60%。歐佩克各成員國的石油現貨價格在2015年明顯下滑,各國出口額平均減少近50%。另外,歐佩克派系之爭所產生的油價波動會加速全球能源供應結構的轉變,未來石油的“中東時代”必然會走向終結,而北美地區非常規能源的地位和作用則會越來越明顯,全球石油貿易流向也會因此發生一定的變化。貿易流向轉變在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較小,原因在于非常規石油目前在國際石油市場的比重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這已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相較之下,歐佩克派系斗爭對國際天然氣市場的影響帶來的更多是間接影響和溢出效應,而這與當前國際天然氣定價機制有一定關系。當前國際天然氣市場有三大定價中心,亞太地區的天然氣定價機制以油價聯動定價模式為主,北美地區采取氣對氣定價模式,歐洲則處于從油價聯動定價模式向氣對氣定價模式轉變的過程當中。油價聯動定價模式是指將天然氣價格與反映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的原油價格掛鉤,使得天然氣價格可以隨著外部市場環境變化而對應調整,*張前榮:“國內外天然氣定價機制分析及經驗啟示”,http://www.sic.gov.cn/News/466/7444.htm. (上網時間:2017年7月15日)這種定價機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而氣對氣定價模式則是指通過實行管道第三方準入,建立天然氣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系,構建完全開放的市場。*同上注。歐佩克派系斗爭會直接導致國際油價的不穩定,而亞太及歐洲現行的天然氣定價機制意味著由歐佩克造成的油價波動必然會影響到全球的天然氣交易,導致氣價跟隨油價波動,這對能源需求大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極為不利。
二是對石油輸出國的影響,這直接體現在全球各石油輸出國的石油收入之上。此次油價暴跌給歐佩克國家自身的經濟造成很大沖擊,這直接體現在歐佩克各國的GDP之上,其成員國在2014年經濟開始放緩,2015年的GDP出現全面負增長。2014年,歐佩克中只有3個國家GDP出現了負增長,而利比亞高達32.74%的負增長率則很大程度上受到戰爭等問題影響;但到了2015年,13個國家(加蓬于2016年重新加入歐佩克,未計算在內)中,有7個國家GDP降幅超過10%,3個國家降幅超過20%,受損最嚴重的科威特GDP下跌了26.27%。同時,2015年歐佩克出現了新世紀的第一次賬上赤字,而上一次赤字出現在1998年經濟危機期間。不減產政策帶來的經濟下滑不僅出現在歐佩克組織內部,也同樣波及到其他石油輸出國。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全球原油開采成本的平均值大約為每桶50美元,歐佩克國家與非歐佩克國家的平均數據分別為每桶35美元與每桶60美元。就具體國家而言,美國頁巖油開采成本為每桶75美元,加拿大油砂礦開采成本為每桶80美元,俄羅斯原油開采成本為每桶45美元。因此歐佩克采取不減產政策之后,就石油行業而言,受到打擊最大的非歐佩克國家是美國和加拿大,而不是俄羅斯。美國方面,2015年上半年頁巖油鉆井平臺減少了52%,從1859臺下降至889臺,7月日均開采頁巖油減少近100萬桶。*IEA,“Oil Medium-Term Market Report 2015”,http://www.oecd-ilibrary.org/energy/medium-term-oil-market-report-2015_oilmar-2015-en.(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日)2015年2月,美國國內爆發了自198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煉油業罷工事件;3月份各大石油公司開始裁員,裁員比例高達10%以上;部分獨立石油生產商聲稱在2015年損失了140億美元。加拿大方面,2015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出現經濟連續負增長的情況,加拿大央行預估2015年國內油氣投資萎縮達到40%;同時,年度石油行業利潤創下新低,負增長率達19%,預估虧損量突破100億美元。俄羅斯方面,2015年石油出口收入為833.2億美元,同比下降約42%。石油出口總額以貨幣計為780億美元,同比減少約43%。對獨聯體國家石油出口為2085萬噸,出口額為52.7億美元,下降33.63%。*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經商參處:“俄羅斯2015年石油出口收入下降約50%”,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1/20160101236579.shtml.(上網時間:2016年11月5日)
三是對歐佩克組織本身產生消極影響。相比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各成員國的關系,2014年不減產政策實施之后歐佩克內部的矛盾被不斷放大和激化。就鷹派和鴿派的矛盾而言,伊朗、委內瑞拉等國不斷向沙特施壓要求改變石油政策,提高國際油價,并以拒絕參加凍產會議、要求產量豁免、單方面與俄羅斯達成相關油氣協定等方式向鴿派表示抗議;在鷹派內部,伊朗和伊拉克兩國為奪取歐佩克第二大產油國的地位矛盾也逐步升級,雖然同為鷹派國家,但伊拉克大力支持歐佩克制定相關凍產協議來穩定油價,而伊朗則表示拒絕采取凍產政策;就鴿派內部而言,看似相對穩定,尤其是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四國在幾次會議的政策協商和制定上表現基本一致,但事實上幾個國家間關系已經出現了裂縫。例如,在也門問題上,阿聯酋對沙特的支持力度一再降低;科威特國內支持巴林反對派的勢力逐漸上升,而沙特則是巴林政府的堅定支持者;卡塔爾則更為特殊,與伊朗共享氣田的現實使它與沙特關系并不如與伊朗關系親密,因此在不減產政策上更多的只是采取“部分追隨”的政策。2017年6月初,沙特等中東七國與卡塔爾斷交使得歐佩克內部成員國間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早前鷹派與鴿派的斗爭尚未平息,尤其是伊朗與鴿派國家針鋒相對,而此次多國與卡塔爾斷交又折射出了鴿派國家內部分歧層出不窮的現實,這將使歐佩克未來走向更加撲朔迷離。整體而言,歐佩克派系之爭只會撕裂組織,使其進一步走向碎片化,集體行動力越來越不如從前。
四是對中東局勢的影響和中東各國對中東領導權的影響。沙特和伊朗是早期爭奪中東領導權的主要參與方,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是君主制國家,與沙特在打擊民族分裂主義等方面有著共同利益,兩國盡管有政策上存在沖突,但彼此并未采取實際的針對措施。自巴列維王朝結束之后,沙特與伊朗走向分野,并開始爭奪中東地區領導權。伊朗在對外關系上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持反感立場,但對發展中國家卻相對溫和。因此伊朗長期在石油政策上都以優惠手段爭取亞太市場,同時利用高油價打壓美國市場,并長期與沙特保持對立。相反,沙特則多將目光投向歐美等發達地區,對亞太市場的關注大約盛于伊朗核制裁時期。以伊朗和沙特兩國為首的兩派國家在石油及外交政策上的互不讓步使中東局勢本就處于緊張狀態,而近幾年來卡塔爾也希望能在這之中有所作為,包括舉辦各種類型的大型政府間國際會議與活動、增強自身話語權、在石油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逐步擺脫“追隨”沙特而加強獨立自主權等。新一輪歐佩克內部矛盾不僅使沙特和伊朗對中東領導權的爭奪越發激烈,也同樣使中東局勢變得更為復雜,未來對中東領導權的爭奪甚至有可能走向三足鼎立的狀態。而中東地區的進一步碎片化可能會加劇地區不穩定,給地區安全帶來威脅。
五是對能源地緣政治的影響。能源地緣政治強調能源特別是油氣資源的供需與能源消費國、能源供應國的國家安全、能源輸出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國家關系、國家權力之間的密切聯系。*伍福蓮:“論當今能源地緣政治的特征”,《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15年第2期,第198頁。對于能源輸出國來說,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供應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政治權力,從而影響國際關系,這集中體現在兩次石油危機當中。由于當前石油仍是全球主要能源,石油供應國的政治權力不容忽視,全球范圍內石油產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中有一半是歐佩克成員國。但是,看似“不對稱”的權力分布有可能會隨著組織內派系之爭而發生變化,石油政策及外交關系上的長期對立會人為地造成國際石油市場供需關系緊張,并且使石油供應給歐佩克帶來的政治權力分散化,而由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三國形成的北美石油供應集團則會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力,甚至在未來取代中東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地位。對能源消費國來說,其首要任務是保障本國能源供應的充足與穩定,并且使能源進口成本在可控范圍內。因此,能源消費國需要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尤其是對單一地區的依存度,歐佩克派系斗爭帶來的國際油價波動使能源消費國的經濟受損,加速了各國推動本國能源進口多元化的進程,同樣也加劇了各消費國對同源能源的爭奪,這都會加快石油“中東時代”的終結。對能源輸出國和消費國之間的互動來說,歐佩克的派系斗爭會使由能源輸出國與消費國所形成的國際能源體系更加不穩定。美國之所以長期在國際能源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原因在于: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中地位特殊,它既是第三大石油輸出國也是第一大能源消費國;美元長期以來是原油唯一的計價單位;美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對全球重要能源產地和能源通道施加影響。但是美國的中東戰略并沒有起到穩定中東石油供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地區不穩定因素,這只會導致歐佩克鷹派國家反美情緒日益加重,進一步威脅地區安全,從而影響全球能源供應、動搖全球能源體系。歐佩克派系之爭則會使地區對抗的可能性大大上升,對美關系的差異也會使能源輸出國和消費國內部出現嫌隙及分野,這將直接影響到中東的石油供應以及全球能源體系的穩定。
三、歐佩克派系之爭的可能走向
從當前歐佩克內部鷹派和鴿派國家的關系來看,兩派斗爭的未來趨勢存在三種可能性:走向緩和、保持原狀、走向決裂。
第一種可能,即兩派關系走向緩和,將呈現出有限斗爭的狀態,兩派的斗爭依然存在,但這些斗爭處于組織協調之下,各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以合作為主。要達到這種狀態,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在歐佩克組織內構建起強制力來約束各成員國,防止組織內各國出現相互背叛的現象,盡管鷹派國家和鴿派國家之間的斗爭仍舊存在,但強制約束力會將這種斗爭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使整個歐佩克組織在政策制定和落實上以合作和集體行動為主;二是伊朗和沙特這兩個分別代表鷹派和鴿派的國家相互妥協,從而促使兩個派系的關系走向緩和,伊朗和沙特分別作為鷹派和鴿派的代表國家,雙方是否能達成妥協對歐佩克的穩定至關重要,而能夠保持組織穩定的妥協至少是中長期的。兩國關系的緩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引導兩派國家關系走向緩和,促進開展合作,從而使派系之間的斗爭降到較低烈度。這種情況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現實中發生的可能性較小,一是由于在歐佩克松散的組織結構下構建強制約束力的操作難度較大,二是由于目前伊朗和沙特的關系仍相當緊張。
第二種可能,即兩派關系保持原狀,則歐佩克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仍以斗爭為主,開展合作的前提條件將變得更加苛刻。而在當前狀態下想要促成兩派的合作需要至少滿足以下兩個前提條件之一。第一,大國給予小國(主要是鴿派國家給予鷹派國家和中間派國家)一定的優惠條件。不管是石油輸出小國還是石油輸出大國,從中長期來看,縮減產量下國際油價攀升所帶來的石油收入,要大于增加產量下國際油價低迷所帶來的石油收益。另外,減產除能增加收入外,還能保護現有的石油資源,從而延長本國石油開采的持續性。但從短期收益來看,石油輸出小國會因為減產而進一步遭受經濟損失。為了鼓勵小國參與到減產行動中,大國需要對小國在短期內給予一定的優惠條件,包括對小國的經濟損失進行補償和在具體減產政策的制定上給小國以產量優惠或最優條件;第二,鷹派和鴿派國家在石油政策上的主要國家利益基本一致。利用共同利益達成合作是最為有效的手段,但這種合作大多數是臨時性的,并且主要是為了應對外部挑戰而產生的,它無法消除成員間的矛盾。合作只能暫時緩和成員間關系,一旦外部挑戰消除,矛盾會繼續持續下去。因此,這種合作是有限的,并且在短中期內發生的可能性較大。當前歐佩克在國際石油市場的地位和影響力仍難以撼動,石油競爭力也依舊強勢,維持組織的穩定更符合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利益。
第三種可能,即兩派關系走向決裂,則整個歐佩克組織就將面臨分化重組的問題,并且至少會形成鷹派和鴿派兩個不同陣營的新型共同體。這在短中期內無法達成,但在長期看來是一種可能性較大的趨勢。原因在于:第一,傳統石油競爭力將會逐步下降。英國石油公司預測,化石燃料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主要能源,并且在2035年國際能源市場比重中仍然能夠達到80%左右*BP, “BP Energy Outlook to 2035 (2016 ed.)”.。但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則預測,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到2040年會持續下降,并且總體數量會維持在1/3左右。*Exxonmobil, “The Outlook for Energy: A View to 2040”.同時,當前國際能源市場上出現的美國的頁巖油、加拿大的油砂、北美地區的致密油、墨西哥灣地區的深海石油等油氣資源開發正在使石油供給結構多元化。各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的迅速發展也將會促使廉價能源進入市場,從而導致傳統石油競爭力下降,但國際能源市場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進入這個周期。一旦進入新能源時代,歐佩克將會失去它在國際能源市場的主導能力,歐佩克的穩定性對于各成員國來說變得不那么重要,兩派也更有可能將這個組織撕裂。
第二,國際能源市場出現多極化趨勢。進入新世紀后,歐佩克僅憑一己之力就能左右整個國際能源市場的時代已經離去。非歐佩克產油國的實力上升,以及各種能源組織的成立使國際能源市場出現多極化趨勢。歐佩克集體行動的落實需要非歐佩克產油國的支持,但同時雙方又是競爭關系。在非歐佩克產油國無法形成一個能與歐佩克相抗衡的國際組織的前提下,這些國家往往會根據外交關系和自身利益與歐佩克內部國家單獨合作,使得組織凝聚力降低。而國際能源組織的興起又起到了市場監督和政策協調的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正在逐步加強,這既打破了歐佩克專斷獨大的局面,也間接地給組織分化創造了機會。
第三,歐佩克組織內的矛盾愈演愈烈。組織內的矛盾是使歐佩克存在走向分化重組可能性的根源所在。歐佩克組織成員國之間的關系陰晴不定,但整體趨勢處于惡化階段。這種矛盾惡化不僅出現在鷹派國家和鴿派國家之中,也同樣出現在鷹派國家和鴿派國家內部。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伊朗沙特兩國不斷交惡,兩次斷絕外交關系,作為兩派的代表國家,兩國關系變化無疑會影響成員國間關系;兩伊關系不穩定,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當前兩國對第二大產油國地位的爭奪等使鷹派國家內部逐步出現分歧;卡塔爾向伊朗示好,阿聯酋對沙特支持力度下降,這將導致鴿派國家內部出現嫌隙。2017年6月5日,沙特以“嚴重違反國際法和睦鄰友好原則”為由與卡塔爾斷交,隨后,阿聯酋、利比亞等國先后與卡塔爾斷交,約旦與之降低外交關系級別。沙特方面聲稱此次事件主要由卡塔爾“支持受伊朗資助的恐怖組織”和“破壞地區安全局勢”*新華每日電訊:“中東多國與卡塔爾斷交,宿怨使然”http://www.sohu.com/a/146539755_115402. (上網時間:2017年6月15日)引起,但卡塔爾卻予以否認。由此可見,歐佩克內部的派系之爭不僅局限在鷹派和鴿派之間,各派系內部的斗爭也不斷顯現出來,這將給歐佩克未來的發展蒙上一層陰影。當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時,整個組織將分崩離析。○
作者介紹陳騰瀚,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
吳興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