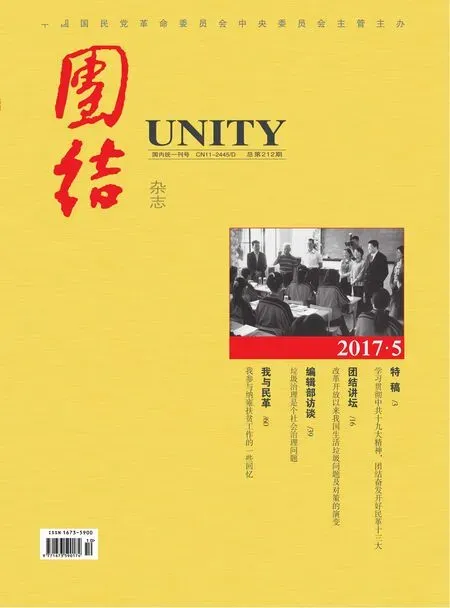共享經濟下政府投資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周 勤
共享經濟下政府投資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周 勤
共享經濟時代來到
共享經濟是對傳統經濟思想的重大發展。我國經歷了長時間的短缺經濟時代,政府投資主要方向是解決人民基本生活。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我國經濟出現相對過剩,在六千億基礎設施資金投入的推動下,以消除地區貿易壁壘為目標,開展全國性大規模高速公路和鐵路建設,加快了區域之間的流通速度,基本消除了東部地區的交通哽堵,為我國進入WTO后東部地區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
1997年東南亞危機結束后,特別是以2001年我國進入WTO等為契機,中國進入以房地產經濟為主導城市基礎設施大發展時代,其模式是 “以地補路”為主導的資源型政企合作模式,進一步完善我國省際公路網,基本完成我國主要通訊網絡和電力設施建設,為共享經濟到來提供能源和通訊方面的保證。在內外經濟環境極其適宜條件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穩定的增長時期,也逐步形成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主體的區域建設。中央政府負責跨區域和西部投資基本分工格局,形成了穩定高速增長的態勢。
這一模式延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而告結束,特別是中央政府四萬億政府投資后。八縱八橫鐵路網,特別是高鐵的全面建設,加上遍及東部每個市縣高速公路,4G網絡覆蓋了幾乎每個三四線城市,進一步觸發地方政府投資熱情,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寬度和厚度,形成巨額地方政府債務。2010年北美和西歐國家開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2012年后我國進入全面過剩經濟時代。這為共享經濟時代到來提供了生產和消費上潛能的保證。
2012年我國跨越式進入全面利用互聯網技術的共享經濟時代。在這一新經濟環境下我國政府投資將何去何從?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我國商品市場從絕對短缺到相對過剩到絕對過剩,企業之間經濟關系從競爭到競合走向共享,國內經濟環境不斷自我完善。問題是我國目前這三種模式既重疊交錯,又彼此獨立運行,企業從叢林規則到選擇合謀再到共享治理迫使我們認識實踐不斷提高。我們要明確我國共享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明晰我國政府投資面臨新挑戰,尋求最優政府投資模式和政策。
共享經濟下政府投資遇到的挑戰
首先是產權的分散性。分享經濟條件下經濟權力的進一步分解,這是對政府投資權益粗放的挑戰。產權作為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基礎權利,本身是一個權利束,在現有組織的委托代理制度下經過了有效的分解,從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開始,權利不斷分解為權益和利益的碎片。在共享經濟下,這些權利碎片還將進一步溶解在共享經濟各個環節中。
共享經濟的核心實際上是部分權利的轉讓,在政府投資的產品和服務中難以實施。例如,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難以碎片化來適應共享經濟多維度空間需求,政府投資只能保證產品和服務中是“有”或者 “沒有”,不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將權利細化以適應不同定價,這將使政府投資方向偏離現代公共服務的需求。從這個意思上說,產權的細化會挑戰傳統政府投資模式,使得向大規模定制型采購模式轉化。
二是需求精準化。差異化需要是共享經濟時代的 “悖論”,一方面是生產能力絕對過剩,另一方面是大量個性化需求無法滿足。特別是中國在過去十五年中,我國制造業的高速崛起,主要工業中間品和制成品都增長十倍以上,使得現有的制造能力不僅遠遠超過了我國國內社會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超過世界發達國家的貿易需求。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20世紀初以泰羅制倡導科學管理引發的大規模低成本生產,第一次解決了人類短缺經濟問題;20世紀七十年代波特提出戰略管理滿足人們差異化需要。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新經濟時代到來,2008年金融危機后,以網絡經濟為主導新過剩經濟,以P-G理論為基礎的能力管理的典范——“微軟—英特爾”模式,開創了供給引導需求時代,使得在新制造業的蓬勃增長為需求精細化提高了先決條件。如何適應這一需求變化,這對我國政府投資長期以來一直注重供給側而形成的行為慣性提出了重大挑戰。
三是收益普惠性。在傳統福利經濟學理論中,政府投資將著力填補市場缺陷、解決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降低社會分配不公,這也是共享經濟中不同于傳統經濟模式一個亮點,兩者具有一致性。但是,從現有共享經濟主要模式和社會福利分析,社會分配不平等日趨嚴重,借助互聯網可以使社會轉移和再分配成本大幅度下降,并沒有提高底層民眾收益。也就是說,共享經濟只是降低個人到社會的交易成本,本質上沒有改善他們的收益分配。
分享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沒有改變人們之間收入的不平等狀態,主要是以政府投資為主體建立了公共網絡和其他基礎設施,其投資者是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而投資來源就是政府投資。每年以萬億為基礎單位,其投入構成互聯網、公路和高速鐵路,其大幅度折舊收益,實際成為主導共享經濟互聯網平臺利潤,也就是政府投資直接或者間接變成網絡平臺企業的基本收益。也就是說,為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政府投資,在分享經濟中可能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這是對現有政府投資的終結目標的最大挑戰?
從現實情況,互聯網經濟加劇了國家、地區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共享經濟降低了個人通過網絡中間自由的轉換成本,同時社會再分配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共享經濟使下層人獲取信息和表達的成本極低,更容易辨別社會不平等程度。那么我國政府投資怎么面對這些挑戰呢?
共享經濟下政府投資治理模式的再突破
一是政府投資治理主體的再突破。在共享經濟時代治理模式已經從以自我管理為中心第一方治理時代 (這是傳統市場經濟以自我為中心的本源),形成 “大社會,小政府”基本模式,政府投資主體是稱職 “守夜人”。但是,市場失敗本身要求政府投資主體承擔消除包括壟斷、外部性和內部性等第一方治理難以彌補的這些缺陷。進入競合時代合謀模式成為第二方治理,政府投資對組織 (或者非盈利機構)的投入,實際是治理主體的轉換,也是對第一方治理的提升,包括政府部門本身的管理,都是第二方治理的體現,而 “政府失敗”也是難以掩飾的事實,其管理成本、尋租與腐敗、以及管制時滯等都是政府投資無法避免又備受詬病的弊端。而新經濟以來政府投資轉向平臺第三方治理應該是一個出路,也就是將政府投資的主體轉換為獨立第三方,并由此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完成共享經濟的目標,從一個投資主體轉化為征信主體。當然,這三種模式將并存不悖,發揮各自優勢,而共享經濟時代的平臺治理將逐步成為主導模式,政府投資治理模式也應該隨之轉換,必須重新選擇新模式實現再突破。
二是政府投資在治理結構上的再突破。在共享經濟時代技術優勢或者技術領先是決定性的,政府投資是否會導致資產結構和治理結構進一步優化,進而促進技術進步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現有所有的平臺共享模式都是以技術先導為決定性的,沒有技術上的領先,所有的共享模式是無法長期維持自己的領先地位的。例如,共享經濟的基礎平臺WINDOWS操作系統是表現為微軟—英特爾模式,實質上是兩個公司技術的領先;同樣,蘋果手機是第一個產品平臺,其APP模式的背后是蘋果公司在智能手機技術上的優勢。從這兩個案例發現,共享的模式只是表現形式,而技術是其基礎。所以從治理本身來說,掌控技術的領先實際上是贏得治理地位的關鍵。反之,沒有技術優勢將永遠處于被治理的被動地位。所以,在共享經濟時代政府投資的方向要從注重共享網絡的基礎設施保證——這已經導致了分配的進一步不公,轉向共享基礎技術的發展,為更多社會底層建立免費或者低成本共享技術,為共享經濟平臺的終極目標提供技術保障。
三是政府投資在治理規則上的突破。在共享經濟時代規則意識與規則優先是政府投資治理模式中最主要的原則,實現共享本身的前提是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們開放初期,為了解決計劃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沉疾,簡化幾乎所有規則,同時也忽視了政府投資治理規則完善,形成簡單粗放與繁復縟節并存政府投資現狀。在共享經濟時代規則優先與技術領先同等重要,所以我們重建共享時代政府投資規則意識,實際上也是對整個社會道德底線的重塑。從目前來看,現有類似共享單車等人為損壞等種種問題,實際上是對傳統政府投資公共品規則意識強烈反應的表現,政府投資的規則彌補了組織規則與市場規則之間的缺陷。
四是政府投資風險防范的再突破。政府投資風險在共享經濟時代也是難以避免的,大數據為政府投資提供治理和防范風險最重要的手段。從理論上說,在共享經濟時代政府投資風險遠遠高于傳統市場經濟時代,投資主體和客體變得更加模糊,產權的細化使得治理成本進一步增加。利用大數據控制治理政府投資風險已成為必然的選擇手段,這本身也是政府部門優勢,同時也是避免政府投資風險擴大必要手段;政府投資的低收益和長期性一直是其高風險起因,而高頻數據可以消除甚至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同時也是政府投資治理中間最重要也是最新的路徑。
總之,政府投資是彌補短缺經濟時代投資不足的主要手段,也是減緩需求過剩 (相對)時代組織與市場失敗的必然過程,更是共享經濟時代實現供給 (絕對)過剩時代的共同富裕的終結目標基本保證。
(周勤,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責編 劉玉霞)